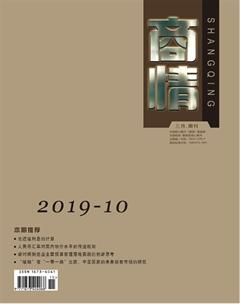同人小說的著作權問題探討
張涵佩
【摘要】金庸訴江南案被稱為“國內同人作品第一案”。查良鏞(筆名金庸)將楊治(筆名江南)、北京聯合出版有限責任公司、北京精典博維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廣州購書中心有限公司以著作權侵權和不正當競爭訴至法院。原告金庸發現被告江南在未經其同意的情況下,在創作的小說《此間的少年》中大量使用了金庸小說的知名人物,如郭靖、黃蓉、令狐沖等。為此,金庸向江南提起訴訟,并將統籌、出版商北京聯合出版有限責任公司、北京精典博維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及對《此間的少年》進行銷售的廣州購書中心有限公司一并作為被告,要求停止侵權。
【關鍵詞】著作權 同人小說
一、案件分析
1、原告作品中所涉及的人物名稱、人物關系、性格特征和故事情節屬于思想范疇還是屬于具有獨創性的表達,是否受我國著作權法保護。2、被告所著《此間的少年》作品所涉人物名稱、人物關系、性格特征及故事情節是否與原告作品構成實質性相似。3、被告是否侵害原告所享有的改編權、署名權以及保護作品完整權被告所稱僅系合理使用作品要素的抗辯能否成立。4、被告是否借助原告作品的知名度,通過搭便車的方式牟取利益。5、本案經濟損失數額如何確定,原告的部分賠償請求是否已經超過訴訟時效。
(一)江南是否侵害金庸的著作權
同人小說,指的是利用原有的漫畫、動畫、小說、影視作品中的人物角色、故事情節或背景設定等元素進行的二次創作小說。《此間的少年》講述的是大學生活,小說以宋代嘉佑年為時間背景,地點在以北大為模版的“汴京大學”,登場的人物是喬峰、郭靖、令狐沖等大俠過著大學生活。經原告比對,被告作品與金庸作品雷同人物為66個,雷同情節為4處,可見《此間的少年》借用了大量金庸武俠小說里的人物角色,對故事情節進行了再度創作。
我國司法實踐中,普遍接受的侵害著作權認定要件是“接觸+實質性相似”。
接觸是指后作品的創作者接觸過先作品的創作者,很顯然,本案中接觸這一構成要件是符合的,金庸的小說出版在先,無論是在書店等線下銷售場所還是在網絡等線上的平臺,被告江南均有機會和可能性接觸到被告的作品。江南的小說運用了66個與金庸小說雷同的人物,進一步驗證了江南符合接觸金庸小說的構成要件。
“實質性相似是指在后作品與在先作品自表達上存在實質性相同或近似,使讀者產生相同或近似的欣賞體驗。”[: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08)二審民終字第02232號]根據這個定義,要判斷作品是否構成實質性相似,應分三個步驟:一、確定作品中實質性部分的內容;二、對實質性內容進行比較,后作品中是否存在與先作品實質性相同或相似的內容;三、這種實質性的相同或相似是否使讀者產生相同或相似的欣賞體驗。
本案所涉及的兩部作品均為小說,小說的構成不僅涉及文字表達,還涉及到情節、人物、對話、背景等要素。實質性部分是作者獨創性表達的部分,在本案中,認定金庸小說的實質性部分及比較金庸和江南小說是否相同或相似應從小說的題材、情節、人物角色和人物關系等重要部分著手進行綜合分析。
金庸小說主題以武俠為主,主背景是虛構的江湖,“郭靖”、“黃蓉”、“楊康”等人在江湖恩怨中的故事;江南的小說主題以大學生活為主,主背景是大學生活,郭靖”、“黃蓉”、“楊康”等人在大學生活中的故事。原告律師統計,《此間的少年》一共78個人名,其中66個與金庸經典作品雷同,單純的來看這個比例,似乎在感官上認為這應該是抄襲。但是在分析人物這一要素時,不能只看表面的相似性,需要結合人名和人物性格分析,如《此間的少年》將《天龍八部》心如蛇蝎的康敏改為正面人物,雖然名字一樣,但人物性格做了改變,與原作品存在較大差別,讀者的閱讀體驗并沒有與《天龍八部》混淆。江南只是將金庸小說中的人物姓名這類素材進行使用,其作品是獨創性的表達,是將原作品的元素當做創作的素材。這種創作是對原作品內容使用的轉換而非復制,這種轉換產生的是不同于原作品的新的質素與內涵,原作品在新作品中的體現微乎其微,新作品中已經完全看不出原作品的架構和情節設計,因此不能認定為江南的作品與金庸的作品存在實質性相似。
根據侵害著作權認定要件:“接觸+實質性相似”,通過分析只能認定江南的小說構成接觸這一要件,不構成實質性相似這一要件,所以不能認定江南侵害了金庸的著作權。
(二)江南是否借助金庸作品的知名度
原告金庸認為被告江南借助金庸作品的知名度,通過搭便車的方式牟取利益。江南對金庸人物名稱的使用是一個無可爭議的事實,如前文所述,江南利用了金庸小說中的大量人物姓名,而這些人物大多為金庸作品中的知名人物。原告所提出的借助知名度來謀取利益是指在讀者閱讀時這些知名人物會使讀者在潛意識里產生好感,為江南的作品贏得有利的地位,增加了《此間的少年》的聲譽,增強了自己的競爭優勢。
但原告提出的借助知名度來謀取利益是建立在讀者知曉這些人物來自于金庸的小說。假設一個讀者沒有讀過金庸的任何一部小說,對于金庸的了解僅限于知道金庸是一位著名的武俠小說作家,聽說過“郭靖”、“黃蓉”等為數不多的幾個人名,但不了解其中的故事,那么原告提出的被告借助原告作品的知名度,通過搭便車的方式牟取利益則不能成立。原告無法證明有多少人是因為喜歡金庸從而被人物名稱吸引去閱讀《此間的少年》,或者說有多少閱讀過《此間的少年》的讀者在此之前閱讀過金庸的小說。雖然金庸的小說出版在先,但也有可能讀者先閱讀《此間的少年》,被小說中人物所吸引,從而去閱讀金庸的小說,那么這種情況下,江南的小說反而對金庸的小說有宣傳和幫助作用。所以原告認為被告“搭便車”、“蹭知名度”的主張不能被支持。
二、小結
同人小說處于一個比較特殊的位置,在判斷一個同人小說是否侵犯原作者的著作權時,一定要具體的比較其中的實質性部分。同人小說涉及的原作者的著作權值得保護也必須保護,但如果同人小說的作者沒有抄襲他人的惡意和行為,其作品由作者獨立創作完成,沒有侵害原作品的實質性部分,那么不論是基于促進文學發展的角度還是基于法律的角度,都應當賦予同人小說的作者應有的著作權利。現如今我國的著作權法沒有對有關同人小說的問題有清晰明確的規定,通過法律的形勢確定同人小說的適用標準和爭議的解決方法,對原作者和同人小說作者的著作權都起到保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