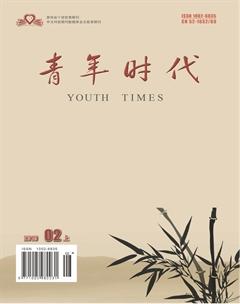論《變形記》中主人公孤獨感的營造
莊敏
摘 要:《變形記》是著名小說家弗蘭茨·卡夫卡的短篇小說。小說中的主人公向讀者傳遞了強烈的孤獨感,這種孤獨感的營造離不開作者的巧妙構思。本文將從主人公遭受的生理異化、空間隔絕以及主人公自身和外界表現的對比三個方面探討作者在小說中對主人公孤獨感的營造。
關鍵詞:孤獨感;生理異化;空間隔絕;自我與外界;《變形記》
《變形記》①講述了一個人變甲蟲的故事,而故事的主人公在遭遇了生命的巨變后則承受著精神上無邊的孤獨感。小說呈現出的孤獨感直接而強烈,能夠輕易被讀者所感知。本文從主人公的生理異化談起,試圖揭示主人公孤獨感的直接來源;繼而以空間隔絕為立足點,分析作者為主人公搭建的空間在表現孤獨感方面的作用;最后整體對比主人公在異化后自身和外界的表現,揭露外部世界如何推動主人公孤獨感的形成。
一、生理異化
《變形記》的開頭對于每位讀者來說都不陌生:“一天早晨,格里高爾·薩姆沙從不安的睡夢中醒來,發現自己躺在床上變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蟲。”緊接著作者對主人公的甲蟲外形進行了細致的描寫。小說開頭的描寫使主人公在最開始就成為了異類,他的格格不入最明顯的表現就是他異化后的外形。作者沒有選取諸如貓狗這一類可愛的動物作為主人公的新形象,而是挑選了外形容易激起常人反感的甲蟲,可見作者是有意通過外形阻隔主人公同其他人的情感聯系。作者數次在小說中勾勒主人公的甲蟲外形,包括他的背部、肚子、外殼、細腿等,讀者在腦海中想象出主人公后都難免會受到強烈的沖擊,更何況小說中的其他人物。因此當主人公以新形象第一次出現在眾人面前時,秘書逃離、母親尖叫、父親哭泣,大家的態度已經很好地說明了格里高爾是個異類,他的外形就像橫亙在他和別人之間的木板,隔絕了共情的可能。
在小說中,作者數次著力描寫格里高爾異化為甲蟲后的行動不便。初為甲蟲,格里高爾不懂如何準確地翻身、著地、后退,他只能獨自摸索,適應不便。然而沒有人會體諒他的難處,也沒有人提出要幫助他,大家都只是冷眼旁觀。
可以說,甲蟲外形在一開始只是一個外在形態,還未能有力營造主人公的孤獨感,但隨著小說情節的推進,甲蟲外形越來越不被小說中的其他人物所接受,而隨著突兀程度的加深,主人公的孤獨感也在逐步加深。外在形態的影響如此巨大,以至于家人不會考慮軀體中是否還會安放著格里高爾的靈魂,因此此時的格里高爾與他的甲蟲外形可以說是“彼此的依靠”了,孤獨感就在主人公與甲蟲外形的融合中凸顯出來。
二、空間隔絕
《變形記》中的空間展現是很明顯的,作者正是有意通過空間的隔絕營造主人公的孤獨感。小說中有三次寫到格里高爾從個人空間進入家庭空間的場景,第一次是他變成甲蟲的那個上午,第二次是妹妹和母親企圖搬走他房間里的家具時,第三次是他進入起居室聆聽妹妹拉小提琴的夜晚,然而這三次經歷最終都以格里高爾被趕回房間而告終。家里人把格里高爾的房間視作一個可怖之地,也視作一個關押之所,并且在格里高爾的個人空間和家庭公共空間之間他們始終設有隱藏的嚴密界限,因此格里高爾每次進入家庭公共空間都會被視為一種攻擊和挑釁。對于格里高爾來說,他由原先的被驅趕到后來在明白了大家的驅趕意圖后自己主動爬回房間,表明他漸漸知道了自己在家庭中應占有的正確空間在哪里,家庭公共空間不接納他的進入已是不爭的事實,他在公共空間中的退場既顯孤獨,又添悲涼。
然而,作者并未將格里高爾的房間描繪成為一片凈土,在他的房間中作者仍然試圖展現第二種空間隔絕。即使在自己的房間中,當妹妹要進入時,格里高爾為了避免驚嚇到她仍然要躲在長沙發的角落里,甚至后來還用床單遮住自己的身體。這種情況下的格里高爾最終的歸屬空間事實上只有一個角落,這也意味著大家對他的接納充其量也只能達到角落般的大小,一旦他越出角落被人看見那么即使他沒有任何攻擊行為大家也會將他視為敵人,罪責將盡數歸到他的頭上。大空間中的二度空間隔絕使格里高爾顯得越發孤獨無助,角落的狹小逼仄與外部世界的寬大廣闊形成了鮮明對比,而他的孤獨感卻在生活空間的被擠壓中噴涌而出。
此外,正是由于這兩大空間的隔絕使格里高爾對自己的房間形成了特殊的感情,房間于他而言是庇護所和休息區,因此在沒有人時他便在房間里任意爬行,感受房間里的事物帶給他的安定,這是他在面對強烈孤獨感時的自我慰藉。但是這種安定很快又被打破——妹妹和母親企圖搬走他房間里的家具。這很有可能會使他失去感情支撐,抹去他身為人類時的記憶,因此他拼盡全力也要保護那幅他喜歡的畫像。一方面,這是他在忍受巨大的孤獨感后的外在表現,因為他只能以房間里的事物作為感情依靠所以他必須得捍衛個人空間;另一方面,外部世界無法看清他的孤獨,甚至誤讀了他的內心世界并對他的個人空間指手畫腳,這種不被理解與他壯烈的行為結合起來就使他的孤獨感尤為動人。
三、自我與外界表現的對比
《變形記》中主人公在變形后自身的表現與外界的表現形成鮮明對比,這些對比進一步渲染了主人公的孤獨感。總體來說對比可分為以下兩類:
一是主人公面對自己的態度與外界對他的態度形成的對比。主人公在剛發現自己變成甲蟲時心態很平靜,也并未表現出很大的驚異,那時他還想著要趕去上班,但外界對其自然是避之不及,這種強大的反差使主人公在小說中展現出的是孤立無援的狀態,他就像在被人嘲笑的丑角一般立在小說之中。
“可是格里高爾才說頭幾個字,秘書主任就已經在踉蹌倒退,只是張著嘴唇,側過顫抖的肩膀直勾勾地瞪著他。格里高爾說話時,他片刻也沒有站定,卻偷偷地向門口踅去,眼睛始終盯緊了格里高爾,只是每次只移動一寸,仿佛存在某項不準離開房間的禁令一般。”
現實生活中平常人不可能做出如主人公一般的反應,這當然能夠從側面說明主人公被生活的重壓異化后的心理,但同時也是對他孤獨感的營造。因為此時的主人公還懷有人類的心理,他以為自己還能夠被社會接納,他還沒有意識到明顯的不妥,他坦然自若的表現與外界對他的恐懼和躲避形成極端對比。甚至到了小說的后半部分,主人公在聽到妹妹拉小提琴的聲音時還幻想讓妹妹把小提琴帶到他的房間去,并且要和妹妹吐露心聲,其實小說發展到了此時這個情節是非常不合理的,但作者偏偏要以音樂為餌誘使主人公跌入不切實際的自我幻想中,繼而又迅速用周圍人的厭惡和冷漠打破主人公的幻想。這種“世人皆醒我獨醉”的態度展現的是主人公對自身命運和人性的認識不清,他愈是以正常的人類思維看待自身,小說中的其他人物甚至包括讀者都愈發認為他不正常,正是此種荒謬和反差使他的孤獨感被進一步放大。
二是主人公對家人的態度與家人對他的態度形成的對比。這一對比在小說中是非常明顯的。主人公在異變后仍然擔心家里人的生計問題,并且為自己無法再賺錢養家感到羞愧,同時他也明白自己對家庭造成的困擾,因此他總是竭力避免影響家人。然而家人對他的態度卻令人心寒,父親對格里高爾的兩次驅趕使小說的氣氛異常沉重,格里高爾的遭遇讓人痛心。被家人冷落和傷害的格里高爾仿佛置身無人的荒原,他只能拖著他日益消瘦的身軀沉默而孤獨地活著,直至走向死亡。而在小說的結尾,格里高爾在死亡前仍然“懷著溫柔和愛意想著自己的一家人”,而他的家人在他死后卻覺得擁有了“新的夢想和美好的打算”。這種春日暖風和冬季寒風般的態度對比使主人公身上的孤獨感在他去世后都無法消散。小說中作者一直在推進故事情節的發展中鋪寫這種對比,這些充滿細節的對比營造出的孤獨感是飽滿而強烈的,每一次明顯的對比都意味著主人公的命運轉入更凄苦的境地。最后作者借助死亡的結局讓主人公的孤獨感在結尾到達了頂峰,但是這種孤獨感并未隨著看似充滿希望的結尾而漸趨減弱,而是久久彌漫在小說之中,始終敲擊著讀者的心靈。
四、結語
在《變形記》中作者從生理異化、空間隔絕以及主人公和外界表現的對比三個方面著力營造了小說主人公的孤獨感,這種孤獨感貫穿全文,能夠引起讀者的強烈共情。小說中孤獨感的營造不僅使主人公的形象更加獨特,同時也對小說主題的表現具有重要的作用。
注釋:
①本文所引內容皆出自卡夫卡.變形記[M].李文俊等譯,北京: 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
參考文獻:
[1]卡夫卡.變形記[M].李文俊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
[2]劉偉安,趙學斌.語言的焦慮——卡夫卡小說《變形記》主題新探[J].浙江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04):73-77.
[3]李麗華.論卡夫卡《變形記》的空間想象與敘事[J].大眾文藝,2017(01):31-32.
[4]索紹武.亦幻亦真好精彩——卡夫卡的《變形記》藝術特色分析[J].蘭州大學學報,2000(S1):157-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