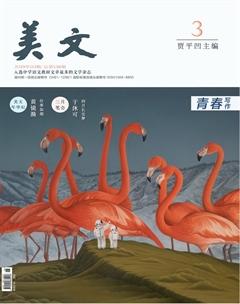醫為氣者
徐澤誠
雁鳴南飛,寒風乍起。徜徉在蘇軾“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豪邁之中;仰望月空,又見“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的愁緒;回憶亡妻,更有“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的柔情似水。盡管他仕途坎坷起伏,卻始終隨性曠達,樂觀開朗。
蘇軾是北宋時期著名的文人,一生事跡載于文獻者頗豐,詩詞文章更是千古流傳,然而鮮為人知的是他對中醫醫理也頗有研究。著名的《蘇學士方》便是他收集的中醫藥方。后來人們把蘇軾收集的醫方、藥方與沈括的《良方》合編成《蘇沈良方》,至今猶存。在我眼中,作為一個中醫愛好者的蘇軾,最能將“氣”之內涵體現得淋漓盡致。“重虛有實候,而大實有贏狀,差之毫厘,便有死生禍福之異。”他批評那些士大夫“秘新患而求診,以驗醫之能否,使索病于魚漠之中,辨虛實冷熱于疑似之間。”對待生命,蘇子可是認真的。
“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蘇軾一生屢遭貶滴,每到一地,他都收集驗方載于筆記雜記中。居黃州時,當地瘟疫流行,他將自己收集的秘方“圣散子”獻出來,救治病人。在惠州,看到當地村民燃蒼術熏蚊子,大表惋惜說:“此長生藥也,人以為易得,不復貴重。”還記得其《論菊》中描寫作為延年藥的菊花,《論茶》中他以茶漱口的口腔清潔方法。
東坡用菊和茶的清氣沖淡了人生的愁悶。在中國哲學里,“氣”是一個核心概念,甚至可以用來概括中國哲學的全部內涵,《內經》繼承和發展了先秦關于“氣”的一元論學說,并將其應用到醫學中來,逐漸形成了中醫學的氣學理論。
“非水谷,無以成形體之壯;非呼吸,無以行臟腑之氣。”“人一離腹時,便有此呼吸,……平人絕谷,七日而死者,以水谷俱盡,臟腑無所充養受氣也。然必待七日而死,未若呼吸絕而即死之速也。”(《醫旨緒余·原呼吸》)
“氣”仿佛一根纖繩,貫穿于中醫理論始終,統攝中醫實踐與經驗的全局。因此,中醫們幾乎都深諳“氣”之道。
不少人初識傅山,源自梁羽生的武俠小說《七劍下天山》,作者賦予傅山一派宗師的形象,他名滿天下,文武雙全,大智大勇,鮮有敗績,近乎完人:
“這些人中,有一個三綹長須、面色紅潤、儒冠儒服的老人……”
儒冠老人名叫傅青主,不但長于武功,而且在醫術上有精深造詣,極為精妙。
醫者仁術,傅青主以悲天憫人之心,體恤男權社會中的弱勢婦女的悲苦,開創婦科治療的一代風氣。傅氏女科的出現,是中醫史上劃時代的事情。
但我最佩服傅青主的,還是他的民族氣節。滿清入主中原后,作為一名有志氣的儒士,傅青主參與民間抗清復明運動,并因此被捕入獄,受到嚴刑拷打,但他“抗詞不屈,絕粒九日幾死,門人有以奇計救者得免”。康熙皇帝下詔舉行博學鴻詞科考試,欲以此網羅各地有名儒士。傅青主被迫到北京后,素聞才學的康熙帝免去了他考試的形式,直接賜他中書舍人。按慣例,這是要向皇帝磕頭謝恩的,但年邁的青主倒在地上,絕不磕頭,在那個專制權威壓死人的時代,這是難能可貴的氣概和傲骨。
傅青主的這種“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不向滿清皇權低頭的氣節,正是孟子“浩然之氣”的一脈相承。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一代一代的中醫將浩然之氣脈脈相傳,他們不會怒氣沖冠,也不會說千古流傳的氣話,更不會將氣化為愚忠一死了之。可能他們都是一個個面色紅潤髯須飄飄的老頭,可能他們只能醫病不能醫心,但是他們確是那些真正為人民解除痛苦,為人民謀福利的人。抱著“不為良相,則為良醫”的志氣,每一次將手指搭在脈上,感受氣的變化無常,每一次在病人吃過藥之后感受到氣的豐盈,都是讓他們繼續下去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