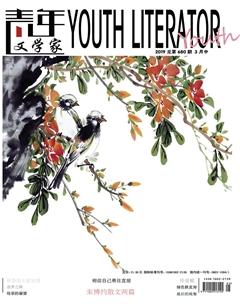淺談雅舍談吃
摘 要:《雅舍談吃》是梁先生的一本有關飲食文化的散文集子,在這本書中,梁先生就各種菜譜、飲食文化等進行了非常獨到的分析。讀來,一方面,閱讀這些介紹性的文章,梁先生對于誘人食物的描述,令人生津,饞涎欲滴;另一方面,也可見梁先生的生活態度和人生體味,可見匠心。
關鍵詞:《雅舍談吃》;梁實秋;美食;故鄉
作者簡介:徐真,南京林業大學人文院漢語言文學專業,指導老師:繆軍榮。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08-0-02
我想凡是世間所有之物,大多數都可以“雅”字冠之,至少這在文本上是數見不鮮的。但此雅非真雅也。我很喜歡那些質樸而又古拙的器物,一件別致的器物,若是被涂抹得濃艷之至便會趨向平庸。世上怕是遠遠不止一處雅舍,劉禹錫的陋室是一處,歸有光的項脊軒又是一處,但梁實秋筆下的雅舍,卻是獨一無二的絕景。
初中畢業后那個烈日炎炎的暑假,我才偶然在書架上欹斜的書堆里觸及到梁先生的文字,幸得梁先生一支生花妙筆,才將那形形色色的美食描繪的如此活色生香讓人垂涎欲滴,其實在都這本書之前,我常常愛大言不慚的以“吃貨”自居,但是在讀了這本書之后卻是萬萬不敢了。梁先生才是名副其實的“吃貨”,我充其量也只是個“饞貓”罷了。其實真正的“吃貨”全然不是毫無挑剔見啥吃啥,而是在品嘗之外細心研究食物背后的文化,追求的是吃到嘴的食物的品質,懂生活的人才懂得食之味。
所謂“君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吃文化向來都是中華文化篇章中不可磨滅的一頁,博大精深源遠流長,盡管歲月生命都在日漸消逝,惟有文化可以代代傳承。一國的吃,深刻地體現了一個民族和國家的文化。雖則,吃總被理解為是口腹之欲,幾乎在所有的文化中,欲望都有必要節制,食欲亦是。宋明理學的“格盡人欲”似乎讓人對于美味的追求變得不那么上得了臺面。在梁先生看來,“如果天理不包括美味的要求在內,上天生人,在舌頭上為什么要生那么多的味蕾?”對于嚴肅的人而言,這話可能漏洞頗多,玩的是一些小伎倆;然而對于老饕食客而言,這話,儼然可以成為饕餮客的圣經了!生命有限,吃一頓少一頓,自然是頓頓都不可辜負。
雖說梁先生的文章,確實將很多筆墨耗費在了食物之上,比如烤羊肉,炸丸子,爆雙脆之謂,但是,正如梁先生所言,“偶因懷鄉,談美味以寄興”。出生于北平的梁先生,借由這些北平的小吃珍饈聊表思想之情,溫馨的氛圍濃濃郁在其中。小吃如豆汁兒、酸梅湯、糖葫蘆,且“實在想念”,而對于所謂“大八件”“小八件”嗤之以鼻。說是“懷鄉”,更多的可能仍是思人。談到獅子頭,心中所思,是客死異鄉的蕭毅武先生;談及“冬筍炒肉絲”,那是“無上妙品”,但必須是“媽媽親自掌勺”;而真道及那些吃食,尤論及父母愛吃之物什,未及供養仍是梁先生之哀傷。幼年時和父母同吃,后與朋友同食,而今古人凋零不只有幾,縱觀全書談美味以寄興。他寫的《雅舍》最為動人之處,便是對故鄉深深的眷戀,是對那似水流年的追憶。
遠去的吆喝聲,逝去的鄉愁,揮之不去的是巷口飄香的美味,早已幻化成風悄然入夢來。同時,梁先生緬懷了一個逝去時代。例如東興樓,日寇盤踞之后,一代名館,后“名存實亡,不復當年手藝”。致美樓、厚德福、便宜坊……那些曾經的手藝,“全在掌勺的存乎一心”,有如“庖丁解牛,不僅是藝,而近于道”了。想想梁先生所謂名坊名齋,手藝不再,卻也值得感傷。食以寄興,也是梁先生的智慧。這本小書,介紹了民國年間北京城內各大樓肆招牌特色菜品,也有對家常飲食的追憶,大到參鮑翅宴,小到豆漿油條,無不涉獵。正陽樓的烤羊肉,肉片要切得飛薄,烤肉也不能用碳不能用柴,要松塔盈筐,敷在炭上,這樣的烤出來的肉才能松香濃郁;蟹要講究時節,七尖八團,先蓄在大缸里,澆雞蛋白催肥,吃的時候食客每人一個黃楊木制木槌木墊敲打,免牙咬手剝之勞。東興樓的爆肚仁,油爆、鹽爆、湯爆,各有妙處,妙處全在觸覺,雪白的肚仁襯上嫩綠香菜梗,嚼上去不軟不硬不韌而脆;法細膩,言語詼諧,民國情物風俗、飲食文化躍然紙上,害得我每次讀完都是垂涎三尺,恨不能生于民國,一品滋味,快意胃腑。在梁先生的《雅舍談吃》之后,不知道有多少談吃的書籍爭相模仿他的文風和邏輯,但是終究畫皮難畫骨,至今也鮮少有出右者,他的豁達瀟灑,那份真正的閑情雅致是旁的人萬萬學不來的。
《舌尖上的中國》的總導演陳曉卿表示最早就是梁先生的《雅舍談吃》迷住了他,他認為美食在作家的筆下早已有了超越它本身的概念,它更是一種文化底蘊的代表。《史記》有言,“王者以民人為天!而民人以食為天”,飲食男女,人之性也。無論是梁實秋先生還是汪曾祺先生,都是熱衷于吃并樂于鉆研吃的,這種吃想來不僅是為了滿足口腹之欲,更是為了感受其中的人生百味。梁老憶豆汁兒時談思鄉,談魚丸時感慨“如今高先生早已作古,空余舊事縈繞心頭”憶友,談“大菜”時表一片愛國之心……可見雅舍談吃,不只是談吃什么,怎么吃和誰吃,更重要的是這份藏于吃中的人情味。這感覺和讀汪曾祺那一句一句“好想再喝一碗茨菇湯,我想念家鄉的雪”,是一樣的情感。從細微處談浮生眾相,不矯揉造作,不堆砌辭藻,只是以情動人,簡練雋永,妙趣橫生,這樣的一本書,難道還不值得我們閱讀嗎/
翻開書,看到目錄上那一排排的菜名,真真把人的饞蟲都勾出來了。更有讀者感嘆:“這才是一個吃貨的自我修養啊!”特別是在深夜,看著書,更覺胃里的空虛,真是體會到書里不斷強調的“饞”。食物因為有了人的聯系,而充滿了人情味。想想以后,因為一道菜而憶起一個人,食物已不僅僅是食物,是感情的紐帶,另一端系著的是回憶中的人,也許是不在人世的人,再無機會共食一道菜,共飲一盅酒。這樣的食物是溫暖的,是別有滋味的,縱使再無機會一膏饞吻,我相信,那味道始終留香齒頰間。由于母親做得一手好菜,我打小口味也被養的刁鉆了些,深感在外求學的這兩年味蕾被外賣破壞了大半。二十出頭的年紀,我不敢自稱老饕,但是有幸嘗過數種美味,酸甜苦辣咸,每一樣都在刺激著味蕾勾動著回憶。似乎記憶中最好吃的東西,永遠是幼年時母親與外婆的家常菜,沒有什么珍貴的食材,做法也不是那么考究,但是那是我記憶中最好吃的東西。
食客有鴻儒、有白丁。鴻儒斯文,齊聚盛宴酒至微酡,興之所至擊案高歌;白丁暢快,血盆巨口吃得青筋暴露滿臉大汗,自食其力心里坦蕩,哪管吃相!似乎老一輩的人都很淳樸,為人處世講究個人情味。現在也有些傳承下來的百年老店,但是初心仍在嗎?信遠齋的酸梅湯,味濃而釅,爽口冰涼,酸甜適度,含在嘴里如品純醪。梁先生就問老板方法,老板回答得很巧妙:請您過來喝,別自己費事了。如果在當今,這有窺探秘法的嫌疑估計會被轟出去。時代變遷,現在這個時代,可以說是最好的時代,但也是最壞的時代,我們可吃的東西遠遠比梁先生生活的那個年代要豐富得多,打開美團,食物琳瑯滿目,我只愿意稱其為食物,而不是美食,因為我覺得真正的美食是用心烹飪制成的而不是那些速成的外賣。那些費工費時的自然饋贈再難尋覓,滿目所見皆是農藥,當然也不乏專供、特供我等草民不能奢求之物。
中華民族自古多難,所以少年老成。對吃的態度也異常嚴肅。孟子說:“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朱子語錄》說:“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學者須是革盡人欲,復盡天理,方始是學”。但是梁先生說:美味固是人欲,可人欲何曾有悖天理?如果天理不包括美味,那么上天生人,在舌頭上為什么要生那么多的味蕾?這個問題問的實在是妙極。
或許,口腹之欲的“欲”,皆“人欲”也,本也無高下之分。講究者,山珍海味仍無處下箸;困苦者,鍋盔加上凍豆腐粉絲熬白菜,吃得稀哩呼嚕,也可見其快樂。終是講究充分享受,或細嚼慢咽,或風卷殘云,“怡然自得”,才是樂事!人有口腹之欲, 其實是一種生活幸福的表現。最后借用梁先生的一句話收尾:《菜根譚》所謂“花看半開,酒飲微醺”的趣味,才是最令人低徊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