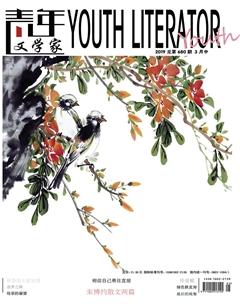淺析《貓》中的文化沙龍現象
摘 要:小說《貓》通過十九歲學生齊頤谷的視角觀察,描寫了抗日戰爭初期北平的一次文化沙龍聚會,寫出了20世紀30年代初北平高級知識分子的聚會方式。錢鐘書以文藝沙龍的形式,使這些知識分子集中登場,諷刺了他們的自私自利與虛偽卑劣,在極短的篇幅內濃縮了戰爭年代北平部分知識分子的真實生態,通過他們表達對于戰爭的態度,將貓的寓意與文化沙龍現象巧妙結合。
關鍵詞:文化沙龍;知識分子;《貓》;戰爭
作者簡介:賈子璇(1994-),女,漢族,內蒙古呼和浩特市人,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碩士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08-0-02
錢鐘書的短篇小說《貓》選自其小說集《人·獸·鬼》,首次發表于1946年創刊的《文藝復興》。其篇名“貓”對應的是小說集書名中的“獸”這一項,在書中所寫的序中指出:“不但人是安分守法的良民,獸是馴服的家畜,而且鬼并非沒有管束的野鬼。”[1]序言概括了四篇描寫各異的小說作品,并也指出了小說集命名的依據。短篇小說《貓》除了向我們展現了一只黑貓的形態之外,更多的是對戰時北平部分虛偽的知識分子進行了群體的展示。在《貓》中,錢鐘書憑借文藝沙龍這種特殊的聚會形式,通過描寫沙龍客人們對戰爭的討論,詼諧而辛辣地鞭撻了戰爭年代部分自私自利、道貌岸然的知識分子。
一、文化沙龍的起源
“文化沙龍”是一個泊來詞匯。沙龍的原意為房間中的客廳,起源于文藝復興的意大利,興盛于17、18世紀的法國巴黎,文藝沙龍是當時西歐上流社會的一種精英社交文化。經過精心挑選的社會各界名流聚集于貴婦人家中。他們志趣相投。沙龍匯聚了時代最顯赫的名士淑媛,社會的浮生萬象也可從中窺見一斑。[2]“沙龍”由一個場所最終演變成了在這個場所進行的一些品評時政,就一些問題發表建議的一種精英聚會,同時也是思想與興趣碰撞的一種文化現象。
最早把西式沙龍移植到中國的,是清末來華的洋人。后來教會大學的學生又把他流傳開來。由于當時中國無貴族,行政組織介入嚴重,因此沙龍最初只存在于極少數的特權階層,處于隱秘狀態,具有小圈子精英文化的特質。[2]文化沙龍傳入中國,隨著時代的演變他也在發生著改變,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具有不同的形式與話題,而其中最出名的要數二三十年代民國時期的文化沙龍聚會。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北平有一批留洋經歷的知識分子圈是最早流行中國式沙龍的起源地,梁思成與林徽因家的“星期六聚會”,亦稱太太的客廳,是當時名噪一時的沙龍。此外,同樣聞名的還有地安門慈慧殿朱光潛家的讀詩會。[2]
這兩個在當時名噪一時的文化沙龍聚集著不同學術圈的精英,是當時京派作家一種典型的聚合形態。他們通常沒有嚴格的組織和規則,沒有貫穿始終的核心刊物,卻以一種超越組織和小集團的形態將當時北平觀念相近的作家逐漸聚合起來。[3]談論的話題既有學理的深度又有文學的風采,對于當時30年代在北京發展的京派文學具有很大的影響和作用。
二、《貓》中的文化沙龍現象
文化沙龍雖然有著很大的自由空間,但同時他也有著固定的圈子與一定的形式。這種定期或不定期的聚會,不拘形式內容,自由靈活,完全是在思想和文化層面的交流與溝通。雖然聚會的方式各不相同,由一位才貌雙全的貴族女性主持,頗具近代以來西方文化沙龍的風格。[4]在《貓》的文本中,在下午時分在愛默家中舉行的這一場聚會就是一場典型的文化沙龍。作者多次用較長的篇幅直接或間接地點表明,愛默家中客廳里的并不是一次普通的茶會,而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流行于北平文人圈的文藝沙龍。
從文本中來看,“今天這種智識分子的聚會上,有女客也絕不會中看,只能襯出女主人的美貌……”[1]這種聚會的核心主持就是文中愛默這位女主人,而接下來在人數方面,錢鐘書又通過齊頤谷的眼來敘述:“假如頤谷是個多心眼的人,他該明白已到的客人和主人恰是十位,加上陳俠君便是十一位。”[1]通過文本中的這段話可以看出這場聚會的人數是固定的,而齊頤谷的加入也是因為與女主人有些許關系的緣故。在聚會的人陸陸續續到齊的時候,作者在這里又敘述了一種大家共同的內心活動:“他們對外賣弄跟李家如何交情,同時又不許任何人新跟李家有同等的交情。”[1]
通過上面的三段文本,可以清楚地看出《貓》中描繪的情景是一次典型的文化沙龍現象,有固定的人數,有固定的女主人來主持,甚至這種聚會具有一定的排外性,所以文中齊頤谷的慌張與寡語都是有依據的。從文本出發,借用文化沙龍這種特殊的聚會方式,在一定的篇幅內使得愛默周圍的一些知識分子集中登場,而最終又回到了錢鐘書擅長描寫的風格——知識分子的主題上,通過這樣一場文化沙龍,他們席間的夸夸而談,在極短的篇幅內濃縮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北平部分知識分子的真實生態。
三、《貓》中文化沙龍中的知識分子
《貓》中的文化沙龍以齊頤谷的視角來觀察,而其中的核心人物是愛默、李建侯夫婦。逐次登場的馬用中,袁友春,陸伯麟,鄭須溪,趙玉山等人,以及著墨更多的陳俠君都是參與這次聚會的人物。這場文化沙龍中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的身份與背景,他們都是當時的上層社會的人物,而其中有五人都有過留學的背景,他們自適應這樣一種貴族聚會的方式,并且在談吐的話題中間也有對于中國傳統與西洋文化的一些討論。
這種身份的復雜性,影響了他們對于戰爭的一些看法。他們在當時的北平安逸的生活,對于戰爭全然不知,也并未想到日本的一次次試探最終會使得大半個中國幾乎淪陷。而他們留洋的背景也會影響到他們對于當時中國國內情況的一些判斷與理解。這樣特殊的組成方式展現了當時這樣一批人對于戰爭和時政的看法。而通過作者的描寫可以看出在當時國內嚴峻的情況下,作者對于他們在客廳內事后諸葛的行為進行了辛辣的諷刺,尤其對親日派進行了強烈的諷刺。
文本中關于每個人對于戰爭態度的描寫,是這場文化沙龍的高潮。這其中分為兩派,有委曲求全的綏遠派,袁友春、馬用中、傅聚卿、陸伯麟認為:“我們只有忍耐著,暫時讓步。”[1]曹世昌:“我想咱們應當喚起國際的同情,先博得輿論的支持,對日本人無信義的行為加以制裁。”也有表面的支持派,鄭須溪:“戰爭也許正是民族精神的需要。”[1]從鄭須溪這個所謂的支持派的角度出發,他并未提及戰爭的殘酷性,或者對于日本的民族仇恨群情激奮的情感,而只是認為戰爭可以激起民族美德。而在當時的國內實際情況,市農工商各階層爆發了大規模的游行,包括躲到安逸鄉的齊頤谷的周圍,也爆發了大規模的學生運動。他們都躲在這一方客廳中,站在一個制高點上對于戰爭發表著無關痛癢的觀點,作者通過描寫他們的言語,對他們進行了諷刺。
在這幾位知識分子中,著墨最多的一個就是陳俠君。名字中帶著一個“俠”字,作者對他的角色定位希望他具有一定的俠客精神。實際上陳俠君也確實是這群人中比較特殊的一個,對于自己的身份階層,他大膽承認,對于戰爭的態度,他也是其中比較大膽和直接的一個:“我就受不了!只有打!”[1]而也只有他肯承認自己的懦弱與害怕:“我不肯,我不敢,而且我不能。我是懦夫,我怕炮火。”這樣的承認放在文本中,更加真實,也將自己的真性情展現了出來。
這場文化沙龍中的人物有十一人,而閱讀過后的感覺是對于大部分人的描寫都很平面化。《貓》并不著重對某一個人物的精心描繪,而是通過對知識分子群體的展示,表現貓樣的共性特質,同時又由于性格化語言的成功運用和對個人身世畫龍點睛的精巧展現,也不乏人物的個性特點。[5]
四、《貓》中文化沙龍的作用
小說以《貓》命名,最終向我們展示的是一次文化沙龍的聚會。這篇小說重要的時代背景就是抗日戰爭爆發初期。當時,北平市各界抗日救國運動正熱火朝天地展開。“‘九一八事變的消息于次日在北平各家報紙刊出……群情激憤,怒不可遏。大中小學校的學生和教師、市民、商人、工人和農民,一致奮起……”[5]北平市工界成立了抗日救國聯合會,北平廣大市民也展開了大規模抵制日貨的斗爭。
外界抗日救國的火熱氣氛同小說中沙龍茶會的閑適平靜形成了強烈對比。平淡與激憤使得當時的現狀與文本之間形成了一種巨大的張力。作者通過描寫虛偽的知識分子,將一片愛國之心和對國家的關注寄寓在小說之中。正如齊頤谷所說:“這些追求真、善、美的名人,本身也應有真、善、美的標志”,這些高級知識分子理應做出榜樣。而在北平市各界抗日救國運動盛行之時,他們卻不切實際地空談,主張讓步。
通過這場文化沙龍,最重要的作用是引出了文本的線索——貓。貓在這篇小說是一條線索,由為黑貓取名而進行的一次討論,將貓的寓意與這場文化沙龍中知識分子對于戰爭的態度結合到了一起,也有了知識分子“貓性”這樣的觀點。關于貓與知識分子的聯系,是借陳俠君之口表達出來的,陳俠君:“這并不矛盾。這正是中國人的傳統心理,也是貓的心理。……沒打的時候怕死,到打的時候就得忘了死。……只有小貓,他愈害怕態度愈兇。”[1]這一段話引出了小說關于以“貓”來命名的核心觀點,是這些知識分子的一個形象的概括。
但我并不認為這場文化沙龍中所有的人都具有貓性,這里的貓,雖說可能不會和危險殊死搏斗,也可能會轉身逃跑,然而這些都要基于這些知識分子有沒有像貓一樣,從一開始就有自己的基本態度,在文本中能做到這一點的只有陳俠君一人。陳俠君在文本中的特殊性代表著很多知識分子不敢表露的態度,他們即使在這樣一個逃避的空間中依舊不肯表達自己的態度實屬劣根之最。至少陳俠君是有態度的,他說出了他們這個階層的特殊性,一句“不肯不能不敢”,其中包含著許多矛盾復雜的情感。表明了他沒有辦法拋棄一切去投入到戰爭中,害怕戰爭,這是他的矛盾性,也是這場文化沙龍中很多知識分子的矛盾性。
五、結語
《貓》這篇小說以一個學生的視角,向我們展示了30年代北平城一次文化沙龍聚會,在特殊的歷史時期通過他們的談話折射出了當時的社會現狀,同時也通過對于戰爭無關痛癢的品評與當時國內群情激奮的現狀進行對比,對一部分虛偽逃避,只圖眼前安逸的知識分子進行了諷刺性描寫。這些所謂的“社會名流”表面上衣冠楚楚,實際上卻卑劣庸俗,自私虛榮,組成了一幅小型的“儒林群丑圖”。錢鐘書借沙龍客人之口對腐朽黑暗的社會進行了針砭,也透露出以陳俠君為代表的這樣一個階層的知識分子對于戰爭的矛盾心態,進而引發了關于“貓性”的探討。這是高級知識分子的真實生態,也是錢鍾書另一種關照現實的方式。
參考文獻:
[1]錢鐘書著.《人·獸·鬼》[M].北京三聯書店,2009,11.
[2]曹丹丹.法國沙龍文化在中國的引入與融合[J].法國研究,2013,2.
[3] 李蕾.京派作家的聚合形態考究——以沙龍為論述中心[J].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報,2009,4.
[4]胡志剛.1930年代北平的文化沙龍風波[J].歷史教學,2013,2.
[5]成漢昌,王美秀.“九一八”到“七七”北平人民的抗日救國運動[J].北京黨史,19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