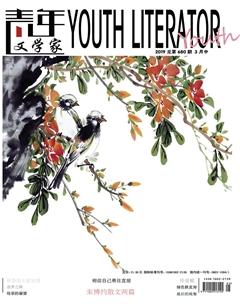論汪曾祺《異秉》的再版
摘 要:汪曾祺40年代創(chuàng)作的《異秉》經(jīng)過了80年代的重寫后,其內(nèi)涵意義發(fā)生改變。本文將重寫后的《異秉》與30年前的《異秉》作相應(yīng)的對比,發(fā)現(xiàn)再版后的《異秉》少了那份戲謔,卻多了一份對小人物生命狀態(tài)的同情,也是對舊時(shí)代生活美好的逝去的一首挽歌。
關(guān)鍵詞:汪曾祺;《異秉》
作者簡介:武詩蕊(1995.10-),女,遼寧省阜新市人,沈陽師范大學(xué)中國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專業(yè)碩士。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08-0-01
汪曾祺是一個(gè)跨越了新舊兩個(gè)時(shí)代的作家。少年時(shí)期故鄉(xiāng)深厚的文化滋養(yǎng)成為他一生創(chuàng)作的主要思想來源。1940年代開始,在自己的努力與老師沈從文先生的幫助下發(fā)表了《復(fù)仇》、《異秉》等小說。1949年,汪曾祺的第一本小說集《邂逅集》出版,收錄了創(chuàng)作初期的8篇小說。新中國成立后的近二十年,汪曾祺基本處于停筆階段。直到1979年,他才重新開始創(chuàng)作,在這之后創(chuàng)作的小說包括《黃油烙餅》、《受戒》等。汪曾祺也因?yàn)?980發(fā)表的《受戒》得到了文壇的肯定。其中《異秉》是比較特殊的一篇。在西南聯(lián)大就讀期間,汪曾祺曾寫過一篇小說名為《燈下》。但在沈從文先生的指導(dǎo)下,他對作品進(jìn)行了反復(fù)的修改,最終以《異秉》發(fā)表在1948年3月《文學(xué)雜志》第2卷第10期上。多年以來,汪曾祺的創(chuàng)作心態(tài)、人生感悟的變化使他突然升起了重寫《異秉》的創(chuàng)作熱情。30多年后,重寫后的《異秉》發(fā)表在了1981年的《雨花》雜志上。
再版后的《異秉》講述了手藝人王二以賣熏燒為生。在其他門店的生意每況愈下的時(shí)候,王二的生意卻越來越興旺。眾人談起王二的異秉,他答是“大小解分清”。聽眾中不得志的學(xué)徒聽后也跑到廁所尋他的“異秉”去了。這里汪曾祺將各色人物置身于他們自己的生活環(huán)境中,敘寫他們的勤勞樸實(shí)、喜怒哀樂與生存狀態(tài)。如小說中生意紅火的王二一整天都為了生意而忙碌。晚上閑暇時(shí)又會去保全堂店堂里的椅子上,聽人聊天。陳相公雖然人有些遲鈍,但他忙到十點(diǎn)多鐘,才可以睡覺。小說中的主人公似乎不是確定的,可以說是各色人物生存狀態(tài)的結(jié)合共同呈現(xiàn)了這個(gè)街景的一切。
40年代的《異秉》主要是圍繞王二展開的故事內(nèi)容。但是,除了王二外的其他人物都是朦朧的,如提到教蒙館的陸先生,除了他姓陸,是個(gè)教書的外我們對他一無所知。而80年代的《異秉》中凡是提到過的人物,如保全堂的管事、刀上、相公,甚至煮飯的老朱,都讓我們對他們有個(gè)相對清晰的認(rèn)識。如長相酷似托爾斯泰的食客張漢,是個(gè)百事通,“三教九流,醫(yī)卜星相,他全知道”[1]。小說中介紹到張漢,寄生蟲一樣的存在。王二卻是白手起家,是他的辛勤改變了自己的生存境遇。而王二的勞作過程,旱煙的炮制、聽書說書的場面、保全堂職位的劃分等都向我們展示了豐富的文化圖景。借助種種充滿畫面感的細(xì)節(jié)描述,我們仿佛置身于城市的上方俯視著街景的一切。
80年代的《異秉》對文化的書寫更為充實(shí)。他借助人物與風(fēng)俗的結(jié)合描繪了一幅人間風(fēng)俗畫。如汪曾祺講到了吃文化,對熏燒的方式和過程作了細(xì)致的描寫,包括過年推牌九,初一、十五給趙公元帥和神農(nóng)爺燒香等等。汪曾祺對所有的這些風(fēng)俗都進(jìn)行了細(xì)致的描寫,可以看出他對這些文化的了解之深,也是對整個(gè)舊時(shí)代社會的一種文化書寫。
走進(jìn)汪曾祺的小說,“他好像為讀者重新打開了生活的大門。大門內(nèi)的世界具有獨(dú)特的魅力,你能從中呼吸道新鮮的空氣,感到腳下踩著的土地,聽到人聲、鳥語和河流……你在這世界里,有一種親切的、熟悉的現(xiàn)實(shí)感,又有一種不曾劉一、不曾感覺到的美感。你感到又熟悉、又陌生。”[2]讓我們充斥在民間文化的氛圍里,重新認(rèn)識過去的現(xiàn)實(shí),同時(shí)也完成了我們對舊時(shí)代生活文化圖景的想象。
《異秉》的再次重寫,在汪曾祺的小說創(chuàng)作中意義特殊。雖然故事的內(nèi)容大致一樣,人物事件大致相同,但卻不是絕對的重復(fù)。30年來的時(shí)間過渡,作者的思想感情早已發(fā)生變化。這也賦予《異秉》以新的意義與思想上的升華。早期的《異秉》更多的是對小人物在市井中生活狀貌的描述。其中沒有任何感傷的情緒,反而還有對世俗生活的一種嘲謔。用80年代人的感情重寫后的《異秉》讓每個(gè)人物活在了真實(shí)之中,也讓我們看到了舊時(shí)代生活的美。同時(shí),小說對小人物的命運(yùn)卻多了一份同情。甚至可以說這篇小說是對舊時(shí)代美好的逝去的一首挽歌。
在汪曾祺眾多對舊時(shí)代生活描寫的作品中,充滿了對家鄉(xiāng)高郵真實(shí)生活的寫照。高郵城蘇北里下河附近小人物的日常勞作、自然景觀、兒時(shí)游戲等帶有濃郁地方特色的風(fēng)土人情被汪曾祺以詩性的語言記錄在他眾多的短篇小說中。甚至他小說中的人物有些是有原型的。如《徙》中的高北溟先生正是對他影響較大的國文老師;《珠子燈》中的孫小姐是封建禮教的犧牲品二伯母;《受戒》中的小英子和石橋和尚是他生活中出現(xiàn)過的小英子與鐵橋和尚。而《異秉》中的王二,在生活中也確有其人。高郵家鄉(xiāng)的王高山,他的父親就是王二的原型。汪曾祺的小說大多取材于兒時(shí)與少年時(shí)期的所見所聞、真人真事。作為一個(gè)跨時(shí)代過來的暮年老者,最易憶家鄉(xiāng)。而過去的家鄉(xiāng)對汪曾祺來說是一個(gè)珍貴而無可取代的存在,多年以來的人生漂泊與生活閱歷讓他對自己的家鄉(xiāng)懷有真摯的懷念與特殊的感情。他將對家鄉(xiāng)所有真切的感受付諸于文字之間,重新構(gòu)建了兒時(shí)與青少年時(shí)期家鄉(xiāng)那些平凡普通又珍貴的畫面,并將這些深入他骨髓的記憶呈現(xiàn)在我們的眼前。在展現(xiàn)他家鄉(xiāng)的同時(shí),也是舊時(shí)代生活畫面的映現(xiàn),甚至是整個(gè)中國文化史記憶的重現(xiàn)。
參考文獻(xiàn):
[1]季紅真:《汪曾祺小說》,浙江文藝出版社,2009年。
[2]程德培:《小說家的世界》,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