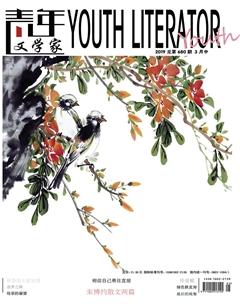《文心雕龍》對韓愈的影響
摘 要:《文心雕龍》作為南北朝時期著名的文論作品,對當世及后世文學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本文試從韓愈的書信體散文出發,探討《文心雕龍》對韓愈的影響,將從書信體本身,韓愈的文學觀,具體作品特點等三個方面進行研究。
關鍵詞:《文心雕龍》;韓愈;散文;書信體
作者簡介:楊萌(1994.8-),女,漢族,山西晉城人,西藏民族大學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中國古代文學。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08-0-02
一、《文心雕龍》中的書信
《文心雕龍》第二十五“書記”篇中,對“書”這一文體進行了詳細說明。開篇:大舜云“書用識哉!”點明,書是用來記錄的。接下來用揚雄的話“言,心聲也;書,心畫也。”,心底發出的是語言,心里發出的文字是書和記。首段對書這一體裁的適用方向進行了說明。第二段,從夏商周說起,用代表人物的典型作品說明一段時期的書信的發展情況,提到了子叔、敬叔、司馬遷、楊惲、揚雄等人的流傳后世的書信。
第三段總結書信體,總的來說,書信的作用在于將心中之意表達詳盡,用語言來紓解心中的郁結之氣,展現自己的風采,所以應該有條有理來使文氣不至于中斷,寬舒從容來使心情舒暢。分析書的分支:戰國之前,君臣的書信都稱“書”,秦漢后,臣對君稱“表奏”,如張敞對膠東王國太后的奏書,他的意義是美好和善的; 后漢后,“記”是記錄自己的意志,“箋”是表明自己的情意,如崔寔向公府上奏記,他想表現的是謙遜,黃香向江夏太守的奏箋,向后人示范了如何書寫謙恭,劉禎的箋記文辭瑰麗而且有意規勸,但由于曹丕《論文》沒有提到,所以大家都沒有注意到他的作品。箋記的體式,向高位者遞交就是奏表類,向同級或者下級交送就是書信類,所以箋這種體式,要恭敬而不拘謹恐懼,簡明而不傲然,應當語言清麗來展現作者的才華,文采華美來擴大他的影響,這才能說是做到了箋的本分。
剩下的幾段在說明記的各種形式,因本文主要研究書信方面的影響,暫不贅述。
可以說《文心雕龍》是劉勰對南北朝之前的多種文體做的整理,書信和筆記被他歸在一篇中說明。先追其淵源,以代表人物的作品來展現自己心目中的正統的寫法,再分述其支流,將一文體的產生、發展、作用、特征等都在短短的幾百字中表現出來。可見其對文學的了解程度。
二、《文心雕龍》與“不平則鳴”
韓愈作為中唐文學的中流砥柱,他提出的最為出名的文學主張是“不平則鳴”,這一學說是在《送孟東野序》中明確提出的“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1]。在《送孟東野序》中用物引人,用草木、水、金石這類本來無聲的事物,或有風聲或被加熱煮沸或被敲擊而有聲音,同時又選擇善鳴的器物來鳴,天的四時成為了鳥鳴迎春,雷鳴夏,蟲鳴秋,風鳴冬。引出物大多是在外物改變的情況下發聲,而人也是這樣,一旦內心受到外物的影響,就會自然發聲,其中又有極其擅長發聲的人,如咎陶、大禹、伊尹、周公、屈原、司馬相如、揚雄等人。但這里的“不平”不僅僅是不公平的意思,還含有不平靜的意思。大多有感情的世間萬物,只要內心有所感而不平靜,那么就會自覺發出聲音來表達,對情緒豐富的人類來說,更是如此,一旦有外物感觸,就會由內心生發出相應的感情,發于外形成文字,使人在讀文章過程中能夠感同身受。韓愈認為,文章不僅僅是對現實的客觀臨摹,而是傾注感情而成的心血。究其根本,“不平則鳴”是文學來源于內心感情的重要表述。
在《文心雕龍·明詩》篇中,劉勰指出“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在《神思》中也有“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于海”的語句。在此前,司馬遷曾言“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2]即著名的“發憤著書”說。其實這種文學來源于感情的說法早在《詩經》中就初露端倪,“我心傷悲,莫知我哀”所寫的傷悲就是一種情感,與“發憤”的“憤”所體現的都是感情;在《論語·陽貨》中有“詩可以怨”;屈原《九章·惜頌》中說“發憤以抒情”。可以看到“不平則鳴”這一學說是在不斷繼承前人學說基礎上改進而得出的。
在《送高閑上人序》中,寫張旭草書寫得好的訣竅為“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于心,必于草書焉發之”,“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于書”,這是韓愈給自己“不平則鳴”學說找的例證。而高閑上人是佛門中人,淡泊萬物,所以草書難以達到張旭的境界。
三、韓愈作品特點
《文心雕龍》對韓愈的影響不僅僅是在文學觀上,在創作上也有所影響。這一部分將以韓愈書信散文為例,探討韓愈對《文心雕龍》的繼承。
在《與李秘書論小功不稅書》中,韓愈與人探討小功不稅的禮制,全文三段,在前兩段不足三百字的文字里,有“而可乎?”“豈牽于外哉?”“豈有聞于新姑死哉?”“其可乎?”“果不追服乎?”“而傳注者失其宗乎?”六個或疑問或反問的句子。這幾個句子其實已經表明了韓愈的態度:小功不稅這一禮制應該有所改革。縱觀全文并沒有什么華麗的語言,只是以感情傾注全文。先說明了古禮的含義,又提出“禮沿人情,其不可不服也明也”,接著對比古時與唐的社會風氣的不同:古代人同一家族內的人都在同一國中,彼此聯系緊密,互相支撐,會有不追服的情況,(但是都有親人去世的悲痛感),是可以理解的。但唐代時,男子在外省出仕,女子出嫁,相距甚遠,又因家境窮苦,所以親人去世的訃告難以及時通知到,所以大部分人都選擇了不服小功禮。但是對君子來說,骨肉至親,為其死而悲痛,進而通過服小功禮來表現自己的悲痛是正常而且值得贊許的行為,怎么能因為外面規矩的束縛就選擇了放棄服禮。現在的人怎么能因為得知消息比較滯后就不再服制呢。內心悲痛,但卻服吉服,別人看到了都會疑惑。或許遵循的古禮并不是這個說不用追服的意思,而只是后人注時有誤也未可知。
全文以情相綴,正如《文心雕龍·情采》篇所說,“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后緯成,理定而后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情感構成了《與李秘書論小功不稅書》的經線,而質樸的道理言辭構成緯線,共同鑄成了這篇文章。全文語言簡練而感情真摯,正是“為情者要約而寫真”的絕對踐行作品。
《答尉遲生書》是非常簡短的一篇書信作品。開篇說明文章要有本質的內容,內容就像樹木的根“木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僅僅是四個短句,韓愈說出了他自己認可并踐行的文章之道,簡潔而可行,可見韓愈的“熔裁”之道,正如《文心雕龍·熔裁》所言“一意兩出,義之駢枝也;同辭重句,文之肬贅也”。語言扼要,非常簡練,是為“極略之體”。
可以說韓愈的所有作品都經過了熔裁,極富情采,并不單單只書信體。就其全部創作來看,他的“變體”戲謔文,也很有文采。就《毛穎傳》、《鱷魚文》、《送窮文》來說,本就是一種文學的流變,“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正是《文心雕龍·通變》的體現。韓愈吸收借鑒了前人的史傳文學傳統,但自己又創造性地將俳諧因素融入其中,將毛筆擬人化,為其立傳,語言詼諧,是謂“名理有常,體必資于故實;通變無方,數必酌于新聲”。《圬者王承福傳》也是其中的佼佼者,以前的史傳文學,只對帝王將相等地位極高或者是名聲極大的人立傳。
追根溯源,韓愈的散體文的出現本就是一種“通變”,在唐前,散體文其實一直存在不曾中斷,在西魏宇文泰等人,為了推廣敦樸化民的思想,提倡質樸的古文。在韓愈柳宗元之前,散體文的發展是沿著兩方面并進:寫作散體的逐漸增加;駢體文的改造變化。但直到韓柳,文體文風改革才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他將文風改革與政治改革結合在一起,“文以明道”明的是“仁義”之道,這其實和《文心雕龍·原道》所尊崇的“道”是一樣的。在駢體當道的時候能夠認識到散體的優點,并且將其繼承并發揚光大,不得不說是一種“通變”。
至于“比興”、“風骨”、“聲律”、“章句”、“附會”、“夸飾”等等文章創作論方面的具體要求,在韓愈的散文中都有顯示,就不一一具體說明。
注釋:
[1]韓愈:《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232頁。
[2]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華書局,1959年,第3300頁。
參考文獻:
[1]王元化.文心雕龍創作論[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02.
[2]韓愈撰,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Z].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2.
[3]周振甫.文心雕龍今譯[M].中華書局,2005.06.
[4]安之樂.文心雕龍在唐代的接受[D].寧夏大學,2015.
[5]羅宗強.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M].中華書局,201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