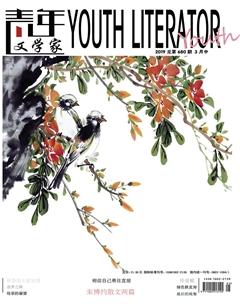孫逖詩中蜿蜒的路途
王芷晴
摘 要:孫逖祖籍山東柳城,唐開元二年始入越為官,在越地幾近二十年,越地實為其第二故鄉。孫逖才華橫溢,創作出眾,再者身處初唐轉盛唐時期,他的仕途一路順暢節節攀高,社會地位的提高以及所處環境的變化使得孫逖的詩風還是有所轉變的,早期的作品比較自由涵蓋了山水詩、詠史詩,后期重回中原地區任職更加傾向于創作應制詩。與越地的關系距離也在影響著詩人的創作。本論文選取詩人在越、離越共三首詩歌,在他的詞中我們去感受其所感,去探究其詩風轉變之原因。
關鍵詞:孫逖;詩風轉變;越地
指導老師:房瑞麗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08--01
一、在越興懷
越州地區自魏晉時期始就以其宜人的風景孕育了也吸引了大量的文人士大夫來此,鐘靈毓秀,使得長于中原的孫逖能夠親歷江南風物,在擔任山陰縣尉的三年間,孫逖遍覽越地名勝,在遠離中原故地的柔山媚水之間抒寫性情,寄寓感慨,[1]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他創作初期一系列的山水詩。再者追溯越地的文化歷史,王羲之、竹林七賢、謝靈運等流芳百世之人皆在此游歷,這是匯集人文薈萃和風景秀麗的福地。唐朝統一天下,久經離別動亂的社會逐漸趨于平靜但是,人們對時間的遷逝而引發的人世滄桑的感嘆卻從來沒有停止過。[2]孫逖是生于初唐,長于盛唐,在尚未弱冠之時已經遠離故土奔赴越州任職,一種感傷情調便在人杰地靈的越州生根發芽,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在孫逖前期的詩作中不少是以歷史作為客體來抒寫主體的情志,在越地,念越人,有所感發。
《登越州城》中詩人登高望遠,所見之景乃是越城被屏障一般的群山所環繞,映入眼簾的景色是滿目蒼翠欲滴,綠的十分鮮明格外生動。詩人遠眺,這城樓仿佛是一直延續到了天際,消失在澄明清澈的湖水之中,詩人再順勢描寫湖上之景。山風輕拂過修竹發出悅耳的音響,蒙蒙細雨滋潤著田間的作物。描繪了一幅多維度多方面的農作圖,最后兩句詩人由景入情。“登高”在眾多的詩歌作品中出現并且代表有一種獨特的意味,當詩人登高望遠時,看到這廣袤無邊的場景,想象著這片土地上承載著的文化內涵,思緒突然飄遠,由此具體將思緒定格在某個人某些事上。孫逖登越州樓,不禁感慨歷史的潮流推開了一群又一群的人,孫逖自己也學著魏晉時期的隱逸思想,利用工作之暇行隱逸之雅事。這是詩人對于自己品格以及追求的側面肯定,但自己與魏晉文人相較到底是相形見絀了,又不免感慨王羲之,像他一樣的英靈都已經離去了,孫逖眼前宏大的場景使他置于時間的長河之中感慨時間之流逝。
二、離越憂愁與入政
越地在詩人心目中有著獨特的位置,詩人在年少之時遠離故土來越地任職,并且在這里度過其人生的三年,越地已然成為了詩人的第二故鄉,以其獨特的人文風光以及山水好景給以孫逖以精神的寄托。離越之時的無限感慨也有對這片土地的感謝,離開所熟悉的環境而要去往一個未知的世界,詩人對于前路的擔憂之情也溢于言表。
西陵渡口,那停泊著船只的小小一隅卻是承載著太多情感的符號,有時會給人一種離別的惆悵之感,亦有迎接歸客的喜悅之情。千萬載來,竟有多少離別重逢在此地上演,有多少少女思婦在此望盡天際,有多少文人墨客在此揮墨寫詩……
《春日留別》中詩人夜訪西陵渡口,向遠處眺望,但是紹興地區的東山已經不在視線之內,滿目皆是西陵夜景,一望無際的江水,天上的孤月以及隨波晃動的月影,耳畔則是潮聲。如此廣闊宏大的場景下詩人獨自一人而立,孤獨之感、漂泊之感更為彰顯。“征帆遙從此中去”,明日清晨離開西陵渡口,車馬慢的古時,此番一別幾近永別,江南的山川美景詩人也許再也不能見到,眼前江南景的流逝以及記憶中江南景的終將流逝,可憐愁思,詩人之愁緒更是上了一層樓。
孫逖在開元五年在長安嶄露頭角,因政治需要以及盛唐文儒的自身需求以及自我價值的實現,在以詩歌創作作為應酬工具的文儒社交活動之中,孫逖的詩風開始有所改變。正當王維、孟浩然等詩壇前輩以及王昌齡、高適、李白等后起之秀以鮮明的主體精神和多元化的藝術實踐繼續高歌猛進,構建盛唐正音之時,孫邀的詩歌創作道路卻似乎與此背道而馳,主體性鮮明的作品驟然減少,日常應景之作成為孫逛詩歌創作的主要類型,程式化的創作手法和集團性的表現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孫逛早年山水詩歌中的個性風格和情感表現。[3]詞作中的山水詩以及詠懷詩數量減少,更多的是一些歌頌盛唐氣象以及國家統治,輔之以對和親政策的強烈反對,這些詩作大多善于用典,辭藻華麗優美,有著宮廷詩的氣質。
《同洛陽李少府觀永樂公主入藩》一詩表現唐玄宗時期東平王之外甥女楊氏被封“永樂公主”,被嫁于契丹王。詩人用短短的二十字極盡全力的表現邊疆之地之荒涼與永樂公主之美色,一片肅殺之景,即使是春天的到來也給人一種毫無新意的感覺。大唐的美人兒降臨在這片荒涼的土地之上,龍塞(契丹王的居住地)才開始有了春天的跡象。縱觀孫逖的應制詩和政治詩我們可以窺探出詩人對于和親政策的極力反對,五言詩的詞不達意的缺點也因此顯現,此詩暗含詩人對于和親政策的不滿以及對于和親女子的憐惜之情,使人深刻認識到和親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邊界問題。前人黃周星曾說“龍塞春則春矣,毋乃難為美人乎”,唐汝溝也認為“以天上美人入無花草之地,果能使龍塞生春乎痛惜之情,見于言外”。從這兩個角度來看,唐朝的和親政策的弊端可見一斑。
由以上三點我們可以從孫逖的創作作品及其各個時期的詩風來看,他的詩歌作品中蜿蜒著一條路途,這是他的人生追求之路,情感之路以及詩風變化之路。
注釋:
[1]轉引自歐陽明亮、鄭莉.《唐代詩人孫逖與他的<宿云門寺閣>》.《古典文學知識》;2009年第2期(總第143期)。
[2]轉引自封向陽.孫逖及其詩歌研究.河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0601。
[3]轉引自歐陽明亮.《孫逖詩歌研究》.華東師范大學碩士學位畢業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