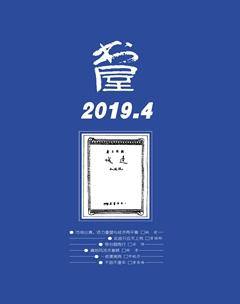《水澄劉氏家譜》序述略
曹曄
族譜與譜牒學是伴隨著宗法制度而生的產物,是我國地方文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圖書館、檔案館等機構所藏史料的一大來源。早在《史記·三代世表》中,司馬遷就寫道:“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諜終始五德之傳。”這說明譜牒資料具有存史價值和稽考信息的功能,能夠反映一族一姓的世系傳承、價值標準、生活習慣等方面的情況。在傳統中國社會里,出于敬宗收族的目的,地方上盛行著修撰族譜、修建家廟、開展族會等風氣。到了民國時期,在浙江紹興縣,當地一些望族仍然進行著族譜重修活動。其中,由劉應桂、劉錕鼐負責纂修的民國二十二年(1933)紹興廣文印書館鉛印本《水澄劉氏家譜》收錄了政界要人馮學書的一篇譜序。馮學書,浙江紹興人,曾擔任袁世凱大總統府秘書廳機要秘書、四川省巡按使公署政務廳廳長、浙江省政府政務廳長等職。今將序文移錄如下,加以標點整理,并對相關問題略作考述:
《水澄劉氏家譜》序
馮學書
自民族主義之標識為舉世所推崇,于是家族制度與宗族制度幾有不能存在之勢。其果狹隘而不適于用耶?余曰:否。一國之大集合,數萬萬之民眾,一心一德,群策群力,以圖自立,則其國必強。雖然,民眾至夥,渙若散沙,驟言集合,談何容易!不知此數萬萬之民族乃數千百萬之家族與宗族所構成。吾國數千年來社會習慣對于家族與宗族之觀念至深極固,且富有團結力。因勢而利導之,本其固有之團結力,以謀全國民族之大結合,事半功倍。吾知其必大有造于國家也。乃者舊日之禮教,不足以維系人心,而貌為新文化者,甚至掘其本根,父子不相顧,兄弟不相問,等家人于陌路,視同姓若秦越,無家族無宗族,遑言民族。邪詞陂行,熒惑青年。此可為世道憂者也。《尚書》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協和萬邦,言德之所,由親而疏,由近而遠也。其果狹隘而不適于用耶?伯貞內兄,夙承詩禮之訓,知親親之道不可廢,又慮詭僻者之足以惑世而迷俗也,毅然以修輯宗譜為己任,并得諸昆季之襄助,不期年而告成。其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歟。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癸酉仲冬
前浙江省公署政務廳廳長代行省長事
簡任金衢嚴道道尹門下裔孫婿馮學書鞠躬謹序
水澄劉氏先世本為廬陵人,到了元大德中始遷紹興城區的水澄巷。自明代以來,陸續有族人對族譜進行了不同規模的修訂;較大規模的修纂活動主要發生在崇禎年間,由族賢劉宗周(1578—1645)主持,形成了較為完備的族譜體例。入清以來,該宗族又在此基礎上對族譜進行了多次增修。目前存世的主要有劉大申等續修的乾隆忠樂堂刻本、劉瀚重修的光緒二十八年(1902)刻本等。
劉應桂、劉錕鼐生活的年代,正是受到五四運動洗禮的時期,中國社會掀起了批判宗法制度的熱潮。著名社會學家馮爾康在談到二十世紀中國社會各界對于家族觀和家族活動的看法時,認為其中的負面看法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家族主義是封建專制的基礎;二是家本位壓制個人,無自由、平等與人格;三是家族共財養成了個人的依賴性,缺乏創造力,使生產和社會不能進步;四是消除宗族家族,促使中國成為近代社會的國家。正是這些對傳統國故不那么友好、甚至抱有敵意的態度,促成了社會上一些劇烈的倒退現象的發生。馮學書在譜序中指出,“民族主義”的興起使原本為封建統治基石的“家族制度與宗族制度”成為“洪水猛獸”。他犀利地抨擊了一些“貌為新文化者”“掘其本根,父子不相顧,兄弟不相問”,將自家人、族人視為陌生人的反常行為,認為這是“詭僻者”、“惑世而迷俗”使然。
面對這樣一種時代的大趨勢,民國時期又出現了一股與之抗衡的潛流,即陽明心學在民國時期的復興。王陽明,浙江余姚人,明代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思想家。他是陽明心學的發明者。對于王陽明的德性、學識的希冀和繼承,在紹興的知識群體中表現得尤其明顯。從學說繼承來看,晚明水澄劉氏族賢劉宗周講學蕺山,著書立說,開壇授徒,闡揚王陽明的良知學說。這種濃烈的陽明情結,也體現在民國紹興知識群體身上。錢明先生指出,當時紹興的泰斗級人物蔡元培、馬一浮等,都對陽明精神進行了提煉與升華,形成了各自獨特的陽明學觀。他們不僅在思想上有所承繼,也積極推動鄉邦文化的建設。其中,馬一浮、馮學書等鄉賢,還曾于1921年倡議修復紹興縣文廟。
盡管民國時期的修譜活動在反傳統的熱潮中看來是格格不入的,但卻得到了紹興鄉賢們的支持。不惟政要人士馮學書欣然作序,蔡元培亦為該家譜題詞。蔡元培,字鶴卿,一字仲申,號孑民,浙江紹興人,近代著名的教育家、革命家和政治家。有研究表明,他在民國時期曾應邀為紹興當地的張川胡氏、車家浦陳氏等數個宗族撰寫序跋題記。在蔡元培看來,家族組織是培養圣賢的搖籃,他將氏族之譜與民族之歷史作比較,認為兩者都能“推見特性”,圣哲的培養離不開“傳誦之家訓,普守之規條”。同樣,馮學書在譜序中亦強調以“親親之道”為核心的家族制度與宗族制度能夠起到凝聚民心、謀求“全國民族之大結合”的效果。傳統倫理道德中的忠、信、孝、悌等觀念,能夠通過血親組織進行傳遞,培養國人以禮來待人接物,以增加國民之間的凝聚力與責任感。
綜上所述,無論是北洋遺老馮學書,還是“新文化運動之父”蔡元培,均將族譜之功能和意義提升到實現民族主義的高度。他們對中華民族文化傳統之一的族譜纂修及其功能,在思想上是認同的,并在行動上予以支持,體現出了這批趨新的權重人物對于傳統文化的自信。正如馮學書所言,“數萬萬之民族乃數千百萬之家族與宗族所構成”。民族國家的國民依然出自無數個家族與宗族,如何正確理解譜牒資料所反映的先賢義理,將民族國家的出路問題與家族組織的教育與功能結合起來思考,既是當時一批重視傳統文化的人士所倡導的內容,至今也依然是一個歷久彌新的時代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