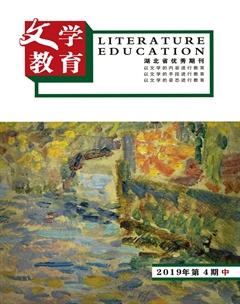莫言文學作品中的狂歡與怪誕
何等
內容摘要:作為第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作家,當前有不少學者在探討莫言文學和諾獎精神的相通之處。筆者以為,除了魔幻現實主義題材,其文學創作的語言特色同樣是成就諾獎的重要因素。在《透明的紅蘿卜》和《紅高粱家族》中,狂歡式的色彩描寫和怪誕的比喻運用使莫言成為文學創作中獨特的“這一個”。
關鍵詞:莫言小說 諾獎精神 語言特色 《透明的紅蘿卜》 《紅高粱家族》
“中國作家何時能摘得諾貝爾文學獎桂冠”,這個每年諾獎前后轟炸網絡的話題,在莫言獲得此獎后,轉化為了“莫言為什么會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他的頒獎詞中寫到,小說中的“高密東北鄉體現了中國的民間故事和歷史。很少的旅程能超越這些故事和歷史進入一個這樣的國度,那里驢子和豬的叫囂淹沒了人的聲音,愛與邪惡呈現了超自然的比例。”很多人因此認為,莫言是用他苦難暴力式的敘事和對中國鄉土荒誕野蠻環境的赤裸展現,抓住了諾獎評審者的眼球。筆者認為,除了魔幻現實主義的題材,其文學語言風格也有獨到之處。為此,筆者從莫言的兩部代表作——《透明的紅蘿卜》和《紅高粱家族》入手,從語言角度分析莫言作品中獨特的“這一個”。
一.狂歡式的色彩世界
莫言對顏色有著強烈的敏感和高超的把控力。《紅高粱家族》中,紅色是高密東北鄉高粱地的顏色,也是整部小說的主題色。小說開頭就寫到,“八月深秋,無邊無際的高粱紅成洸洋的血海”。紅高粱隨風狂舞,同時紅色作為鮮血的顏色,浸透著抗日兒女腳下的土地。“我奶奶”戴鳳蓮的傳奇人生,離不開紅色的高粱地,她和“我爺爺”余占鰲在高粱地的野合,為高密東北鄉的歷史“抹了一道酥紅”,開啟了她埋藏在內心深處渴望自由和無畏的天性。因此才有勇氣在官府和土匪之間斡旋,在支援抗日時挺身而出,最后犧牲在她最愛的高粱地上。高粱在一個瀕死之人的眼里不再是紅色,而是“紅紅綠綠,白白黑黑,藍藍綠綠”,如此有沖擊力的顏色象征著戴鳳蓮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和轟轟烈烈的一生。
莫言還擅長運用對比度高和濃墨重彩的顏色進行對比鋪陳,形成奇詭絢麗的畫面。《透明的紅蘿卜》寫小石匠的外貌,“小石匠長得很瀟灑,眉毛黑黑的,牙齒是白的,一白一黑,襯托得滿面英姿”;寫他和小鐵匠打架,“一白一黑兩個身體又扭在一起”。主觀化的渲染,構造了情緒豐滿的場景。在描寫黑孩幻想紅蘿卜時,寫鐵砧子“泛著青幽幽藍幽幽的光”,寫紅蘿卜“線條流暢優美,從美麗的弧線上泛出一圈金色的光芒。光芒有長有短,長的如麥芒,短的如睫毛,全是金色”,藍色、青色和金色的交織相映,傳達出黑孩在饑餓中對幸福的朦朧憧憬,隱含著作者對他的人道主義關懷。
二.怪誕的比喻運用
莫言擅長在行文中靈活使用各種怪誕比喻。《紅高粱家族》寫羅漢大爺被日本人關在柵欄里,他聽見“有人往柵欄邊角上那個鐵皮水桶里撒尿,尿打桶壁如珠落玉盤”。把“尿打桶壁”這種聽來并不雅的聲音,比作古代詩歌里形容琵琶聲的“大珠小珠落玉盤”,突出羅漢大爺在緊張壓抑的氣氛下仍能感受到一絲生機,讀來有一種雅俗錯位的不適感。莫言的暴力想象也讓人在閱讀中難以忘懷,如《透明的紅蘿卜》寫黑孩被小鐵匠欺負,“感到有一個帶棱角的巴掌在自己頭皮上扇過去,緊接著聽到一個很脆的響,象在地上摔死一只青蛙”;寫他被后娘打時“打屁股的聲音好象在很遠的地方有人用棍子抽一麻袋棉花”;寫他被燙的傷疤“紫疤象一只古怪的眼睛盯著自己”。黑孩受暴力凌虐的各種場景,轉化為怪誕的抒情意象,形象地寫出了黑孩在對待外界傷害時強大的內化和隱忍。讓人在虛實變幻中,體會到超乎人類生理極限的感官世界,無法捕捉的陌生感和恐懼油然而生。
莫言還熱衷于把事物比喻成吃的食物。《紅高粱家族》里寫戴鳳蓮出嫁時“兩滴高粱米粒般晶瑩微紅的細小淚珠跳出奶奶的睫毛”,細膩生動,仿佛淚珠也帶上了熱騰騰的米飯香。《透明的紅蘿卜》寫老鐵匠“臉色象炒焦了的小麥,鼻子尖象顆熟透了的山楂”,這是對小說所強調的饑餓主題的體現,而莫言作為饑餓年代的親歷者,將自己經歷過的情感融入小說創作中,可以說他的語言文字就是他本人情感世界的展現。
總之,莫言獲獎是對中國當代文學成就和價值的鼓舞。我們手握這個獎項,應當更有底氣重視和發展當代文學,在探索諾獎精神和莫言作品語言特色的關聯中,尋找中國文學“走出去”的一些路徑。
參考文獻
1.莫言.紅高粱家族[M].上海文藝出版社,2008
2.莫言.透明的紅蘿卜[J].中國作家,2012(11):4-23.
3.李秀林.試述莫言小說的語言特點[J].集寧師范學院學報,2012(3):32-35
4.曠新年.莫言的《紅高粱》與“新歷史小說”[J].杭州師范學院學報,2005(4):96-101.
5.喬宇.暴力的溫度與詩意——莫言小說《透明的紅蘿卜》中的暴力敘事淺析[J].名作欣賞,2018(8):104-106
6.李建軍.直議莫言與諾獎[J].文學自由談,2013(1):87-92.
(作者單位:浙江工業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