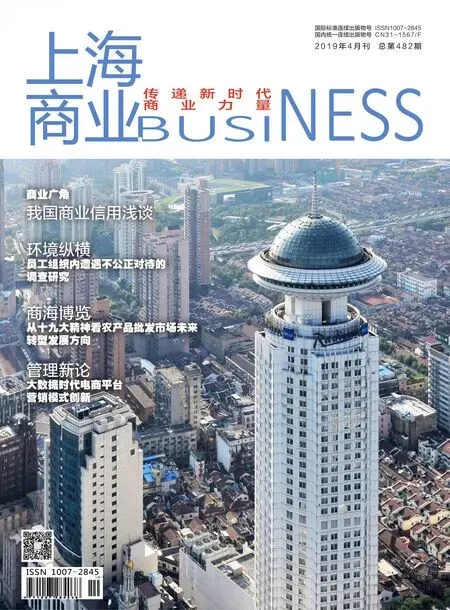工作性質(zhì)內(nèi)部行政行為的外化和可訴性探析
文 / 王 琳 許燦英
一、判決引發(fā)的問題

“寧波市鎮(zhèn)海百斗再生資源有限公司訴寧波市鎮(zhèn)海區(qū)人民政府安監(jiān)行政批準(zhǔn)案”中,兩審法院裁判結(jié)果相去甚遠(yuǎn)。一審法院認(rèn)為被訴批復(fù)并未實質(zhì)影響原告的權(quán)利義務(wù),由此駁回原告的起訴;二審法院認(rèn)為被訴批復(fù)對上訴人寧波市鎮(zhèn)海百斗再生資源有限公司具有直接強(qiáng)制力,實際影響上訴人的權(quán)利義務(wù),屬于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該案是典型的內(nèi)部行為可訴性與否的案件,但相同案情下法院對于內(nèi)部行為可訴性判定不一,類似的情況其實并不少見。
為什么法院對同一工作性質(zhì)內(nèi)部行政行為(以下簡稱“內(nèi)部行政行為”)可訴性與否審理結(jié)果截然相反?歸根究底法律規(guī)范的模糊化占絕大因素,直接導(dǎo)致現(xiàn)實當(dāng)中案件處理的不確定性。
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印發(fā)《關(guān)于進(jìn)一步保護(hù)和規(guī)范當(dāng)事人依法行使行政訴權(quán)的若干意見》的通知第十二條規(guī)定,如果層級監(jiān)督行為和內(nèi)部指示行為設(shè)定或者實質(zhì)影響當(dāng)事人的權(quán)利義務(wù),人民法院應(yīng)當(dāng)予以立案。但是該條更傾向于是《行政訴訟法司法解釋》第一條兜底條款的翻版,進(jìn)步點在于明確指出內(nèi)部行為可能具備可訴性,但卻僅規(guī)定層級監(jiān)督行為和內(nèi)部指示行為,其他類型內(nèi)部行為的可訴性不予置否,并且內(nèi)部行為的可訴性需要具備要素依舊未明確。
盡管2000年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1998)行終字第10號行政判決對內(nèi)部行政行為外部化的規(guī)則進(jìn)行明確闡釋,2013年以指導(dǎo)案例22號《魏永高、陳守志訴來安縣人民政府收回土地使用權(quán)批復(fù)案》(以下簡稱“魏永高案”)再次答復(fù)該問題,重申這一規(guī)則。但是,仍存在不容忽視的問題。因此,在行政相對人起訴內(nèi)部行政行為糾紛頻發(fā)的今天,有必要進(jìn)一步深入探討內(nèi)部行為外化模式,同時釋明其具體可訴性標(biāo)準(zhǔn)。
二、工作性質(zhì)內(nèi)部行政行為可訴性標(biāo)準(zhǔn)分析
通過整合分析現(xiàn)有司法案件,可以得出內(nèi)部行為外化而具備可訴性時需兼具以下要素:
(一)內(nèi)容要件:權(quán)利義務(wù)指向明確、具體
在認(rèn)定涉案內(nèi)部行為具備可訴性的案件中,行政行為的內(nèi)容均具有權(quán)利義務(wù)的指向性。如“陳永華不服建湖縣人民政府專題會議紀(jì)要案”中,法院認(rèn)定“本案建湖縣政府第32號會議紀(jì)要針對特定的對象,是可訴的具體行政行為,陳永華與被訴具體行政行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關(guān)系。”重點強(qiáng)調(diào)行為內(nèi)容權(quán)利義務(wù)的指向性。相反地,認(rèn)為涉案內(nèi)部行政行為沒有外化的案件,如“張運(yùn)福等與開封市人民政府會議紀(jì)要行政糾紛再審案”中,法院認(rèn)為“《會議紀(jì)要》所作出的為2010-58號宗地建設(shè)項目頒發(fā)土地使用權(quán)證,啟動規(guī)劃、住建、環(huán)保、人防、消防等涉及建設(shè)項目的備案工作以及對項目建設(shè)單位免于行政處罰的決定,并不是針對張運(yùn)福、楊開蘭、劉子榮的國有土地使用權(quán),也未對其合法權(quán)益產(chǎn)生明顯實際影響”。分析以上正反方面表述,可見權(quán)利義務(wù)的指向性直接關(guān)系著內(nèi)部行政行為外化的判定,缺少這一關(guān)鍵要件,內(nèi)部行為就不存在“外化”的前提要件。
(二)形式要件:相對人通過合法途徑知悉
首先,形式要件強(qiáng)調(diào)的應(yīng)當(dāng)是“相對人的知悉”而非送達(dá)的方式,送達(dá)方式可以多種多樣,例如“魏永高案”中原土地使用權(quán)人通過申請政府信息公開知道該批復(fù)的內(nèi)容;“延安宏盛建筑工程有限責(zé)任公司不服延安市安全生產(chǎn)監(jiān)督管理局生產(chǎn)責(zé)任事故批復(fù)案”[3]中,上訴人延安市安監(jiān)局并未正式向被上訴人宏盛公司送達(dá),而是事故調(diào)查成員單位之一的子長縣監(jiān)察局將批復(fù)內(nèi)容以談話和復(fù)印件方式告知宏盛公司,由此外化批復(fù)的內(nèi)容。由此說明送達(dá)的主體除了內(nèi)部機(jī)關(guān)本身還可以是外部機(jī)關(guān);其次,相對人必須通過合法途徑知悉,即內(nèi)部行為外化應(yīng)是依職權(quán)的外化。“任何通過竊取、私下打探、偷聽等不正當(dāng)途徑獲取內(nèi)部行為的信息,都不應(yīng)當(dāng)被認(rèn)定為內(nèi)部部行為的外化。”[4]主要有兩點緣由,其一就是防范作出內(nèi)部行為的程序被干擾。當(dāng)相對人通過不正當(dāng)途徑知悉自己權(quán)益有減損可能時,其極易通過各種途徑去試圖改變結(jié)果,導(dǎo)致本來無意對外發(fā)生法律效果的內(nèi)部行為被干擾。其二就是倘若認(rèn)可這樣的外化方式,不僅不尊重內(nèi)部機(jī)關(guān)的意思表示,還會極大打擊行政積極性,內(nèi)部機(jī)關(guān)可能會為避免被訴而盡量不作出批復(fù)、批準(zhǔn)等文件。
(三)實質(zhì)要件:權(quán)利義務(wù)產(chǎn)生直接實際影響
刪減權(quán)利、增加義務(wù)應(yīng)是權(quán)利義務(wù)產(chǎn)生直接實際影響的具體判斷標(biāo)準(zhǔn)。行政訴訟法解釋第1條第6項規(guī)定,行為沒有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權(quán)利義務(wù)產(chǎn)生實際影響的,不屬于人民法院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由該兜底條款可見行為對相對人實際影響的有無決定其可訴性的與否。結(jié)合收集的案例分析,實際影響的判斷可以從內(nèi)部行為做出的文件內(nèi)容上入手,分析其是否刪減相對人的權(quán)利,或者給相對人增設(shè)新的義務(wù)。“沈均等與杭州市國土資源局蕭山分局等批準(zhǔn)上訴案”中,法院裁判“案涉拆遷方案系拆遷人申請集體土地房屋拆遷許可證必須提交的文件之一,蕭山國土分局作為許可機(jī)關(guān)對拆遷方案等材料的審核系作出拆遷許可前的準(zhǔn)備性行為,并未設(shè)置新的權(quán)利義務(wù)。本案中,蕭山國土分局對新街街道提交的拆遷方案等文件審查后頒發(fā)蕭土資拆許字(2010)第12號《房屋拆遷許可證》,新街街道方可實施拆遷,故對沈均、沈關(guān)木權(quán)利義務(wù)產(chǎn)生實際影響的是準(zhǔn)予拆遷許可的行為而非對拆遷方案的審核。綜上,沈均、沈關(guān)木的起訴不屬于人民法院行政訴訟受案范圍,依法應(yīng)予以駁回。”可見新增義務(wù)或者刪減權(quán)利都是法院認(rèn)定實際影響的具體基準(zhǔn)。
在司法實踐當(dāng)中,有些法院會強(qiáng)調(diào)實際影響的“直接性”。 正如“趙穩(wěn)穩(wěn)等與西安市城中村(棚戶區(qū))改造辦公室批準(zhǔn)上訴案”中,法院說理部分談及“本案中,《西安市城中村(棚戶區(qū))改造辦公室關(guān)于雁塔區(qū)北石橋村城中村改造方案的批復(fù)》系市棚改辦對下級機(jī)關(guān)請示的答復(fù),僅針對下級機(jī)關(guān),屬于行政機(jī)關(guān)內(nèi)部的行政行為,對趙穩(wěn)穩(wěn)、王東軍的權(quán)利義務(wù)不產(chǎn)生實際的影響。而在具體的實施中,實施主體才會根據(jù)相關(guān)規(guī)定和《批復(fù)》,就具體的事項作出相應(yīng)具體的行政行為,該具體行政行為才對當(dāng)事人的權(quán)利義務(wù)產(chǎn)生實際的影響,具體的實施行為才具有可訴性。綜上,該《批復(fù)》不具有可訴性,趙穩(wěn)穩(wěn)、王東軍的起訴不屬于法院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
(四)三要件間的內(nèi)在聯(lián)系
在逐一分析內(nèi)部行為外化的各個要素基礎(chǔ)上,有必要進(jìn)一步探究三個要素之間的關(guān)系,以更好的適用于內(nèi)部行為可訴性的判斷。分析三個要件的內(nèi)在邏輯應(yīng)當(dāng)是:首先,內(nèi)容要件是內(nèi)部行為外化的先決條件,只有內(nèi)部行為有涉及到具體的相對人和事,才有進(jìn)一步探討外化的必要;其次,形式要件是內(nèi)部行為外化的輔助性條件。僅部分案件涉及送達(dá)問題,其中“鄭素華等不服成都市武侯區(qū)人民政府國土行政批復(fù)案”裁判中提及“雖然是行政機(jī)關(guān)就行政事項作出的內(nèi)部審批行為,該批復(fù)也并未向原告送達(dá),但該批復(fù)實際對原告的相關(guān)利益產(chǎn)生影響,因而是可訴的行政行為,原告對此批復(fù)提起行政訴訟符合相關(guān)法律規(guī)定。”從否定可訴性案例看,“張召久等與臺前縣人民政府等行政批復(fù)行政糾紛再審案”提及“該批復(fù)雖然通過政府信息公開的形式為再審申請人所知悉,但并未改變其系內(nèi)部行政行為的性質(zhì)。”由此可見,相對人知悉的與否并不必然導(dǎo)致內(nèi)部行為外化的有無,相對人知悉但內(nèi)部行為可能依舊是內(nèi)部行為,相對人不知悉但內(nèi)部行為卻可能外化;最后,實質(zhì)要件是內(nèi)部行為外化的必要不充分條件。在判斷內(nèi)容要件和形式要件的基礎(chǔ)上,要對內(nèi)部行為是否實際影響相對人權(quán)益進(jìn)行實質(zhì)判斷,針對相對人且對其有實際影響則可認(rèn)定內(nèi)部行為的外化,法院應(yīng)當(dāng)受理該類案件。
三、結(jié)論
內(nèi)部行為的外化是個老生常談的問題,但在當(dāng)前行政訴訟受案范圍不斷擴(kuò)張,司法案例裁判標(biāo)準(zhǔn)依舊模糊不定背景下,該問題有必要重新明確。只有內(nèi)部行為有涉及到具體的相對人和事,相對人通過合法途徑知悉被刪減權(quán)利或增加義務(wù),才有可能發(fā)生內(nèi)部行為外化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