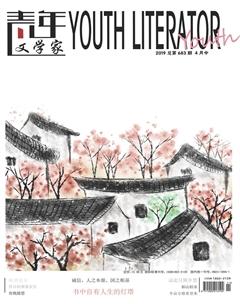唐昭宗乾寧元年省試《止戈為武賦》的現實意蘊
孫嘉明
摘? 要:為宦官擁立而獲承丕構的唐昭宗,氣質雄俊,好文重儒,即位之初希冀一改懿、僖兩朝朝政之頹勢,加強中央集權。通過對于唐昭宗乾寧元年省試《止戈為武賦》及相關史料的分析,可以一窺乾寧初年風云變幻的社會現實。
關鍵詞:唐昭宗;省試賦;現實意蘊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11-0-02
賦作為唐代科舉考試中一種重要的應試文體,備受主考官和應試士人的重視,《舊唐書》載:“非以辭賦登科者,莫得進用”。[1]洪邁《容齋續筆》載:“唐以賦取士”。[2]唐代省試賦的題目多由“所司”所命,且試賦命題往往有所本,多出自儒經、史傳以及道家經典。此外,試賦還經常限韻,而所限韻和賦題往往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是對于賦題的概括與闡釋。除去因故停貢舉之年,唐代每年省試通常于正月舉行,因此省試賦的命題有時會反映出國家前一年以及之前一段時期的重大社會現實,故“題目的設計不僅反映出命題者的學識,更關涉到命題旨趣,甚至還會折射出特定的時代精神”。[3]
唐朝國勢在宣宗朝得到略微恢復,隨之在懿、僖兩朝陡然急下。懿宗本質平庸,又寵幸宦官、任用佞臣,遂因蠱惑侈言而亂驕淫方寸。史載:“上好音樂宴游,殿前供奉樂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設不減十余,水陸皆備,聽樂觀優,不知厭倦,賜與動及千緡。”[4]皇帝不親庶政,游宴無度,遂委權于宦官、宰相,而宰相多為貪贓枉法之佞臣,宦官也因之權勢日炙,使得宣宗時期較為有效的中樞行政體制遭到破壞。咸通九年爆發的“龐勛之亂”曠日持久,使得中原地區為之掃蕩幾盡,此后內亂頻仍,國家動蕩不安。
在此背景下,年幼的僖宗由宦官擁立入膺寶位,政事皆委左神策軍中尉田令孜,而田令孜“知帝不足憚,則販鬻官爵,除拜不待旨,假賜緋紫不以聞。百度崩弛,內外垢玩。”[5]在宦官權力只手遮天的情況下,僖宗朝君臣離心,邊患四起,藩鎮相攻,以王仙芝、黃巢為首的農民軍更是從根本上動搖了唐王朝的統治。
唐僖宗文德元年(888)三月,宦官首領、左右神策十軍觀軍容使楊復恭擁立壽王即帝位,是為昭宗。昭宗是一位有著宏偉志向的皇帝,史載:“帝攻書好文,猶重儒術,神氣雄俊,有會昌之遺風。以先朝威武不振,國命寖微,而尊禮大臣,詳延道術,意在恢張舊業,號令天下。”[6]昭宗皇帝即位時已過加冠之年,并非童稚即位的僖宗;有英氣、胸懷大志,不似懿宗醉心于享樂。故而昭宗能夠深刻認識到宦官勢力對于皇權的威脅,在藩時就素疾宦官。為了削弱宦官勢力,昭宗在即位之后采取拔擢翰林學士為相并重用宰相的方式來提高相權,借文官集團之力與宦官相抗。經過不懈努力,終于在景福元年(892)借藩鎮之力屠滅宦官首領楊復恭這一宦官集團,宦官的氣焰得以稍抑。
據徐松《登科記考》及孟二冬《登科記考補正》所載,唐昭宗乾寧元年(894)所試《止戈為武賦》,此賦題與當時的社會現實有著密切的聯系:即位之初,昭宗銳意進取,立志掌握殺伐決斷之大權以重振國勢。而乾寧元年(894)省試《止戈為武賦》之賦題正契合了昭宗執政初期欲削平強藩而遭失敗的現實情況。唐代科舉考試所試詩賦之題目多出自儒經、道家經典以及史傳典籍,而乾寧元年(894)所試《止戈為武賦》即出自《左傳·宣公十二年》:“丙辰,楚重至于邲,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筑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7]通過分析史料可知,乾寧元年(894)所試《止戈為武賦》的賦題意義與當時的社會現實聯系緊密。
在昭宗時期,深深威脅皇權的除了宦官勢力,還有藩鎮勢力。而在黃巢起義之后,“江淮轉運路絕,兩河、江淮賦不上供,但歲時獻奉而已。國命所能制者,河西、山南、劍南、嶺南西道數十州。大約郡將自擅,常賦殆絕,藩侯廢置,不自朝廷,王業于是蕩然。”[8]此后諸道的賦稅收入、藩鎮將吏的任免、軍隊的調動都不由朝廷,中央政府已然成為擺設。
在此背景下,昭宗在即位之初就意識到了藩鎮的威脅,并致力于討伐驕藩。文德元年(888)三月昭宗即位,六月即授權宰相韋昭度入川戡平內亂;大順元年(890)昭宗于京師廣募兵士至十萬人,組建聽命于皇帝本人的武裝力量;同年五月,在宰相張濬與兩河藩鎮的請求下,以宰相張濬為帥發禁軍及邠、寧、鄜、夏諸州軍士共五萬人討伐河東節度使李克用。然而由于藩鎮強勢、朝廷實力不足以及藩鎮之間、藩鎮與宦官之間相勾結等原因,上述討伐皆以失敗告終,驕藩實力愈來愈強,逐漸開始憑陵王室。景福元年(892)正月,宦官逆賊楊復恭藏于興元節度使楊守亮處,鳳翔節度使李茂貞以討伐叛臣楊守亮為名聯合邠州、華州、同州、秦州等藩鎮上表朝廷,請求允許諸藩出兵,且授予李茂貞山南招討使之銜。是時,李茂貞盡有長安西北的廣大地區,而山南道則是位于長安以南的廣大區域,得此地,則朝廷將更加受制于李茂貞。故內臣皆不同意李茂貞之奏,李茂貞聞之忿怒,遂與王行瑜自行發兵攻興元,并致書宰相杜讓能、中尉西門君遂,言辭詬詈,凌蔑王室,昭宗為之怒不可遏。景福二年(893)七月,昭宗下詔以李茂貞為山南西道節度使,而以宰相徐彥若為鳳翔隴州節度使,以分其權,茂貞不奉召而上表自論,“昭宗以茂貞表辭不遜,不能忍”遂“怒曰:‘吾不能孱孱坐受凌弱!乃責讓能治兵,而以覃王嗣周為京西招討使”[9],率扈駕五十四軍討伐李茂貞。九月,王師敗績,李茂貞兵臨長安,昭宗趣登安福門斬兩樞密使、貶宰相杜讓能以求罷兵。
據孟二冬《登科記考補正》考證,乾元元年(894)省試《止戈為武賦》以“和眾安人,是為武德”為韻,而“和眾安人”同樣出自上文所引《左傳》,正是對于武德的解釋。對于武德,楚莊王認為其義在禁止暴力、管制兵士、穩定王業、鞏固功勛、安定百姓、協和萬邦、增加財富。而“止戈為武”一詞,歷來有兩種解釋:一是指通過武力的方式來消除戰爭,二是指停止戰爭即為武。乾元元年(894)省試賦文目前僅存一篇,為此年進士及第的徐夤所作之賦。其賦文中有:“今我后洞窮經之旨,知為君之難,功不宰而八蠻自服,書同文而萬國咸安。列圣摧兇,我則懷遠而柔邇;前王伐罪,我則去殺而勝殘。故得文物重新,妖氛自弭”等句。剖析上述賦文,則止戰意味極其濃郁,其中“列圣摧兇,我則懷遠而柔邇;前王伐罪,我則去殺而勝殘”一句更是明顯地表達出了停止使用武力、采用懷柔政策的思想。按此年省試之前一年,即景福二年(893),朝廷剛下詔于李茂貞使弭兵,而次年的省試賦題又以罷兵為旨,真實地反映出這一時期嚴峻的社會現實。以徐夤為代表的應考士子敏銳地察覺到有司釋放停戰信號這一命題意圖,故而在賦中將“止戈為武”釋為君王修德懷遠、停止戰爭方能達到真正的武德境界,使得國家萬象更新、國泰民安。這就與朝廷以及主考官的旨趣相符,因而得以一舉中第。
綜上所述,唐昭宗乾寧元年(894)省試以《止戈為武賦》為賦題與當時的社會現實聯系密切。賦題中“止戈為武”的意義應為停止戰爭即為武德,表達了希望天下安寧、偃甲息兵的愿望,同時此賦題也體現了昭宗即位之初朝廷削藩失敗、強藩愈加憑陵王室的社會現實。
參考文獻:
[1](后晉)劉昫等撰.舊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3440.
[2](宋)洪邁撰,孔凡禮點校.《容齋隨筆》[M].北京:中華書局,2015:375.
[3]王士祥.唐代試賦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22.
[4](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鑒[M].北京:中華書局,1956:8117.
[5](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5885.
[6](后晉)劉昫等撰.舊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735.
[7]左丘明撰,杜預集解.春秋左傳集解[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590.
[8](后晉)劉昫等撰.舊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720.
[9](宋)歐陽修撰,(宋)徐無黨注.新五代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4: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