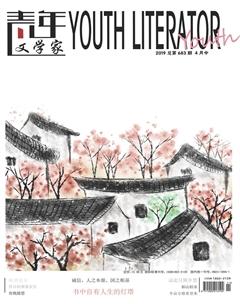昆丁的阿尼瑪原型解讀
盧玉芝
摘? 要: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分別以家族人物小兒子班吉、大兒子昆丁、二兒子杰生、老仆人迪厄西的生活經歷與心理意識為依托,并輔之哀憐生動的筆觸,不僅刻畫出了南方地主康普生大家族的沒落,也揭示出了種植園經濟制度的解體。其中,生動獨特的人物形象以及伴隨著人物形象的繁亂紛呈的內心意識一直是國內外學者的研究熱點,而本文將從榮格的阿尼瑪原型理論出發,分析主人公之一昆丁的阿尼瑪原型特征,并探尋其深層含義。
關鍵詞:昆丁;阿尼瑪原型;救贖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11--02
一、引言
威廉福·克納是美國文學史上最具影響力的作家之一,意識流文學的代表人物,其文學作品多描繪20世紀的美國南方社會,追溯急劇變動的南方社會歷史以及捕捉變遷中人們動蕩的心理,《喧嘩與騷動》便是其中一部,通過大家族的衰落,一方面揭示了時代向前發展的必然性,另一方面也道出了現代社會的價值多元與道德取向,以及引人深思的現代精神危機。該作品自問世以來,許多評論家、學者便對其獨特的敘事結構、人物形象、意識流手法、文本意蘊等方面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和研究。而本文則主要運用榮格的原型理論對昆丁這一人物進行解讀,并探尋其深層含義。瑞士心理學家榮格是原型分析理論的代表人物,他在奧地利精神分析學家佛洛依德的無意識學說基礎上提出了集體無意識,是指由遺傳保留的無數同類型經驗在心理最深層積淀的人類普遍性精神。而集體無意識的主要組成部分是原型,榮格將原型主要分為四種:人格面具、阿尼瑪、阿尼姆斯、陰影,這四種不同的原型分別體現了人的不同方面。其中,阿尼瑪是每個男人心中都有的女人形象,是男人心靈中的女性成分。阿尼瑪身上有男性認為女性所有的好的特點。每個男人的阿尼瑪都不盡相同,而在《喧嘩與騷動》中,從承載著沒落家族復興之任的哈佛高材生到無心學習、街頭閑逛的漫游者,從護妹心切的兄長到無路可走的自殺者,昆丁的阿尼瑪原型一方面顯現于其富有陰性特征的性格之中,另一方面積淀于昆丁與文中兩位女性(母親和妹妹)的病態關系與想象。
二、陰柔“阿尼瑪”之性格顯現
主人公昆丁身上的阿尼瑪特征首先體現在他的性格上。昆丁作為家中長子,一邊承載著家族復興的厚望,一邊深陷于現實的泥潭,長此以往,形成了陰郁敏感、耽于幻想、怯懦無能的性格,并在歷史變遷的巨大心理激蕩與妹妹凱蒂的失貞墮落的沖擊之下,昆丁走向自我滅亡。在以昆丁為主的第二章節里,主要敘述了昆丁1910年6月2日這天所發生的事情與其交錯不清的各種心理意識,僅僅是這一天的時間里,昆丁的阿尼瑪特征也十分明顯。
首先,其陰郁敏感:章節開篇,昆丁從睡夢中醒來,回到時間之中回憶起父親關于時間的話:“甚至根本沒有人跟時間較量過。這個戰場不過向人顯示了他自己的愚蠢與失望,而勝利,也僅僅是哲人與傻子的一種幻想而已。”[1]這種因面對時間流逝而無所作為的消極觀點雖并未直接出自昆丁之口,但毋庸置疑,他是認可并秉持該觀點。并且開端的此番觀點也為行文鋪墊出陰郁的氛圍。接下來,在長達100頁的自述里,昆丁并未提及他本該豐富充實的大學生活,例如他的同窗情誼、參加哈佛的劃船賽事或者未來的生活規劃或展望,相反他曠課缺席、外出閑逛、回憶往事,游離于過去與現在之間,這些毫不動情的敘述也正是昆丁陰郁性格的一種體現。此外,昆丁的陰郁還體現在他與水(河)及陰影的聯系。他總是長時間地專注于河面以及陰影,水(河)既是他漫無目的時的一種消遣,也是牽引出無限回憶的源頭,更是他萬念俱灰后的歸屬之地。而陰影,無論是投射在水面的、殘留在路面上的還是折疊在欄桿上的陰影,都是昆丁想極力反抗、擺脫的。陰影對他來說始終承載著時間,是流逝時間的一種投射,是籠罩而來的黑暗,是無法逃脫的陰郁,而與此同時,水與陰影本是陰性的,是屬于阿尼瑪的。而昆丁的敏感則主要體現在對時間的態度上,昆丁一直在努力地逃避時間,他似乎在努力做到忘記時間,但事實上,越是逃避,越無處可逃,時間分秒未差,他時時刻刻都能感受到那小齒輪輕輕的喀嚓喀嚓聲。即使砸掉那只祖傳的表,時間依舊流逝。另外,昆丁的敏感還體現在對妹妹凱蒂的童貞問題上,他一直視妹妹為純潔的象征,而保護妹妹的純潔也成了他義不容辭的責任。例如在都還是孩童時,妹妹凱蒂因玩水弄濕了衣服,而脫下弄濕的衣服卻遭到了小昆丁的一記耳光。事情雖小,但足以看出在昆丁眼里,妹妹是必須圣潔的,不允許有任何不合時宜的行為,以至于后來,妹妹的失貞墮落行為更是讓他脆弱敏感的心靈不堪一擊。
其次,耽于幻想。在昆丁的自述里,描述實際行動的部分不多,大部分篇幅都是他的內心獨白或是幾重回憶與現實的相互交織,例如昆丁眼中的有著特別含義的各種景物,以及由妹妹失去貞潔而引發的各種想象與回憶。他希冀靠砸掉表來挽留住時間,以此來幻想家族依舊興旺;他幻想依靠亂倫來掩蓋妹妹失去貞潔的事實;發覺無法掩蓋殘酷事實后,他便開始幻想和妹妹一起帶上班吉去過一個隱世隔絕的生活;但這個幻想破滅之后,他揚言要殺掉妹妹,并幻想和妹妹一起重生于地獄。這些不切實際的夢幻始終充斥于昆丁的頭腦,讓他無力面對生活。
再次,昆丁又是懦弱無能的。由于出身于沒落的南方種植園主家庭,嚴重受到南方傳統價值觀念的影響,他作為家中長子,也是家中唯一一位在哈佛念大學的孩子,卻只知道一味地沉浸于家道中落的傷感之中,并未為整個家族做出過什么切實的貢獻。而他的名字“昆丁”在英文中本有勇敢之意,但事實上,他的英勇不過是在他自己的世界里幻想家族依舊興旺以及自己能像勇士那樣保護妹妹。面對妹妹失去貞潔的實情,他只能像個孩子一樣號啕大哭;他想要像勇士一樣趕走妹妹的情人,卻在雙方對陣時暈厥過去;在妹妹婚禮那天,他也選擇把自己喝得爛醉如泥,企求麻痹自己、麻痹現實。也正是因為懦弱無能,昆丁在精神上和肉體上遭受著難以忍受的煎熬與恐懼。
雖然阿尼瑪是陰性的,具有其消極的一面,但也不乏積極的一面,而在昆丁身上,阿尼瑪的積極一面也有所體現,即昆丁性格之中的溫和與善良。在昆丁自述里,他從小乖巧聽話、謹遵父親教誨,與人交往,例如同室友、鐘表店老板的對談,亦舉止得體、謙和有禮。另外,他向老黑人施舍硬幣,以示圣誕祝愿,雖然施舍不多,但足以表達出昆丁對窮苦黑人的憐憫與關愛;后來他還主動詢問關心因意見不合而單獨行動的小孩,這都說明他是一個平易近人、心地善良的人。最后,在面包店里,他又主動為一個來路不明的小女孩買面包,并決定送她回家。雖然最終由于語言障礙非但不成功,反而被誣陷為人販子送進警察局,但一路上,他都耐心十足、彬彬有禮、不溫不怒。總之吧,昆丁這種樂于助人、善良、謙讓的脾性更讓阿尼瑪原型特征的積極面更加光明。
三、病態“阿尼瑪”之人物關系
另一方面,昆丁的阿尼瑪原型特征的深層含義則主要體現在他與妹妹凱蒂的關系上。在康普生這個沒落的種植園主家庭里,對于昆丁來說,凱蒂不僅僅是她的妹妹,更是他的心靈向導與救贖之源。兒時的昆丁與凱蒂感情一直要好,作為南方種植園主階級的最后一代的主要代表者,一種無形的沒落感與壓抑感始終伴隨著他,而他只有與凱蒂在一起,這些感覺才會有所減輕,才會看到光亮。但昆丁身上的阿尼瑪原型特征最初是受到其母親的影響的。榮格認為在男人的無意識當中,通過遺傳方式留存了女人的一個集體形象,借助于此,他得以體會到女性的本質。也即,阿尼瑪是從嵌在男人身上有機體上的初源處而遺傳而來的因素,是他的所有祖先對女性經歷所留下的一種印痕或原型,是女人打下的全部印象的一種積淀。而昆丁所接觸到的最早女性是他母親-康普生太太,一位整日杞人憂天、無病呻吟的舊式家族婦人,她自私、冷漠、勢力,并不正真關心自己的丈夫和子女。她作為母親帶給昆丁的阿尼瑪影響無疑是消極的,它預先存在于昆丁的情緒、反應、沖動之中,存在于他精神生活中自發的其它事件里,特別顯現于性格之中的驅趕不散的陰郁、一觸即發的敏感、萬般沉醉的幻想以及不堪一擊的懦弱。但除了母親之外,家中還有美麗活潑、溫柔且不失心的妹妹凱蒂,與妹妹的相處無疑為昆丁打開了另一扇阿尼瑪之門。由于阿尼瑪一方面是無意識的人格化表象,同時它又是和無意識發生關聯的機能,由妹妹凱蒂引發的阿尼瑪作為昆丁與無意識之間的橋梁,則可以作為其心靈的救火梯或向導,如同歌德在《浮士德》結尾處寫下的:“永恒之女性接引我們向上。”[2]而昆丁也確信凱蒂有如此魔力,他視妹妹為最圣潔的象征,能夠引導他的內心,能在內心世界開辟出一條道路,并將他從沉重的世俗觀念與家道中落的悲涼中解救出來。
此外,凱蒂還是昆丁的救贖之源。昆丁是具有原罪意識的,在他看來,曾經顯赫一時的望族日漸衰微這是一種罪,家庭的分崩離析也是一種罪,而自己無力挽回又是一種罪,時間的流逝是一種罪,時代的變遷更是一種罪,在重重罪惡的壓迫下,昆丁不由得把希望投向了凱蒂,希望通過凱蒂走向救贖。所以,保護妹妹,讓她永遠保持貞潔成了昆丁的最大的救贖方式。但與此同時,不得不提,昆丁一方面在早年的家庭生活里受到母親的負面的阿尼瑪影響,另一方面他的潛意識中的阿尼瑪也使他在與凱蒂接觸時產生一些自然的生理或情緒反應。作為一種原型,妹妹凱蒂所投射出的阿尼瑪正是他所向往的各種情感的混合體,如美麗、溫暖等。長此以往,昆丁對妹妹已產生出一種模糊不清的感情和情緒,這使得他們的關系更像是一對超出常理的戀人,而昆丁也深知這種情感也是有罪的。但無論如何,昆丁始終在以一種非理性的、甚至有些病態的方式進行著他的救贖:他阻止妹妹戀愛、以幻想亂倫來掩蓋妹妹失身的事實、反對妹妹結婚、夢想著和妹妹雙雙自殺以洗清罪孽。但昆丁的救贖之路終究太過崎嶇,妹妹凱蒂不但失去貞潔,而且淪落為妓,他的救贖之源堙滅了,最終只能走向自殺。
四、結語
昆丁不僅僅是憂郁軟弱的,也是溫和善良的,他深陷重重罪惡的同時,亦渴望著能夠走向救贖。在對昆丁的阿尼瑪原型特征的解讀里,昆丁這一明暗交織的人物形象一方面詮釋出了阿尼瑪原型特征應有的二元性,另一方面也昭示出了整個時代背景下的普遍精神困頓。而昆丁最終沒能走出困頓,他的自殺不再是個人的悲劇,而是在整個社會裹挾發展中所作出的無法避免的犧牲。
注釋:
[1]威廉福·克納. 《喧嘩與騷動》.李文俊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第77頁.
[2]歌德. 《浮士德》[M]. 綠原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5.
參考文獻:
[1]歌德. 浮士德[M]. 綠原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
[2]榮格. 心理學與文學[M].上海: 三聯書店,1987.
[3]肖明翰. 威廉·福克納研究[M].北京:外語與教學研究出版社,1999.
[4]威廉·福克納. 喧嘩與騷動[M].李文俊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
[5]朱剛. 二十世紀西方文藝批評理論[M].上海: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