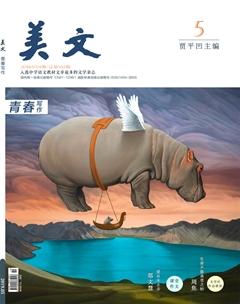風(fēng)動(dòng)·幡動(dòng)·皆心動(dòng)
郝可心
“浩浩乎如馮虛御風(fēng),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dú)立,羽化而登仙。”“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初讀《前赤壁賦》,我懵懂不解,不知其深意。細(xì)讀《蘇東坡傳》,我似乎于蕪雜中抽得一絲,悟得一點(diǎn)兒真諦。
樹欲靜而風(fēng)不止。風(fēng)動(dòng)?幡動(dòng)?皆心動(dòng)!若秉承一顆初心,躲進(jìn)小樓成一統(tǒng),管它春風(fēng)與冬風(fēng)。這,是蘇東坡教授給我的。他的一生也確實(shí)經(jīng)歷了春風(fēng)得意、夏風(fēng)灼灼、秋風(fēng)蕭瑟、冬風(fēng)凜冽,而不管在哪種風(fēng)候中,他都能保持一種曠達(dá)與自適,做一個(gè)樂天派與道德家。
生于小康之家,父親因其降生而發(fā)奮讀書,父子三人同時(shí)進(jìn)京趕考,他名列第二,二十歲高中進(jìn)士,才華出眾、壯志凌云,春風(fēng)得意、快馬疾馳。“人生到處知何似,應(yīng)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fù)計(jì)東西。”其心之自如可見一般。他奉命為本朝皇帝寫傳記,為百姓向上天祈雨,閑暇之余吟詩作賦。“一門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詩賦傳千古,峨眉共比高”的口碑開始有所樹立。他始終保持著那份低調(diào)與從容,不事張揚(yáng)、不求聞達(dá),可謂春風(fēng)得意還需策馬加鞭。
神宗繼位,新法推行,朝堂之上刮起新舊兩黨之爭(zhēng)的灼灼夏風(fēng),以王安石為首的新派和以司馬光為首的舊派劍拔弩張、不可調(diào)和。身在廟堂之上,難免被風(fēng)吹,何況蘇東坡這一耿直之士?蘇東坡不騎墻、不媚上,從事實(shí)出發(fā),力陳青苗法、募役法的危害,并向皇帝上呈萬言書,直呼王安石名字直陳新法之弊,并于萬般無奈之中提請(qǐng)歸隱,自然引起得勢(shì)新黨宵小之輩的極度嫉恨。在風(fēng)雨飄搖中保持一顆初心何其難能可貴,可謂夏風(fēng)灼灼我自遺世獨(dú)立。
初次遭貶黜,自杭州、湖州而黃州、宜興、登州……他的生活境遇每況愈下,而他的心境卻并無太大變化。他力求為百姓解除饑饉,指定醫(yī)生為囚徒治病,成立救兒會(huì)拯救被遺棄嬰兒。他無端遭受指控,經(jīng)歷了牢獄之災(zāi)和以為死期臨近的喜劇式恐慌,化身為農(nóng)民和隱士。他躬耕于東坡,因號(hào)“東坡居士”;他與藥師、大夫、酒監(jiān)為友,感受普通人的快樂;他將“富者不肯吃,貧者不解煮”的豬肉做成人間美味,讓“東坡肉”至今蜚聲;他靜習(xí)瑜伽,創(chuàng)作《養(yǎng)生論》。這個(gè)時(shí)期他的文學(xué)才情達(dá)到了極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的《飲湖上初晴后雨》,“月有陰晴圓缺”的《水調(diào)歌頭》,“孤館燈青、野店雞號(hào)”的《沁園春》,將胸中塊壘抒發(fā)于筆端,可謂于秋風(fēng)蕭瑟中品味獨(dú)得之樂。
在短暫的太后恩寵之后,蘇東坡迎來了人生的寒冬——二度被流放,成為被貶謫到廣東高山大禹嶺以南的第一人,隨行者唯有朝云而已。他依舊極盡所能為百姓做事:推行“浮馬”緩解插秧之苦,創(chuàng)辦公立醫(yī)院,實(shí)施飲水工程,努力陳規(guī)陋俗……在極其惡劣的境遇中,他研究釀酒之法,寫成《松醪賦》;他研制良墨,苦心鉆研書法和畫藝;他去鄉(xiāng)野采藥,尋求新的醫(yī)藥用途;他校注《論語》《易經(jīng)》,從經(jīng)典中吸納人生智慧……即便飲食已成憂,他還調(diào)侃陽光療餓之法,可謂寒風(fēng)凜冽心中依然有溫度。
歲月有四季,人生有四風(fēng),不管風(fēng)從哪個(gè)方向吹來,不管風(fēng)帶著何種溫度,我們內(nèi)心的淡定和從容或許比風(fēng)帶來的影響更重要。聯(lián)想到自己,太容易為風(fēng)向所左右,太容易受外物所羈絆。朋友不經(jīng)意的一句話語會(huì)讓我如沐春風(fēng),一次不起眼的考試會(huì)讓我如夏風(fēng)吹過大汗淋淋,媽媽無意識(shí)的幾句譏諷就讓我覺得風(fēng)雨凄凄,班主任無意的一個(gè)小眼神近乎寒風(fēng)過境。其實(shí),世間萬物皆隨心而動(dòng)而非隨風(fēng)而動(dòng),變的不是環(huán)境,是我們的心境,倘若心懷曠達(dá),即便“八月秋高風(fēng)怒號(hào),卷我屋上三重茅”,也會(huì)“吾廬獨(dú)破受凍死亦足”。
在這個(gè)喧囂浮躁又發(fā)展神速的世界里,或許,讓心沉靜下來,感受不到風(fēng)的侵襲才是最上上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