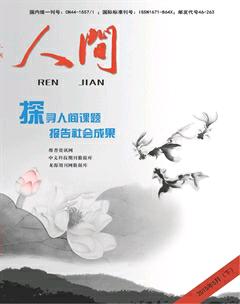涼山州教育現(xiàn)狀研究
胡伍強
(甘洛縣新市壩鎮(zhèn)爾覺小學(xué)校,四川 甘洛 616850)
涼山州教育現(xiàn)狀研究
胡伍強
(甘洛縣新市壩鎮(zhèn)爾覺小學(xué)校,四川 甘洛 616850)
育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教育泛指一切有目的地影響人的身心發(fā)展的社會實踐活動。不言而喻教育是一個關(guān)乎國家發(fā)展的大問題。中國是一個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有55個少數(shù)民族。據(jù)中國人口普查統(tǒng)計少數(shù)民族人數(shù)僅占全國人口的8%,但聚居地區(qū)約占全國總面積的50~60%。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由于種種社會歷史原因,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社會經(jīng)濟一般比漢族地區(qū)落后,發(fā)展很不平衡,個別地區(qū)甚至還保留著某些原始公社制度的殘余。所以對少數(shù)民族來說,教育是擺脫貧困,獲得全方位發(fā)展的根本途徑。
涼山;教育;現(xiàn)狀
當(dāng)前的世界,政治、經(jīng)濟、科學(xué)技術(shù)日新月新、發(fā)展迅速,各行各業(yè)的競爭日趨激烈。全世界正步入一個嶄新的世紀(jì)時,“政治多極化”、“經(jīng)濟全球化”、“科學(xué)技術(shù)是第一生產(chǎn)力”、“新世紀(jì)是知識經(jīng)濟時代”、“網(wǎng)絡(luò)化”、“智能化”……一句又一句的口號,預(yù)示著我們這個世界將進入一個充滿發(fā)展、機遇與挑戰(zhàn)的時代。面對這一切,世界各國都在思索,都在討論,尋找一條條各國的發(fā)展之路。在這其中,教育的改革與發(fā)展,無疑當(dāng)處于重中之重。而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教育事業(yè)要跨躍式發(fā)展、要有一個質(zhì)的飛躍,結(jié)合實際。涼山彝族自治州,是中國最大的彝族聚居區(qū),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川滇交界處,幅員面積6萬余平方公里,總?cè)丝?73.04萬人,境內(nèi)有漢、彝、藏、蒙古、納西等10多個世居民族。全州轄1市16縣。彝族人口167萬,占總?cè)丝诘?2.41%,是全國最大的彝族聚居區(qū)。彝族是一個擁有悠久歷史,有著自己獨特的文字和語言的民族,歷史上的彝族創(chuàng)造了燦爛的文化。
一、教育觀念認(rèn)識缺失
處于涼山彝族地區(qū)工作的教育工作者、領(lǐng)導(dǎo)者均要徹底轉(zhuǎn)變陳舊、傳統(tǒng)、落后的觀念,樹立和倡導(dǎo)先進的教育教學(xué)觀念。轉(zhuǎn)變觀念并不是只是口頭上的一句空話,要徹底,從心底轉(zhuǎn)變,落實于行動。當(dāng)前很多地區(qū)的學(xué)校、主管單位的領(lǐng)導(dǎo)在會上大講小說,經(jīng)常提轉(zhuǎn)變觀念,學(xué)習(xí)先進的教育教學(xué)方法……但最終落實在組織、管理、教學(xué)上卻似乎絲毫未變,還是老一套,這叫什么轉(zhuǎn)變呢?當(dāng)今的世界是高度發(fā)展的世界,結(jié)合發(fā)展趨勢,我們要樹立終身教育觀念、大教育觀念、素質(zhì)教育觀念、全面發(fā)展觀念、現(xiàn)代技術(shù)教育觀念等諸多新觀念。結(jié)合鄧小平同志提出的“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現(xiàn)代化”,真正培養(yǎng)出德、智、體、美、勞全面發(fā)展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jì)律”的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shè)者。
二、重男輕女習(xí)俗導(dǎo)致學(xué)生中性別比例失調(diào)
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 小學(xué)階段,女生輟學(xué)率一般比男生略高。之所以如此, 源于少數(shù)民族傳統(tǒng)的重男輕女的習(xí)俗。雖然隨著社會發(fā)展, 不少地區(qū)這一陳舊觀念已有很大轉(zhuǎn)變, 但在一些貧困地區(qū)這種觀念仍然是影響當(dāng)?shù)亓x務(wù)教育發(fā)展的障礙性問題。
2000年人口普查資料顯示,6歲及6歲以上未上學(xué)人口女性占到了66.17%,文盲和半文盲人口中女性占了2/3的比例。對女性受教育權(quán)利的漠視導(dǎo)致了學(xué)生中性別比例嚴(yán)重失調(diào),部分學(xué)校甚至出現(xiàn)了“和尚班”。
其次,經(jīng)濟、交通、安全等問題也是導(dǎo)致女童教育水平低的原因。這一點從聯(lián)合國開發(fā)計劃署在1998年出版的《中國:人類發(fā)展報告》就可以看出,此書指出:“在中國,女孩的教育最容易受到貧困的沖擊。除了這些教常見的原因外,女童自身也存在一些心理障礙。
三、教師數(shù)量少
加強師資隊伍建設(shè),不斷提高師資水平是實現(xiàn)教育現(xiàn)代化的關(guān)鍵,教師的素質(zhì)及水平勢必會影響學(xué)生的發(fā)展。當(dāng)前,我們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教師,雖經(jīng)過多年的發(fā)展,素質(zhì)有所提高,但總體上,還遠(yuǎn)遠(yuǎn)不能適應(yīng)21世紀(jì)的社會發(fā)展需求。雖然很多教師學(xué)歷均能達(dá)標(biāo),但政治思想、教育素養(yǎng)、知識能力水平、教學(xué)藝術(shù)、教學(xué)方法等方面還很欠缺。社會在發(fā)展,知識在更新,我們教師也要不斷提高自己的修養(yǎng)及知識水平,跟上社會發(fā)展的步伐,樹立終身教育、終身學(xué)習(xí)、的觀念。
涼山州由于環(huán)境惡劣,條件差,許多內(nèi)地教師人才不愿去貧窮落后的涼山州教學(xué);而財力不足,要教師墊付學(xué)生書本費等,也使本地教師覺得待遇低無法堅持而盼改行;或是因資金問題,許多地區(qū)不得不請代課教師,代課教師既要教書又要務(wù)農(nóng),教學(xué)質(zhì)量難以保證。在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召開扶貧開發(fā)攻堅動員大會上,提出在優(yōu)先發(fā)展民族教育上抓突破,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目前,涼山州缺中小學(xué)教師近6000名,學(xué)前教育老師缺1.8萬名。
總之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教育事業(yè)要從根本上有一個大的改觀,教育作為一項具有全局性,基礎(chǔ)性意義的社會系統(tǒng)工程,關(guān)系著國家的發(fā)展,牽動著千家萬戶的切身利益。筆者僅以此文拋磚引玉, 豐富對此問題的研究, 為涼山州彝族教育發(fā)展的理論研究與實踐探索提供相應(yīng)資源。
[1]羅嘉福. 提高認(rèn)識 加強領(lǐng)導(dǎo) 采取有力措施 大力推進我省民族教育改革與發(fā)展在省委民族工作領(lǐng)導(dǎo)小組(擴大)會議上的發(fā)言[Z].
[2]馬英林、羅涼昭:涼山彝區(qū)教育發(fā)展現(xiàn)狀調(diào)查及對策建議,西南民族學(xué)院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03年,第3期。
[3]潘正云、馬林英:“涼山彝族女童教育面臨的問題和發(fā)展策略”,貴州民族研究(季刊),2000年,第4期(總第84期)。
[4]彭雪芳:“對彝族教育的現(xiàn)狀分析及對策”,西南民族大學(xué)學(xué)報(人文社科版),2006年4月,總第176期。
G750
A
1671-864X(2015)05-0087-01
胡伍強(1977-),甘洛縣新市壩鎮(zhèn)爾覺小學(xué)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