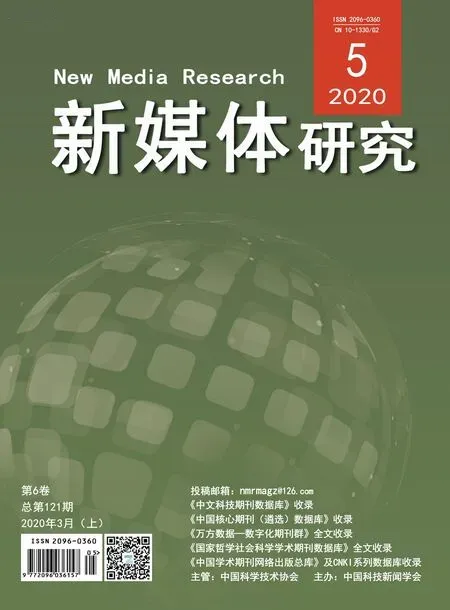“土味文化”躥紅原因探析
龔江怡
摘 ?要 ?“土味文化”從直播平臺到短視頻平臺再到微博和B站等平臺,不知不覺在手機各大軟件中占據一席之地。文章聚焦“土味文化”的發展,以“快手”App為例,分析“土味文化”躥紅的背后原因。
關鍵詞 ?土味文化;“快手”;短視頻
中圖分類號 ?G2 ? ? ?文獻標識碼 ?A ? ? ?文章編號 ?2096-0360(2019)05-0109-02
1 ?“土味文化”的概念與特點
“土味文化”是一種伴隨著直播的發展而出現的網絡亞文化,在短視頻的繁盛中獲得越來越多大眾的喜愛,它的傳播者大多文化水平不高,傳播內容以“鄉村文化”為基礎,受傳者不局限于某個群體,甚至有漸漸擴大的趨勢,而這些受傳者往往通過模仿傳播者的特殊符號體系成為其中一員。
2 ?“土味文化”躥紅的原因分析
2.1 ?美學理論淵源
“土味”的事物,一定程度上是“丑”的事物。在美學領域,“丑”是具有審美價值的,不同于倫理學中的“丑”。一方面,“丑”作為一種客觀存在還原了現實的本貌,鄭板橋在《題畫》中就對歷代畫家筆下的“丑石”做過總結,將“丑”作為美的對立面表現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和自然界的千姿百態;在文學領域,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塑造了長相奇丑、身帶殘疾的底層人物“卡西莫多”,同時他也是書中“真善美”的代表,所謂“丑就在美的旁邊,畸形靠著優美,丑怪藏在崇高的背后,美與惡并存,光明與黑暗相共”就闡述了“丑”的存在意義;同理,“快手”中奇裝異服的小鎮青年搭配上DJ舞曲的短視頻引發潮流也就不足為奇。另一方面,對人物形象和特點的刻畫和突出也需要“丑”的表現,因為“丑”的人物才能區別于普通人,才具備獨特的藝術形象和效果。如列賓的名畫《伏爾加河上的纖夫》描繪了烈日下勞動的瘦骨嶙峋、愁眉苦臉的纖夫,這些形象不具有觀賞上的美感,甚至可以算得上是“丑”的,可是卻展現了現實生活中纖夫工作的艱辛和個體的愁悶;魯迅利用孔乙己、阿Q等形象映射“丑陋”的中國人,這些形象之所以被一代代的讀者銘記一定程度上基于這種“丑”的特殊性;“快手”上短視頻的制作者通過“丑化”自己,也是利用了人們的“審丑”心理,通過這種方式吸引受眾,達到賺取流量最終將流量變現的目的。
2.2 ?受眾心理分析
1)據觀察,多數受眾與“土味”傳播內容的初次接觸是出于獵奇心理。“獵奇心”與“好奇心”相似,但又有所不同。“好奇心”是人類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內在驅動力,“獵奇心”雖說也是產生于對環境的認識需求,不過“獵奇”的對象具有極端特殊的特點,這些對象常與“暴力”“性”“丑”等元素相關,能帶給人極端刺激。“快手”紅人陳山憑借其“長相巨丑無比卻擁有豪車和美女”的視頻標簽在2017年就坐擁528.5萬粉絲,雖然其身份的真實性有待考究,但是倘若有幕后者,也一定是一個深諳受眾心理的高人。
2)尋樂心理是“土味文化”進一步“籠絡人心”的工具。大部分人打開“快手”的時間段集中于飯后和睡前,在休息時間里,尋求精神的放松成為刷“快手”的主要目的。“企鵝智酷”2018年12月的《快手用戶數據研究報告》顯示,57%的用戶選擇關注“有意思的普通人”,69.6%的用戶更喜歡看“搞
笑/惡搞類”視頻。“快手”上的“土味短視頻”大部分也是基于“有趣”而制作的,這一點也就成為快手吸納忠實用戶的“殺手锏”。
3)人是群居動物,人也是社會中的人,一個人不可能脫離群體而存在,群體歸屬是馬斯洛需求層次的重要一層。因潛意識中對群體歸屬感的需求進而激發從眾行為的心理機制在“土味文化”的走紅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當個體觀察到某個“土味視頻”的點贊量和評論量達到很大的數量時,會傾向于認為大多數人喜歡和追捧這種視頻,從而采取與普遍大眾相同的態度。另一方面,不管是“快手”中“土味短視頻”的用戶群體還是發布群體,個體與群體之間都存在著無形的聯系,他們是有共同的興趣愛好、欣賞水平或價值取向的個體集合,群體的聚合也就為“土味文化”不斷吸納個人搭建了
平臺。
4)事實上,人們在觀看“土味視頻”或“土味直播”時會以一種嘲諷的態度找尋自我的滿足感。這種在貶低他人的過程中抬高自己的心理其實非常普遍,同學之間比成績、背后嚼舌根等都存在這方面的心理因素,舉個例子,如果受眾在某視頻上看見某一穿著奇裝異服的年輕小伙跳“老年迪斯科”,很可能會產生“這個人心理是否正常”的疑問,并在自我與他人的對比中獲得自我高人一等的錯覺,這也是“土味文化”得到廣泛關注的重要原因。
2.3 ?城鄉文化認同
新媒介的出現突破了信息傳播的時空局限,這一過程也伴隨著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在“四大媒體”占主導地位的時代,我們對其他文化的認知只能通過報紙、雜志、廣播和電視塑造出的“擬態環境”來了解,短視頻的出現則打破了傳統媒體的既有結構,以其視聽結合的獨特傳播形式,最大限度地傳遞文化信息,我們得以通過另一種渠道建立對異種文化的新認知。過去相對獨立的城鄉文化在這一過程中交織相融并且不可避免地發生碰撞。《報告》顯示,61.2%的快手用戶集中于三四線城市及以下。“快手”上的“土味視頻”一定程度反映了“鄉村文化”。不管是會唱Rap的農村giao哥還是操著一口廣西口音說“我信你個鬼”的外賣小哥,不管是用貴州方言唱著“好嗨喲”的毛毛姐還是愛吃竹鼠的華農兄弟,都從各種側面展現了“鄉村文化”,而作為鄉村文化聚集地的“快手”就像是一個窗口,城里人透過這個窗口窺見了農村人的生活面貌,而農村人也透過這個窗口看到了其他農村人的生活
面貌。
2.4 ?媒介內容補充
長久以來,各種媒體上的主流內容很大部分代表的是“城市文化”,尤其是各種電視劇和電影,呈現的是城市里的繁榮,講述的是城里人的故事,反映的是城里人的價值觀、人生觀、世界觀,“鄉村文化”不知不覺被擠壓和忽視。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我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城鎮化率)為58.52%,城鄉人口相對均衡的結構理應是城鄉文化形成相對平等的地位,事實上,大眾傳媒卻將城市文化中心化,“鄉村文化”反而成為邊緣性的存在。“城市文化”力壓“鄉村文化”占據大眾媒體的半壁江山的原因十分復雜,根深蒂固的文化偏見、媒體人視野的局限、政治力量的介入等都是不可繞開的話題,此處不作詳細論述。以“快手”為發源地,“土味文化”的迅速擴張無疑形成一股相對于“城市文化”的對立力量,“土味文化”的傳播者有意無意參與到城鄉文化的博弈之中,而在傳播者的努力下,“鄉村文化”作為越來越能與城市文化分庭抗禮的勢力,填補了從前大眾媒體內容傳播的空缺。
2.5 ?UGC短視頻平臺助力
在過去,傳播的權利掌握在少數人的手中,社會底層的群眾幾乎沒有傳播資源也不具有傳播技術,因此作為受眾的我們只能被動接受經過“把關人”選擇和加工后的信息,在這種情形下,主流文化很容易形成強有力的攻勢到達受眾甚至排斥任何亞文化的生存,然而UGC短視頻平臺的出現將內容制作和發布的權利轉交給普通大眾,在普通大眾的參與中,這些“接地氣”的短視頻也就應運而生,這些制作者將普通人的生活展現在公眾眼前,將不被了解的農村面貌和形態呈現到平臺之上。“快手”作為典型的UGC短視頻平臺,首先,對于文化水平不高的用戶來說,它的制作流程較之文字編輯更為簡易,用戶只需點擊手機屏幕上的“拍攝”按鈕錄下想要分享的內容就可以直接發布,并且對于文化水平不高的用戶來說,“短視頻”相較于其他傳播方式也更加易于理解;此外,“快手”一開始的用戶群體也是集中在當時的“非主流”愛好者之中,這些人一定程度影響了“快手”的品牌調性,而伴隨著短視頻近幾年的迅速發展,“快手”也順勢延續了以往的風格。
3 ?結束語
“土味文化”的迅速發展從側面反映了傳播受眾群體對傳播內容選擇的分流和細化。在全民皆為內容生產者的時代,內容才是贏得受眾的關鍵,如果制作者能進一步摒棄低俗、落后之風,精心打造新穎且優質的內容,那么在未來,就會形成不同種類的受眾群體,他們有各自青睞和聚集的社交軟件和媒介,整個網絡空間將會被打造成無數種既有交叉部分也有獨立部分的生態圈。
參考文獻
[1]葉朗.美學原理[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358-362.
[2]劉星鑠,吳靖.從“快手”短視頻社交軟件中分析城鄉文化認同[J].現代信息科技,2017(3):111-113,116.
[3]劉娜.重塑與角力:網絡短視頻中的鄉村文化研究——以快手App為例[J].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45(6):161-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