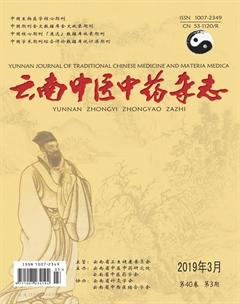針刺結(jié)合隔姜灸治療中重度貝爾面癱68例
吳珍鎧 朱雪飛 陳玉玲


摘要:目的?觀察針刺結(jié)合隔姜灸治療中重度貝爾面癱的臨床療效。方法?將148例中重度貝爾面癱患者隨機分為治療組(針刺結(jié)合隔姜灸治療)和對照組(針刺治療),治療組74例,脫落6例;對照組74例,脫落4例。每日治療1次,5次為1療程,共治療4個療程。4個療程結(jié)束后,采用Sunnybrook面神經(jīng)評分和面部殘疾軀體功能指數(shù)(FDIP)進行臨床療效評價。結(jié)果?治療后2組患者Sunnybrook評分和FDIP評分均較治療前提高(P<0.05),且治療組優(yōu)于對照組,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5)。結(jié)論?針刺結(jié)合隔姜灸治療中重度貝爾面癱優(yōu)于單純針刺治療。
關(guān)鍵詞:貝爾面癱;針刺;隔姜灸
中圖分類號:R276?文獻標志碼:B?文章編號:1007-2349(2019)03-0058-03
貝爾面癱是常見的顱神經(jīng)疾病,占我國神經(jīng)系統(tǒng)疾病患病率的第六位[1]。研究表明,貝爾面癱有很高的自愈性,但將近30%的患者殘留后遺癥[2],持續(xù)的面肌運動功能障礙造成進食、飲水的不便,面部的不對稱給患者容貌帶來終生難以消除的影響,嚴重影響患者的生活質(zhì)量。國內(nèi)外研究表明,輕度面癱患者預后良好,不同療法間并無顯著差異[3-4]。而對于中重度面癱,僅用口服激素、針刺等常規(guī)治療,療效并不理想,常常需要2~3個月以后才能逐漸恢復部分表情肌的功能,并且延續(xù)到半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才能基本康復[5]。本課題組采用針刺結(jié)合隔姜灸治療中重度貝爾面癱,取得一定療效,現(xiàn)報道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所有病例均為本院針灸科就診患者,發(fā)病1周后經(jīng)肌電圖檢測為中重度面神經(jīng)損傷,采用DPS 7.05統(tǒng)計軟件獲得隨機序列,將所有患者隨機分為治療組和對照組。研究共納入患者148例,治療組入組74例,脫落6例;對照組入組74例,脫落4例。最終治療組完成68例,其中男44例,女24例,年齡23~72歲,平均(49.15±13.56)歲;對照組70例,男40例,女30例,年齡23~75歲,平均(50.76±13.63)歲。2組患者性別、年齡無統(tǒng)計學差異(P>0.05),具有可比性。
1.2?診斷標準?根據(jù)2011年中國中醫(yī)科學院與中國針灸學會組織編寫的《中醫(yī)循證臨床實踐指南:針灸》[1],參照《臨床疾病診斷依據(jù)治愈好轉(zhuǎn)標準》[6]中的相關(guān)標準確立,具體如下:①發(fā)病前常有受涼、受潮、吹風或咽炎史。少數(shù)患者于病前幾天可有耳后、耳內(nèi)疼痛或面部不適等前驅(qū)癥狀;②急性或亞急性發(fā)病,出現(xiàn)一側(cè)(偶為兩側(cè))周圍性面癱,可伴有舌前2/3味覺障礙,少數(shù)可有耳鳴,聽覺過敏或耳部皰疹等;③已排除其他原因所致之周圍性面癱(如小腦橋腦角病變、腦干病變、手術(shù)損傷、腮腺病變、格林-巴利綜合征等)。
1.3?面神經(jīng)損傷程度分級標準?采用神經(jīng)肌電圖分級法[7],以患側(cè)面神經(jīng)誘發(fā)電位(M波)波幅損失百分比為指標進行分級,波幅損失百分比=健側(cè)波幅-患側(cè)波幅/健側(cè)波幅。分級如下:①波幅損失<70%為輕度損傷;②波幅損失70%~90%為中度損傷;③波幅損失>90%為重度損傷。
1.4?納入標準?①符合貝爾面癱的診斷標準;②首次發(fā)病者;③病程<7 d;④單側(cè)面肌麻痹者;⑤年齡18~75歲;⑥簽署知情同意書,自愿參加本項研究者。
1.5?排除標準?①由其他疾病如感染性多發(fā)性神經(jīng)根炎、侵犯顳骨的腫瘤、腦卒中、腦外傷、中耳炎、帶狀皰疹等導致的面癱患者;②亨特氏綜合征患者;③發(fā)病第8天進行肌電圖檢測,排除波幅損失<70%的輕度損傷患者;④合并嚴重的心腦血管、肝、肺、腎和造血系統(tǒng)等疾病,以及糖尿病、惡性腫瘤、消化道潰瘍、精神病患者;⑤暈針或?qū)Π呐懦庹?⑥孕婦及哺乳期婦女;⑦正在參加其他臨床試驗者。
1.6?治療方法?所有患者均接受常規(guī)的抗炎、抗病毒治療。發(fā)病1周后經(jīng)肌電圖檢測明確為中重度面癱后進行分組治療。對照組:根據(jù)《中醫(yī)循證臨床實踐指南:針灸》進行針刺治療。針具選用0.30 mm×25 mm華佗牌一次性無菌針灸針。亞急性期:發(fā)病后7天至21天為亞急性期。主穴:患側(cè)地倉、頰車、陽白、下關(guān)、翳風、牽正,雙側(cè)合谷。患者取仰臥位,穴位常規(guī)消毒后,快速進針,面部穴位接電針儀,采用疏密波,強度以患者能夠耐受為度,通電30 min;恢復期:發(fā)病后22天至6個月為恢復期。主穴:患側(cè)地倉、頰車、陽白、魚腰、下關(guān),雙側(cè)合谷。患者取仰臥位,地倉透頰車、陽白透魚腰,余穴常規(guī)針刺,面部穴位接電針儀,疏密波,中等刺激強度,通電20 min。每日1次,5次為1療程,療程間休息2 d,共治療4個療程。
治療組:在對照組的基礎(chǔ)上配合隔姜灸治療。于每次針刺前,先進行隔姜灸治療,施灸部位為患側(cè)面部及前額。操作如下:將生姜切成約0.2 cm厚的姜片,大小約2*2 cm,置于患側(cè)面部。點燃艾柱置于姜片上,以患者自覺溫熱而不灼燙為度,灸至局部皮膚潮紅時移到下一部位。姜片烤干皺縮時更換。每日1次,5次為1療程,療程間休息2 d,共治療4個療程。
1.7?觀察指標?2組患者均于分組治療前及治療4個療程后進行Sunnybrook 面神經(jīng)評分[8]和面部殘疾軀體功能指數(shù)(FDIP)評分[9]。Sunnybrook從靜態(tài)和動態(tài)兩方面評定面神經(jīng)功能,分值范圍0~100分,分值越高表示面神經(jīng)功能越好;FDIP是反映與面部神經(jīng)肌肉功能相關(guān)的軀體殘疾程度問卷,共5個選項,每項分值為2~5分,分值越高提示功能越好。
1.8?統(tǒng)計學方法?采用SPSS 18.0統(tǒng)計軟件進行統(tǒng)計分析,計量資料以(x±s)表示,進行t檢驗或秩和檢驗,計數(shù)資料進行χ2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
2?結(jié)果
2.1?2組治療前后Sunnybrook評分比較?治療前,2組患者Sunnybrook評分無統(tǒng)計學差異(P>0.05),具有可比性;治療后,2組患者Sunnybrook評分均較治療前提高(P<0.05),且治療組優(yōu)于對照組,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5)。見表1。
2.2?2組治療前后FDIP評分比較?治療前,2組患者FDIP評分無統(tǒng)計學差異(P>0.05),具有可比性;治療后,2組患者FDIP評分均較治療前提高(P<0.05),且治療組優(yōu)于對照組,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5)。見表2。
3?討論
貝爾面癱又稱特發(fā)性面神經(jīng)麻痹,是周圍性面癱中最常見的類型,其發(fā)病機制尚未明確,目前認為因多種致病因素作用于面神經(jīng)管,引發(fā)面神經(jīng)非特異性炎性病變[10]。西醫(yī)常用類固醇激素、抗病毒、營養(yǎng)神經(jīng)等藥物進行治療。
中醫(yī)學認為面癱是由于營衛(wèi)不調(diào),氣血衰少,腠理不固,脈絡(luò)空虛,風邪侵襲陽明、少陽經(jīng)脈而致面部經(jīng)脈阻滯,氣血運行不暢,經(jīng)筋失養(yǎng)、肌肉弛緩不收而致病[11]。針刺治療廣泛運用于貝爾面癱,研究表明,針刺能夠促進損傷面神經(jīng)的再生[12]。然而,本病的預后與神經(jīng)損傷程度有關(guān),對于中重度貝爾面癱,常規(guī)治療難以取得滿意療效。
醫(yī)學入門有云“凡病藥之不及,針之不到,必須灸之”。現(xiàn)代研究表明,艾灸能夠有效抑制炎性反應損傷,其“溫通”效應針對炎性反應的功能障礙、氣血阻滯狀態(tài)發(fā)揮治療作用[13]。隔姜灸是在艾柱與皮膚之間放置姜片施灸的一種方法,能使艾火的溫熱作用直接作用于患者面部,同時利用生姜的辛溫之性,與艾灸之熱相互為用,灸得姜助,其溫補祛寒行氣血之力更旺;姜得灸助,其辛溫走竄之力增強,二者相得益彰,共奏溫通經(jīng)絡(luò)之效[14],因而能夠配合針刺更好地促進面部經(jīng)脈的恢復。
本研究采用國際通用量表綜合評價臨床療效。Sunnybrook面神經(jīng)評分通過觀察靜態(tài)時眼、頰、嘴與健側(cè)的比較,動態(tài)時隨意運動(抬額頭、輕閉眼、張嘴微笑、聳鼻、唇吮吸)的對稱性以及聯(lián)動程度對面神經(jīng)功能進行評估。面部殘疾軀體功能指數(shù)(FDIP)對患者吃東西時嘴里移動食物、用杯子喝飲料、特殊發(fā)音、漱口的困難程度,以及一側(cè)眼睛流淚過多或發(fā)干的程度進行評定。研究結(jié)果顯示,2組患者治療前Sunnybrook評分和FDIP評分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2組患者Sunnybrook評分和FDIP評分均較治療前提高(P<0.05),且治療組優(yōu)于對照組,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5)。提示針刺結(jié)合隔姜灸治療中重度貝爾面癱與單純針刺治療相比,能夠明顯改善患者的癥狀和體征,促進面神經(jīng)功能恢復。
綜上所述,針刺結(jié)合隔姜灸治療中重度貝爾面癱能夠顯著提高療效,具有臨床應用價值。
參考文獻:
[1]中國中醫(yī)科學院,中國針灸學會.中醫(yī)循證臨床實踐指南-針灸[M].北京:中國中醫(yī)藥出版社,2011:48-50.
[2]Peitersen E.Bells Palsy:The Spontaneous Course of 2,500 Peripheral Facial Nerve Palsies of Different Etiologies[J].Acta Otolaryngol Suppl,2002,122(7):4-30.
[3]溫昌明,張保朝.康復訓練治療不同程度特發(fā)性面神經(jīng)麻痹:療效比較[J].中國臨床康復,2004,8(13):2446-2447.
[4]Nicastri M,Mancini P,De Seta D,et al.Efficacy of early physical therapy in severe Bells palsy: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Neurorehabil Neural Repair,2013,27(6):542-551.
[5]郭佳,霍則軍.反思Bell麻痹治療中的過度與不足[J].針灸臨床雜志,2010,26(9):64-66.
[6]孫傳新.臨床疾病診斷依據(jù)治愈好轉(zhuǎn)標準[M].北京:人民軍醫(yī)出版社,2002:198.
[7]邱小輝,謝榮波,王盛.85例面神經(jīng)炎患者的肌電圖臨床分析[J].中國醫(yī)藥指南,2014,12(24):138-139.
[8]李健東.面神經(jīng)評分標準[J].國外醫(yī)學(耳鼻咽喉科學分冊),2005,29(6):391.
[9]陳平雁,范建中.面部神經(jīng)肌肉系統(tǒng)功能障礙的一種評價手段—面部殘疾指數(shù)及其信度和效度[J].國外醫(yī)學(物理醫(yī)學與康復學分冊),1997,17(4):173-176.
[10]孟令浩,朱瑞麗,耿曼英,等.高壓氧治療貝爾面癱臨床觀察[J].中國實用神經(jīng)疾病雜志,2017,20(5):64-66.
[11]金澤,金載潤,金亨鎬.針刺配合穴位注射治療頑固性面癱的臨床研究[J].中醫(yī)藥信息,2003,20(3):38-38.
[12]牙祖蒙.穴位針刺對面神經(jīng)再生影響的實驗研究[J].針刺研究,1999,24(2):111-115.
[13]姜勁峰,王玲玲,徐斌,等.抗炎—艾灸溫通的效應機制[J].中國針灸,2013,33(9):860-864.
[14]楊萬春.針刺配合穴位隔姜灸治療頑固性面癱的臨床觀察[J].中國中醫(yī)基礎(chǔ)醫(yī)學雜志,2013,19(5):545-5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