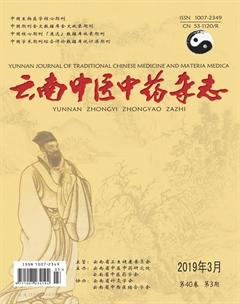基于針刺治療慢性疲勞綜合征的現狀探討
李梓萌 朱鳳亞 湯莉潔 吳曦
摘要:近年來,慢性疲勞綜合征(CFS)的發病率呈快速上升趨勢。通過CFS的免疫機制研究和主流治療方法進行小結,進一步探討針刺治療CFS的優越及不足,并為今后的研究工作提出一些參考意見。
關鍵詞:慢性疲勞綜合征;免疫機制;治療方法;綜述
中圖分類號:R245.31?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7-2349(2019)03-0088-04
慢性疲勞綜合征(chronic fatigue syndrome,CFS)是以不明原因引起的反復或持續發作6個月及以上的慢性疲勞為典型表現,且伴隨低熱、頭痛、咽痛、淋巴結痛、關節疼痛、肌肉酸痛、睡眠障礙、焦慮抑郁等多種軀體及精神神經癥狀為特征的的臨床綜合征[1-2]。CFS的全球患病率約為0.8%~3.5%,發病率約為0.4%~1%[3-4]。一份來自美國國家科學院的報告顯示,CFS影響美國多達250萬人,每年直接和間接的費用多達17-240億美元[5]。隨著社會形態、生活方式的改變,導致人們承受更多來自生活、工作、學習上的高強度壓力,在這些綜合因素的影響下,CFS發病率呈不斷上升的趨勢,該病可嚴重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且帶來巨大的經濟損失。因此,美國疾病控制中心(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CDC)預測CFS將成為21世紀影響人類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故本文將系統闡述CFS的免疫機制研究進展和治療方法現狀,并結合大背景下的研究方向和趨勢,試分析未來針灸治療CFS的研究重點及注意事項。
1?CFS免疫機制研究概況
總結國內外對CFS的相關研究,專家學者普遍認同該病可能與神經-內分泌系統、免疫系統、病毒感染、能量代謝、抗氧化應激等有關。由于促炎性細胞因子產生特點與CFS的癥狀相似,都會出現疲勞、發燒、淋巴結腫大、肌痛、關節痛、睡眠障礙、認知障礙和情緒障礙[6],故CFS發病的免疫機制一直是研究重點之一。近幾年來,CFS的細胞因子水平異常成為研究的熱點,并取得一定進展。綜合相關報道,認為本病的產生主要因為自然殺傷細胞功能受損、活化的CD8+細胞毒性T細胞數量增加、各種自身抗體的存在以及各種促炎細胞因子的產生和增加[7]。研究發現,CFS患者的IgA、Igg,IgM 水平普遍降低,采用免疫球蛋白治療后癥狀改善[8];吳文忠等[9]通過針刺百會、關元、足三里等穴后,發現IgA、Igg,IgM水平均較治療前升高,而CFS患者相應的臨床癥狀明顯改善,證實了針刺治療CFS的有效性。國內王向義等[10]通過針刺CFS大鼠降低血漿T-bet表達水平,升高GATA-3表達水平,從而調節T-bet/GATA-3比值治療CFS有明顯療效。Montoya JG等[11]采用高通量測序技術對血清細胞因子檢測后發現有17種細胞因子與CFS的嚴重程度有關,其中瘦素(Leptin)的增加和抵抗素(Resistin)的下降與疲勞程度之間呈明顯的相關性;Hornig M等[12]采用相同技術對病程持續3年以上(長期組)和3年以下(短期組)的CFS患者進行分析,發現短期組中51種細胞因子中有28種表達上調,但長期組水平正常或低于正常水平,兩個實驗結果表明細胞因子水平的異常與疲勞程度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還存在爭議;Stringer EA等[13]對以往研究進行了補充,假設細胞因子中的leptin與疲勞程度呈正相關,連續25天對10名CFS女性患者進行抽血檢測,其結果精度高達78.3%,支持其假設。由此看出,免疫與CFS的發病機制以及針刺治療CFS的機制有極大的相關性。
2?CFS治療方法現狀
為了找到一個具有推廣性、科學性的方法,從目前來看,中醫治療包括單純針刺、針刺加艾灸、電針、溫針灸、針藥結合、針刺加推拿等方法,其他療法主要包括認知行為療法(cognitive behavioural therapy,CBT)、分級運動療法(graded exercise therapy,GET)、心理治療、抗氧化應激、抗炎抗病毒、抗抑郁抗焦慮治療、膳食補充劑、藥物療法、長時間休息療法等[14]。
在CFS治療方法眾多的情況下,針刺治療具有安全性高、療效顯著、操作簡便、價格低廉、接受度高等優勢,且在治療CFS上取得了明顯療效,并開始被廣泛研究。從國際上看,一項雙臂隨機對照試驗發現CFS患者在接受連續4周針刺治療后,其體力和腦力疲勞以及身體健康相關的生活質量的改善程度均優于對照組[15];另一項隨機對照研究對CFS患者連續針刺治療4周后,其生理功能、總體健康水平、認知功能、社會活動能力、心理健康及痛苦的感覺上都明顯優于安慰對照組[16];一篇關于針灸治療CFS的系統評價與meta分析結果顯示針刺較單純中藥、單純西藥、假針刺而言,更能夠改善CFS患者的疲勞及認知功能障礙,證實了針刺治療CFS的有效性[17]。在國內,基于傳統針刺、溫針灸、電針、針藥結合等方法治療CFS的研究非常之多,均有明顯療效。
CBT和GET在改善CFS患者疲勞程度及認知功能、提高患者生活質量上,其療效較為理想,但從患者的經濟能力及依從性上講,由于CBT價格昂貴且治療周期長,故難以廣泛普及和推廣;GET仍然需要長時間治療并且在患者耐受度上也存在考驗,因而患者接受度很低;在眾多藥物治療上一直存在爭議,首先沒有特異性藥物能有效治療CFS,如糖皮質激素、抗抑郁劑、月見草油、加蘭他敏、肌肉鎂補充劑、歐米加3脂肪酸補充劑均起調節作用,其作用機制也不確切,故推薦度低;而國內外單用飲食補充療法、心理療法及長時間休息療法治療CFS的臨床試驗較少,尚不能明確上述療法對CFS患者有積極影響[17-22]。
對于CBT、GET等療法來說,從患者的角度來看,沒有很好的依從性和經濟實力的支撐,將難以開展,因而針刺療法成為目前綜合性較好的一種治療方法。
3?小結
3.1?針刺治療CFS發病機制的建議?隨著CFS發病率的不斷上升,搞清CFS的發病機制仍是重中之重,盡管針刺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改善CFS的疲勞相關癥狀,國內外也從神經-內分泌、免疫調節、抗氧化應激、節律調整等方面對針刺治療CFS的作用機制進行了研究[23],但相互作用關系仍未明確。已有研究證實促炎性細胞因子與CFS關系密切且CFS的發病及嚴重程度與細胞因子水平的異常存在關系,但CFS的癥狀究竟是由于細胞因子水平的異常所致,還是說CFS引起了細胞因子的異常,或者說水平異常只是該疾病的偶發現象仍需進一步探索,細胞因子與CFS患者疲勞程度之間的相關性并未得到進一步證實,且通過針刺調節CFS疲勞程度的免疫機制尚不清楚。因此,從目前的研究水平來看,驗證CFS發病機制的研究結果,把研究的方向適當集中化十分必要。
3.2?針刺治療CFS臨床試驗的不足?在針刺治療CFS的臨床試驗中,我們除了看到其療效的顯著性外,在試驗上也暴露出諸多不足:(1)針刺治療CFS的作用機制一直含糊不清,諸多研究僅總結其研究結果是否為陽性,并未闡明其結果的科學依據。(2)技術層面,數據處理嚴謹度較差;國內涉及的專業設備及研究人員的專業度不夠成熟。(3)從實驗設計上來講,部分研究缺乏合理的分組及對照,統一標準、診斷標準和療效評定標準未能統一。國內很多研究報道都缺乏具體的細節闡述,如選穴依據、針刺深度、角度、操作手法、不良反應等;多數研究并未注明隨訪結果,且樣本含量太少,導致療效缺乏全面性及代表性[24-25]。(4)在治療方法上,國外大多進行單純針刺或電針治療CFS,而國內還有針藥結合、溫針灸、針灸加推拿等方法,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用針刺治療CFS的療效判定。(5)從管理層面,患者的依從性、數據的收集和處理、不良事件的應對措施等方面仍存在很大問題。
3.3?針刺治療CFS有廣闊的前景,確定規范的針灸治療體系是關鍵?在眾多治療CFS的方法當中,首先,中醫領域當中針刺療法在國際上的認可度更高,文化推廣更好,當前,很多國家已經開辦了針灸學校、醫院、診所,其傳播的力度更強,最主要在于針刺治療CFS療效顯著。(1)在國內,政府大力扶持中醫藥事業,筆者認為政府應加大對科研儀器設備的投入以及專業研究人員的培訓工作,先進的研究設備確保研究的準確性,專業的技術人員保證研究工作的嚴謹性;(2)加強對原始數據及實驗數據的管理,例如建立表格式管理方法,對試驗過程進行實時動態管理。針對試驗過程中的不同時期制定表格,包括篩選期的篩選表、治療期的治療記錄表、理化檢查記錄表、受試者復診時間表以及隨訪期的隨訪表等;(3)提高受試者依從性管理,盡可能保證數據的完整性,在納入時勿片面強調受試者的受益,對受試者承擔的義務應充分說明,避免倉促入組,并與受試者時刻溝通交流,維持已經建立的信任度,多為受試者進行心理疏導,防止其脫落,同時要制定好不良事件的應對措施。(4)在中醫整體觀念和辨證論治原則的指導下,以循證醫學為指導開展臨床試驗,加強針刺與不同手法相結合治療CFS的臨床研究,確定規范的針灸治療體系是關鍵所在。
以上通過對CFS的免疫功能的發病機制、治療方法以及針刺治療CFS相關研究的優缺點進行了小結,并給予相關建議,CFS是一組復雜的功能紊亂癥候群,探索出一條治療CFS的理想道路仍重而道遠,研究者必須做好各個試驗環節。
參考文獻:
[1]Fukuda K,Straus SE,Hickie I,et al.The chronic fatigue syndrome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to its definition and study[J].Ann Intern Med,1994,121:953-959.
[2]蔡德英.慢性疲勞綜合征針灸臨床研究進展[J].中國中醫藥信息雜志,2011,10(8):109.
[3]Bhui KS,Dinos S,Ashby D,et al.Chronic fatigue syndrome in an ethnically diverse population:the influence of psychosocial adversity and physical inactivity[J].BMC Med,2011,9,26-38.
[4]Capelli E,Zola R,Lorusso L,et al.Chronic fatigue syndrome/myalgic encephalomyelitis:an update[J].Int J Immunopathol Pharmacol,2010,23(4):981-989.
[5]Institute of Medicine.Beyond Myalgic Encephalomyelitis/Chronic Fatigue Syndrome:Redefining an Illness[M].Washington:National Academies Press,2015.
[6]Komaroff AL.Inflammation correlates with symptoms in chronic fatigue syndrome[J].2017,114(34):8914-8916.
[7]Loebel M,Grabowski P,Heidecke H,et al.Antibodies to β adrenergic and muscarinic cholinergic receptors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fatigue syndrome[J].Brain Behav Immun,2016,52:32-39.
[8]Trojani F T.The chronic fatigue syndrome[J].La Clinica Terapeutica,1994,144(4):373-376.
[9]吳文忠,陳益.針刺對慢性疲勞綜合征免疫功能的影響及臨床療效觀察[J].江蘇中醫藥,2013,45(10):58-59.
[10]王向義,劉長征,雷波.針刺對慢性疲勞綜合征大鼠血漿T細胞轉錄因子/GATA結合蛋白3表達的影響[J].針刺研究,2017,42(3):246-249.
[11]Montoya JG,Holmes TH,Anderson JN,et al.Cytokine signature associated with disease severity in chronic fatigue syndrome patients[J].PNAS,2017,114(34):E7150-E7158.
[12]Hornig M,Montoya JG,Klimas NG,et al.Distinct plasma immune signatures in ME/CFS are present early in the course of illness[J].RESEARCH ARTICLE,2015,1(1):1-10.
[13]Stringer EA,Baker KS,Carroll IR,et al.Daily cytokine fluctuations,driven by leptin,are associated with fatigue severity in chronic fatigue syndrome:evidence of inflammatory pathology[J].Journal of Translational Medicine,2013,11:93-103.
[14]Brkic S,Tomic S,Ruic M,et al.Chronic Fatigue Syndrome[J].Srp Arh Celok Lek,2011,139(3):256-261.
[15]Ng S M,Yiu Y M.Acupuncture for chronic fatigue syndrome:a randomized,sham-controlled trial with single-blinded design[J].Alternative Therapies in Health & Medicine,2013,19(4):2-6.
[16]Zhang w,Liu ZS,Xu HR.Observation on therapeutic effect of acupuncture of Back-shu acupoints for chronic fatigue syndrome patients[J].Zhen Ci Yan Jiu,2011,36(6):437-41,448.
[17]Wang TW,Xu C,Pan K,et al.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for chronic fatigue syndrom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BMC Complementary & Alternative Medicine,2017,17(1):163.
[18]Pae C U,Marks D M,Patkar A A,et al.antidepressants[J].Expert opinion on pharmacotherapy,2009,10(10):1561-1570.
[19]Revelas A,Baltaretsou E.Chronic fatigue syndrome:diagnosis and treatment[J].South African Family Practice,2013,55(1):53-55.
[20]Carruthers B M,Jain A K,De Meirleir K L,et al.Myalgic encephalomyelitis/chronic fatigue syndrome:clinical working case definition,diagnostic and treatment protocols[J].Journal of chronic fatigue syndrome,2003,11(1):7-115.
[21]Yancey J R,Thomas S M.Chronic fatigue syndrome:diagnosis and treatment[J].Am Fam Physician,2012,86(8):741-746.
[22]Steven R,Tuide C,Anthony C,et al.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Chronic Fatigue Syndrome[J].BMJ,2011;5:1-56.
[23]唐樂微,陳亮,韓亮,等.針刺治療慢性疲勞綜合征機制進展[J].時珍國醫國藥,2014(11):2750-2752.
[24]張寶文,瞿恒,苑迅.針灸治療慢性疲勞綜合征臨床研究現況[J].遼寧中醫藥大學學報,2017,19(10):182-184.
[25]毛楠,孫忠人.針灸治療慢性疲勞綜合征臨床研究概況[J].針灸臨床雜志,2009,25(8):5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