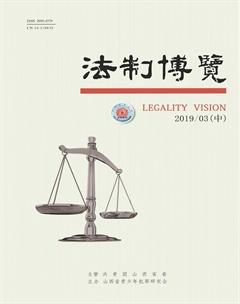論運輸毒品罪中“明知”的推定
摘 要:由于毒品犯罪的隱秘性,行為人歸案后往往否認主觀明知,因此毒品犯罪中對行為人主觀明知的認定歷來是審判中的難點和重點。本文從具體案例分析推定的適用,并對合理使用推定規則提出了建議。
關鍵詞:運輸毒品罪;明知推定;基本理論
中圖分類號:D924.3;D92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4379-(2019)08-0189-02
作者簡介:顏瑾瑾(1983-),女,漢族,云南昆明人,碩士研究生,云南大學,博士研究生在讀,昆明醫科大學,教師,研究方向:地方司法制度。
一、從一則案例談起
公訴機關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檢察院。被告人馮某,女,河南省××縣人。公訴機關指控:2013年1月31日,被告人馮某乘坐車牌號為豫××××昆明至河南駐馬店的客車,途經昆曲高速公路昆明北收費站時被公安民警抓獲,在其攜帶的一紙箱內的茶葉筒里查繳毒品甲基苯丙胺凈重11220克。同年2月3日,當該客車到達河南駐馬店市后,駕駛人員在車上發現一個無人認領的粉色旅行箱,客運公司工作人員將該行李箱交由河南駐馬店警方,警方在該箱內查獲被告人馮某的內褲一條和毒品甲基苯丙胺凈重3699.37克,平均含量為18.25%-19.62%。本案共查獲毒品甲基苯丙胺凈重14919.37克。
對于本案而言,被告人未作過有罪供述,自始至終否認主觀明知的運輸毒品案件,因此圍繞馮某主觀上對毒品是否具有明知性認識,形成了兩種不同的意見。如何運用推定認定毒品犯罪中的主觀明知一直是司法實踐中的難題。這就要回到推定制度本身來討論與分析。
二、何謂推定
陳瑞華認為推定是一種根據所證明的基礎事實來認定推定事實成立的方法。張保生把推定界定為標志基礎事實與假定事實之間法律關系的證據法范疇。也有學者對推定作如下界定:推定是指依據法律直接規定或經驗規則所確立的基礎事實與待證事實之間的常態聯系,當基礎事實確證時,可認定待證事實存在,但允許受不利推定的當事人舉證反駁的一項輔助證明的標準化規則。
從上述定義中,我們可以總結出推定機制具備以下幾個特點:一是推定的前提是基礎事實的成立,從而推定出待證事實。二是基礎事實與待證事實之間,并沒有建立必然的因果關系,雖然也會有經驗基礎上的邏輯聯系,但可能存在一種邏輯推理上的跳躍。三是推定事實只有在推定不利一方無法提出反證的情況下才成立。推定的反對證據一旦確認,該推定就如氣泡爆裂,不再發生效力。
推定作為一種證明的方法,是否有存在正當性,是否與無罪推定原則相違背。龍宗智認為應肯定訴訟中包括刑事訴訟中推定的意義。因為這些特殊的推定,基于經驗基礎上的高度蓋然性、基于證明上過于困難,也基于刑事政策實現的需要,是可以作為無罪推定原則的例外而成立的。第一,如對于毒品案件而言,毒品的持有人對所持有物品的性質通常比其他任何不接觸該物品的人更了解,其不了解持有物品的性質可能性雖然存在,但要小得多,這就符合經驗上認知規律。第二,從證明困難的角度來看,對于特定犯罪構成要件事實,證明起來是非常困難的。如毒品案件多是在一對一的情況下進行,除了犯罪嫌疑人供述外,很少有證實犯罪的直接證據,易開成孤證。而推定就可跳過司法證明,直接推定待證事實,從而減輕了公訴機關的舉證困難。第三,自由、秩序、正義、效益等是刑事政策的價值目標。而我國刑事政策經歷了從以消滅犯罪為目標的理想型階段到以預防犯罪為目標的現實型階段等兩大階段。在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總的刑事政策提出后,出現了重在教育預防,堅持保障公民權利與保護社會秩序相結合的時期——突出強調依法從重從快嚴厲打擊犯罪,維護社會秩序穩定的時期——到突出預防犯罪,堅持打防結合,堅持依法辦事,堅持保障公民權利與保護社會秩序相結合的時期等曲折發展的三個時期。對于一些需要嚴厲懲罰的犯罪案件,如果犯罪嫌疑人零口供,就要求控訴機關收集其他證據加以證明,不僅會極大地浪費司法資源,也會常常導致訴訟證明走入死胡同。這與嚴厲打擊某類犯罪的刑事政策是不相符的。因此相對于嚴厲打擊某類犯罪,維護社會秩序的刑事政策需要來說,進行推定也是有可取的價值的。
三、推定在本案中的運用
在本案中,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根據被告人馮某的犯罪事實、情節及對社會的危害程度,作出了以下判決:一、被告人馮某犯運輸毒品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二、查獲的毒品甲基苯丙胺14919.37克予以沒收。
本案審判人員之所以做出上述判決,正是基于查證的基礎事實合理地運用了推定來認定被告人主觀明知的事實,對進一步完善毒品犯罪主觀明知推定制度、準確打擊毒品犯罪,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價值及現實意義。具體分析來看,其推定的過程如下:
(一)查證的基礎事實
第一,在案證據證實被告人馮某從景洪上昆明攜帶了兩件行李即藏匿有毒品的紙箱及行李箱。
第二,被告人馮某和接送其去旅館、客運站的黑車司機方某認識,并且在案發期間有多次通話聯系。
第三,多名證人可以證實幫被告人搬運過兩個裝有毒品的行李即紙箱和行李箱。
第四,被告人送給方某的茶葉與河南警方出具的茶葉筒照片及昆明警方出具的物證照片,可以證實從被告人馮某攜帶的查獲的毒品藏匿方式及所藏匿毒品的茶葉筒都是一致的,毒品都是藏匿在暗紅色的茶葉筒中,而且行李箱中5個沒有藏匿毒品的米黃色茶葉筒,與被告人馮某送給方某的米黃色茶葉筒也是一致的。
第五,DNA鑒定證實從藏匿毒品的行李箱內查獲的內褲系被告人馮某所有。
(二)庭審過程
被告方未作過有罪供述,開庭之前對客觀事實和主觀明知都予以否認,庭審過程中在大量證據面前承認客觀事實,但還是堅決否認主觀明知。然而,其辯解并不能反證其不具有主觀明知運輸毒品的事實。理由如下:
第一,被告人馮某在被公安機關查獲其攜帶藏匿毒品的紙箱時,堅決否認還攜帶行李箱,并且其稱已查獲的這個紙箱是他人在客運站才交給她的,對于其所作的與客觀事實完全不相符的謊言,其始終不能做出合理解釋。
第二,被告人馮某一直否認與黑色司機方某認識及有通話聯系,對于其為何說謊,其一直無法解釋。
第三,被告人將沒有藏匿毒品的米黃色茶葉筒送給了方某,這就說明被告人馮某主觀上對毒品不僅明知,而且明知其中的暗紅色茶葉筒里才真正藏匿有毒品。
第四,公安機關通過檢查茶葉筒中茶葉的重量才查獲了紙箱中所藏匿的毒品,被告人自己顯然是清楚其中的重量差別,而且這兩件裝有毒品的行李一直在被告人控制之下,其所作的辯解,被告人無法做出合理解釋。
第五,從藏匿毒品的行李箱內查獲被告人的內褲,被告人馮某將這樣的隱秘貼身衣物放在藏匿有毒品的行李箱內,其還堅持否認主觀明知,顯然不合常理。
因此通過上述環節的論證,審判人員認為從上述的基礎事實已經能夠推定被告人主觀上明知是毒品,而被告人對其所作的無罪辯解無法反證其不具有“主觀明知”。本案審判人員根據在案證據證實的基礎事實與推定事實之間的常態聯系,按照經驗法則和邏輯規則作出的認定被告人馮某具有運輸毒品的主觀故意是準確的。
四、推定在運輸毒品案件中運用的啟示
根據我國犯罪基本理論和刑法分則關于運輸毒品罪的規定,主觀上的故意是運輸毒品罪的必要構成要件,須認定行為人主觀上明知是毒品為前提。而“明知”包括“知道”和“應當知道”。即要求行為人主觀上知道、認識到、意識到或者懷疑到可能是毒品,而不要求確切地知道具體的毒品的種類、含量、數量等等。只要行為人認識到、意識到、或者懷疑其所運輸的、攜帶的物品可能是毒品,就能認定行為人主觀上“明知”,從而構成運輸毒品罪。
[ 參 考 文 獻 ]
[1]徐丹丹.販賣、運輸毒品罪中“明知”的認定[D].蘇州大學,2016.
[2]論運輸毒品罪死刑的適用——兼評《武漢會議紀要》中的相關規定[J].西部法學評論,2016(3):73-83.
[3]袁琴武.運輸毒品罪若干問題研究[J].法制與經濟,2016,37(7):3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