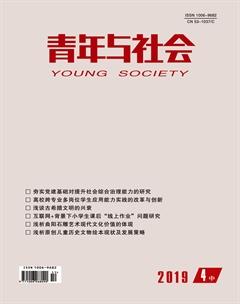地方政府債務發展歷程、風險測度及防范
早期工業化國家發展歷程表明,信貸(或負債)可以通過用于支持投資以驅動經濟增長(張曉晶等,2019)。按照弗里德曼的貨幣觀點,信貸(或負債)短期內驅動經濟增長;然而其過度膨脹之后,其往往演變成為經濟體系中的“阿喀琉斯之踵”(Tobin,1989)。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主要發達國家紛紛采取去杠桿的方式以擺脫危機;但就當前全球經濟形勢來看,各大經濟體杠桿率高企、債務攀升再次成為令人擔憂的全球性現象,債務積累對經濟增長呈現出顯著甚至是“加速式”的負面影響。
《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以下簡稱“《預算法》”)自2015年1月1日起實施后,地方政府舉債的唯一合法方式明確為發行地方政府債券(一般債券、專項債券),即從立法層面將地方政府顯性負債納入了預算管理體系。2018年8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的意見》(中發〔2018〕27號)以及《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關于印發<地方政府隱性債務問責辦法>的通知》(中辦發〔2018〕46號)兩個文件接連下發,標志著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進一步明確納入監管。地方政府顯性債務和隱性債務在大的框架下納入了綜合管控和治理。系統梳理地方政府債務發展歷程,厘清地方政府債務的口徑和當前債務風險情況,對地方財政高效持續穩健運行有著重要意義。
一、地方政府債務發展歷程
(一)體制改革
從“財政包干”到“分稅制”。作為基礎的財政制度,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時期,我國從1950-1952年、1969-1970年實行統收統支體制(其余年份實行略有改動的分類分成或總額分成)。改革開放之后,“承包”成為這一時期的改革主調,作為一種過渡性的財政制度(賈康,2008),我國開始實行劃分收支,分級包干的“包干制”(孫雷,2008)。這一的體制顯著推進了當時社會經濟發展,但也間接導致了中央財政的難以為繼和1993年的嚴重經濟過熱,進而催生了“分稅制”改革。
(二)債務凸顯
1994年分稅制改革,旨在解決中央財力不足問題。同時導致“事權下沉、財權上移”,GDP競賽、收入激勵和晉升機制,助推基建持續投入并導致資金缺口不斷擴大,地方財政壓力凸顯。與此同時,1995年和1996年相繼實施的《擔保法》和《貸款通則》進一步限制了地方政府向銀行貸款融資的途徑。地方政府通過平臺公司發揮投融資職能的需要也就應運而生(周岳、肖雨,2019)。值得注意的是,隨著2008年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四萬億計劃”落地,中央逐步放開地方“自發自還”政府債券,以解決地方政府配套資本金融資難題。相關監管政策也允許政府融資平臺通過市場機制籌措配套資金,致使地方政府利用下屬的企事業單位或者融資平臺公司陸續借助各類渠道(包括城投債、專項建設基金、銀行信貸、PSL政策工具、非標融資甚至互聯網金融等各類金融工具)進行債務擴張。然而,伴隨著2010年后的歐債危機,國內高信貸密集型增長導致的房地產泡沫和通脹潛在危險,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焦點從保增長轉向防風險;審計署在2011年和2013年對地方政府債務進行兩輪審計的基礎上,逐步明確建立政府性債務管理制度并實施分類處置。
(三)監管流變
嚴格意義上來說,改革開放以來曾有過三輪地方政府債務監管(勵雅敏等,2018)。第一輪監管始于“四萬億”刺激后舉債過多,為避免地方政府財力的透支以及防范債務風險,2010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正式提出“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監管發文規范融資平臺貸款行為,禁止違規或變相擔保;但在表內貸款受限情況下,依托工業化城市化等抵押品密集型行業,表外信貸興起,銀行借助非銀通道向平臺輸送資金。第二輪監管于 2013 年開啟,在2013年政府性債務審計結果基礎上通過債務甄別,控制新增平臺債務規模并將隱性債務顯性化,按照額度管理的思路逐步使地方政府舉債行為限定在國務院確定的限額內。為了防范地方債務風險的發生,打贏“防風險”攻堅戰,2017年以來進入第三輪監管,加大金融去杠桿、平臺融資渠道穿透監管力度,從非標業務的資金方、通道方和融資方進行綜合管制,嚴控地方政府違規或變相舉債;同時,從2018年8月下旬起,國家審計署全面開啟新一輪地方政府隱性債務審計工作,隨后財政部也陸續下發《財政部地方全口徑債務清查統計填報說明》等文件,全面統計監測各地政府截至2018年8月31日的隱性債務余額、資產情況。
二、地方政府債務規模特征和風險測度
(一)規模特征
審計署于2011和2013年對地方政府債務進行了兩輪審計,一是對改革開放至2010年底尤其是1996年以后的地方政府債務進行了全面的梳理,二是對截止2013年6月底的地方政府債務規模和結構等情況進行了公開。同時,財政部在全國范圍內對截至2014年底的存量債務進行了一次性清理甄別工作,將地方債務分門別類納入一般公共預算和政府性基金預算管理。根據刁偉濤2018整理的1996至2017年地方政府債務規模及其增長情況,地方政府債務從1996年末的1502.37億元,按年復合增長25.08%的速度,到2017年達到165099.8億元,靜態增長了將近109倍。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1月末,全國地方政府債務余額188041億元,非政府債券形式存量政府債務3151億元。值得說明的是,2009年的地方政府債務規模跳躍式增長至與中央政府債務相當,然后在2011年開始超過中央政府債務并保持至今。
(二)風險測度
對于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的評估測度有不同的指標和指標體系,被普遍認可并廣泛采納的兩個直接指標是負債率(債務余額與當年GDP的比值)和債務率(債務余額與當年地方政府財力的比值)。其中,債務率指標根據分母選擇的口徑不同,可細分為自有財力負債率和綜合財力債務率,收入口徑的債務率和支出口徑的債務率,一般債務率和專項債務率三類。但利用負債率和債務率指標體系對地方政府債務風險進行測度,也有較大缺陷和不足。負債率指標從宏觀視角出發,衡量政府債務相對于經濟體量的大小,側重于反應政府債務的資源配置及其對經濟增長效應,但難以反應債務償還和可持續管理的相關狀況;同時,GDP指標也難以具體對應政府債務的分級分層情況。相比而言,債務率指標既能夠反映以償還壓力為核心的債務風險情況,也能夠分解出不同層級地方政府的債務風險,但是其衡量的債務風險更多是相對于政府財力規模的相對大小,不能反映債務風險的絕對規模。
三、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的建議
綜合而言,我國地方政府債務規模(顯性部分)已得到較為有效的控制,整體債務風險有所降低;但隨著區域經濟運行和財政收支的進一步分化,經濟周期和地方政府債務周期疊加,債務風險的不均衡狀況在逐步顯現并呈現出一定的惡化趨勢,更需要加強債務風險預警防范和應急處置。
(一)嚴控債務規模和保證債務可持續
一是強化地方政府的預算管理,各級地方政府在編制債務預算時,應同步明確提出債務的償債資金來源和償還計劃,同時加強債券發行信息披露的質量和深度。二是依據債務率指標對地方政府債務實施分類管控,進一步健全地方政府債務監測、風險評估及預警機制,并制定行之有效的債務風險防控和處置方案,適時采取債務重組、不良債務減記等救助措施化解相關債務。三是加大政府資產處置力度,按時正常還本付息,保證債務可持續。在編制地方政府資產負債表的同時,加強對政府資產或股權的整合、重組和盤活,理順政府資產變現機制,如通過加強土地收儲和盤活存量,處置低效閑置資產和部分非辦公資產等,加快推進經營性國有資產的證券化,多渠道籌集資金,保證地方政府債券到期本息的及時全額償還。
(二)深化專項債券限額管理和發行主體自我約束能力
由于專項債券更多以項目收益為支撐,需要項目收益與融資自求平衡,這使得項目收益對專項債券的發行規模已形成了有力的約束;同時按權責對應,發債、用債和償債主體應逐步趨同,因此建議逐步賦予縣市級政府自主發行專項債券的權利,同時逐步取消專項債券的限額管理。
(三)加強債務審計監督和違法違規舉債的問責力度
債務管理應結合財政預算執行、決算審計、領導干部經濟責任審計等環節,加大監督處罰力度。另外,應持續對地方政府違法違規的舉債和擔保始終保持高壓態勢,嚴厲查處部分地方政府通過回購安排、保底承諾、固定回報、明股實債等進行的變相融資和違規舉債行為。
參考文獻
[1] 張曉晶,劉磊,李成.信貸、杠桿率與經濟增長:150年的經驗和啟示,比較,2019年(1)期.
[2] 刁偉濤.中國地方政府債務風險(2014-2017)[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
[3] 特納.債務和魔鬼:貨幣、信貸和全球金融體系重建[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
[4] Friedman,M.and A.J.Schwartz,1963,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867-1960,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5] Tobin,J.,1989,“Review of Stabilizing an Unstable Economy by Hyman P.Minsky”,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27,pp.105-108.
作者簡介:肖劍(1988- ),男,云南昭通人,中級經濟師,碩士,云南交通發展產業基金股權管理有限責任公司,副總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