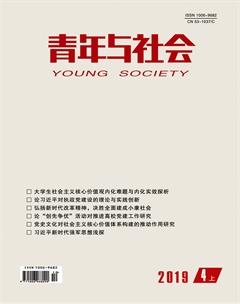試論王夫之詩歌理論的革新
摘 要:王夫之對詩歌理論的革新促進了后世詩歌創作的發展。他對“興觀群怨”說進行新解,將四者統一起來進行分析,認為“興”作為詩歌創作最重要的一環,可以成為詩與非詩的判定標準,通過“心之元聲”的創作理念,分析了詩歌創作的源泉與本質特征,并且利用“現量說”將情景再一次深度融合,進行真性情的客觀書寫,同時對后世詩歌的創作進行了規范,豐富了詩歌的創作理論。
關鍵詞:王夫之;興觀群怨;情景
王夫之處在明末詩歌轉型的關鍵時期,他所代表的革新派不僅摒除了復古繁冗的創作理念,更是將開放多元的人文思想灌注其中。明代詩歌創作受程朱理學影響極深,官學理念影響下的詩人創作更是走入刻板嚴謹的封閉空間。王夫之打破思想禁錮,開辟了獨特的詩學思想。他從對“興觀群怨”說的繼承中找到詩歌發展的廣闊舞臺,并將“興”作為考量詩與非詩的標準,通過對情與景的關系分析,對詩歌理論作出革新,極大的推動了后世詩歌的創作。
一、“興觀群怨”說的再發展
“興觀群怨”說是孔子對于詩歌社會作用的高度總結,這種對詩歌的認識促進了社會教育的作用,也促使中國早期詩歌理論的形成。王夫之在此基礎上,接受公安派理論的影響,逐步形成獨有的新“興觀群怨”理念,不僅強調詩歌要著重表現情感,更要規范抒情,積極健康。
“興觀群怨“說首先強調詩歌的社會功用,通過對禮樂、祭祀等活動的紀實性描寫,對百姓進行宣傳教化,鞏固上層統治。“興”可以肆意抒發情感,觸物興詞,引起傳唱。“觀”著眼于社會現實,對社會不同階層進行觀察,反映時代特色。“群”激發的是人們共同的思想情緒,無論是農事耕桑或是節日慶典,人們都能找到所謂的文化認同。“怨”則對社會問題進行剖析與批判,揭露腐朽統治和殘酷暴政。這四者統領了詩歌的創作,對古代詩風的發展具有總領概括的意義。但是“興”、“觀”、“群”、“怨”四者并未真正融合,孔子提出這個理念的目的依然是恢復禮樂、鞏固綱常。這四者的割裂使得詩歌理論的發展逐步走向封閉,尤其以明代后期詩歌為代表,前后七子、公安派等人的詩歌創作理念深受其影響,無論是注重教化意義還是直抒情感,都失去了節制與理性,王夫之通過對“興觀群怨”再次解讀,提出了“攝興觀群怨于一爐”的思想,打開了詩歌創作的新局面。
“王夫之非常重視文學的社會教育作用。他主張詩歌表現感情的同時,還特別強調詩歌的情應當是積極的、健康的,必須具有”動人興觀群怨“的作用。”明末詩文理論主要集中于對前后七子復古主義和公安派“性靈”書寫的討論中。王夫之將二者的特點集中起來,立足于解決文學創作的源泉問題。他批判了前后七子模擬復古的刻板思路,主張獨創。同時關注公安派“性靈說”的創作特征,注重情感抒發,但同時認識到情感的肆意抒發不加節制將會失去詩歌創作的意義。受李贄“童心說”的影響,他認為詩歌是人的“心之元聲”。王夫之強調真實情感的自然流露,主張不俗于“性靈”的更注重現世的抒情,而非空無一物獨說情。
他在《古詩評選》中對謝靈運的《東陽溪中贈答二首》進行評論:“二十字,括一篇檄文在內!看他瀟灑中血痕迸出!所持以動人者,亦此足矣。此而不動,更數千言,又孰聽之?始知陳琳未是俊物。”王夫之強調的真情是要超越功利的審美性質,他立足于個人與社會對詩歌的審美意義,批判的繼承了公安派獨抒性靈的特色,對其過于俗誕的部分加以否定,贊成高雅脫俗,重性情的創作方式。
王夫之將“興觀群怨”綜合在一起進行再解讀,他認為這四者不能獨立存在,應該是相互補充,互相影響,從而激發詩歌的教育和美學意義。傳統的詩學理念認為“興觀群怨”代表的是四種完全不同的社會功能,忽略了他們的必然聯系。王夫之從它們本身的美學意義入手,系統闡釋了他們之間的統一性。
二、詩歌標準“興”的確立
王夫之認為是否可以“興”是詩與非詩的區分標準,他認為“詩言志,歌詠言,非志即為詩言即為歌,或可以興,或不可興,其樞機在此。”王夫之認為詩歌意向的生成就在于“興”,先秦時期,“興”的本意為“起”,祭祀時用于情感的烘托與表達。到《詩經》創作的繁盛時期,“興”則有觸物興詞,引發詩人歌唱的意義。至此延續,“興”的內涵愈加豐富,王夫之則將其提到了更高的位置。
“興”在詩歌創作中的豐富內涵決定了它作為詩與非詩的標準。首先,觸物興詞是“興”的基本表現形式,情感和觸發情感的形式相結合,客觀事物觸發了詩人的創作熱情,引起詩人的歌唱,例如《小雅·鴛鴦》、《周南·桃夭》等。其次,“觸物”也是激發真情創造的條件,寄情于景,由景生情是最自然的情感表現方式。王夫之認為:“有識之心而推諸物者焉,有不謀之物相值而生其心者焉。知斯二者,可與言情矣。天地之際,新故之跡,榮落之觀,流止之幾,欣厭之色,形于吾身以外者化也,生于吾身之內者心也;相值相取,一俯一仰之際,幾與為通,而勃然興矣。”他認為人和自然萬物相知相協,才能物我相諧和情景交融。
詩歌創作需要真情,會心,才能達到情感的宣泄。而意向作為重要一環,促使詩人“即景會心”,通過意象書寫,達到得情、會心的效果。詩人創作講求心與物的相互交流,主客體之間得到內在溝通,審美活動自然而然的進行,于無意識之中發掘萬物美好所得來的靈感比刻意堆砌要來的更加真實。王夫之認為“興”的一系列反應應該是有意識與無意識的結合。創作者作為主體,需要一部分有意識的行為,為讀者創造想象世界,而情景交融作為靈感的觸發又是無意識的操作行為,它讓情感更豐富立體,使審美創作在不知不覺中完成,同時影響讀者的審美體驗。這是感性與理性的結合,意象在這里發揮著重要作用。
王夫之在對“興”的獨特解讀之上,對意象的產生進行分析,他多次強調詩文創作中“意”的重要性,認為“意”是真正激發詩人主體創作性的環節,通過無意識的靈感融入,更具體更形象的展示豐富的情感世界,但他并不認為意象是虛無抽象的,“意”必須與情感結合,隱含于情,不能空洞寫意,當然也就不能空洞說情,他強調真情真心,必須結合現實情況,并且指出公安派“獨抒性靈”的局限,抒發真性情而不是毫無節制的空談,這才能強化詩歌的社會作用。
三、“情”與“景”的相和關系與對后世詩歌的影響
王夫之通過挖掘“興”的統領作用,用意象的真情書寫構建了情景交融的創作模式。他的“現量說”也成為了直覺關照的重要理論。王夫之詩學創作理論的突破主要集中在情與景的相和關系中,他認為情景要高度統一,不能夠造景或造情,要注重自然的情感發展,才能做出真情真性的詩歌,這對后世的詩歌創作影響深遠。
情景交融的最高境界是兩者“妙合無垠”、難分物我的“物化”狀態。但既要客觀描寫自然景觀,又能準確的直抒胸臆,抒發強烈情感,做到二者統一是很困難的。有部分詩歌都存在刻意造景或者為景強抒情的尷尬,王夫之認為最難的是不帶有創作者的主觀色彩,而是客觀描寫事物,做出情感的自然流露。因此他提出“即景會心”的現量說,用來解釋情景交融是一瞬間涌出的驚喜,沒有刻意勾畫,也沒有虛構的成分。情景必須統一,不能太過割裂,容易造假情假景,或者無法突出重點。他主張對直覺和靈感的把握,做到渾然天成,少些雕琢之氣。
王夫之抓住的是詩歌創作的細微之處,他在《夕堂永日緒論內編》中說:“‘池塘生春草,‘蝴蝶飛南園,‘明月照積雪,皆心中目中與相融浹,一出語時既得珠圓玉潤。要亦各視其所懷來而與景相迎也。”王夫之強調物我合一,情景的自然交融才能迸發靈感,產生真切的情感,創作情真意切的優秀詩篇。他認為并不能預先設定或者強行抒情,這樣破壞了詩歌應有的審美,這才是詩歌真正的社會功用,用真情打動人心,用景與意象構建一個細膩的情感世界。王夫之非常注重詩人創作的實踐經歷,認為作家的豐富經歷和親身體驗更能獲得創作的源泉,對現實生活的觀察更能刺激詩人的創作欲望,同時又要極盡克制和隱忍的抒發情感,才能產生客觀的審美意識。
王夫之對于詩歌理論的革新做出極大貢獻,他從客觀現實角度出發,重視真實情感的自然流露,既批評了前后七子的復古擬古思想,又批判的繼承了公安派的獨抒性靈,并從中找到最恰當的抒情方式,那就是要渾然天成、物我合一,不刻意追求造景,也不太過極端的主觀抒情。他的“心之元聲”說對李贄和公安派的學說進行革新,擯棄了只顧堆砌而毫無真情的陳詞濫調,并開啟了新派的詩歌創作模式,由此對后世詩歌的多樣化發展進行了開拓,產生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參考文獻
[1] 錢穆.宋明理學概述[M].九州出版社,2010年.
[2]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M].百花文藝出版社,1999年.
[3] 戴鴻森.姜齋詩話箋注[M].人民出版社,1981.
[4] 張少康.中國文學理論批評教程[M].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9年:第234頁.
[5] 王夫之.古詩評選[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13頁.
[6] 王夫之.唐詩評選卷一評孟浩然《鸚鵡洲送王九之江左》[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2頁.
[7] 王夫之著陳良運編.唐詩評選詩廣傳[M].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5年:第878頁.
[8] 李建中.中國古代文論王夫之夕堂永日緒論內編[M].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303頁.
作者簡介:王婧瑩,新疆大學人文學院,中國語言文學2017級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