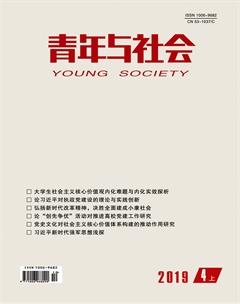費希特對康德哲學的超越
高天
摘 要:費希特是德國古典哲學中的一位重要的哲學家,他的知識學中首次用理性演繹的方式超越了康德哲學中的現象界與物自體之間的割裂,通過知識學原理中的主體辯證法,實現了二者的融合,同時為黑格爾到馬克思的辯證邏輯的開啟提供了方法論基礎,文章通過對知識學中三個原理的深入分析,探尋費希特知識學原理中的邏輯脈絡,及其對康德哲學的發展與超越,進一步豐富和深化對馬克思辨證思維方式的理解。
關鍵詞:知識學;自我;非我
近代以來,數學和自然科學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由于在科學領域內發生了一次思維方式上的變革。這場革命的實質正是在于:“幾何學家意識到他既不是研究經驗中的感性的幾何圖形,也不是對幾何圖形的概念進行分析,而是依據理性事先規定好了的概念,不依賴于經驗而直觀中‘構造出幾何圖形,然后從這種圖形引申出種種幾何學的先天綜合判斷。”同時,自然科學家們也認識到“他們依賴的不僅是經驗的觀察,也不只是對概念的分析,而是以理性確定的原理為依據,提出問題,然后根據原理設計實驗,強迫自然回答這些原理提出的問題,從而得出自然科學的判斷。”康德指出正是由于這場思維方式的革命,數學和自然科學才建立起統一的科學范疇,但是大陸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兩派哲學的發展的懷疑論的危機,讓科學命題存在的普遍必然性缺失根基,陷入了不可實證理論局限之中。此時,孕育于宗教載體中具有思辨、超驗特性的德國哲學開始運用理性批判考察人的認識,為科學知識的普遍必然性奠定基礎。康德指出,只有提高人的思維方式,才能解決這一理論困境,他提出人類科學的根基恰恰在于人主體自身,科學思考的對象是物,而哲學思維的對象在于人自身。因此哲學作為科學何以可能的依據,必須對人的主體思維能力進行反思和審視,展開理性的批判。因此康德提出:“我坦率地承認,就是休謨的提示在多年以前首先打斷我教條主義的迷夢,并且在我對思辨哲學的研究上給我指出來一個完全不同的方向。”他通過考察普遍性科學知識的知識結構,重新批判了以往哲學的認識論體系,指出認識既不是理性主義中堅持的“某種形式”,也不是經驗主義堅持的“經驗內容”,而是內容與形式(架構與質料)的統一,因此他在認識領域中展開了一場思維方式的革命,將人的認識形式從被動反映顛覆為感性直觀——時空觀。
康德重新批判了以往認識領域的反映論,對時空的存在提出了“形而上學的闡明”,提出人的感性認識形式,時間和空間先于經驗世界而存在,“空間表象不能從外在現象的關系中經驗地獲得,相反,這個外在經驗本身只有通過這個表象才是可能的。”它是人對一切事物感知的前提。因此空間提供的是人認識事物的外部直觀,而時間為這一空間的持續存在提供基礎。“只有在時間的前提之下我們才能想象一些東西存在于同一個時間中(同時),或處于不同的時間內(相繼)。”因此,人所認識的經驗世界必然以時間和空間的先驗認識形式為條件。在這里,空間提供物體的廣延性而時間提供現象的持續存在,因此,人主體可以憑借存在于自身的先驗的感性認識形式時間空間來認識整個現象世界。但是,客觀存在中的物自體世界是人的認識所無法達到的。
費希特在知識學原理中,通過理性的演繹,解決了康德哲學中的二元分裂。第一原理:自我設定自己。他從形式邏輯中的同一律命題出發,即A=A(A是A)展開反思,只有當A與A的內容相等的時候,命題才能夠成立,因此,在這個命題中只體現出了形式卻沒有體現內容,因為A本身的內容屬于未知,因此只有在人自我在下判斷的時候才能夠形成“邏輯主語”,此時這個命題成為了自我按照必然聯系所進行的判斷即“活動”,這樣,這個用來做判斷的“活動”一定存在于人的“自我意識”之中,并且只能夠由自己提供給自己,此時A本身才是存在。因此在命題A=A中主詞與賓詞之間存在“活動”時,二者才具有同一性,而這種同一是建立在自我的同一性基礎之上的,這個同一的內容就是“我是我”。“A=A”與“我是我”這兩個命題在形式上完全相同,但是在“A=A”中如果沒有自我意識中的“活動”便無法確定A的內容。但是在命題“我是我”中則是形式與內容的雙重確定,因此費希特推出“我是我”才是永久有效的“絕對”命題,它表明了“自我”的“實在性”。“一切意識經驗的事實的理由根據就在于,在自我中的一切設定以前,自我本身就先已設定了。”因此自我在自身的活動中直觀到了自身的存在,并且自我在意識中將自己“擺放、確立”起來。“設定著的自我與存在著的自我是完全相同的,是同一個東西。”因此“自我就是自我”具有無條件的絕對性,這個“絕對”的“自我”的存在,正是人類一切精神活動的根據所在。費希特指出,知識學的第一原理在形式上的“絕對性”使邏輯學的同一律具有普遍有效性。
第二原理:自我設定非我。在這里,他從形式邏輯的矛盾律出發即命題“非A不=A”進行反思的過程。“基于同一個理由,第二原理也像第一原理一樣,既不能證明也不能推論。因此我們在這里,恰恰同前面一樣,也從一根經驗意識的事實出發,并且我們根據同樣的權力按照同樣的方式來處理這個事實。所以,非A以A為前提存在,當我們提到非A的時候必然已經假定存A,因此這一命題在形式上是無條件的存在,但是在內容上,它的存在卻是有條件的。對于非A行動的設定是“反設定”(Gegensetzen),同樣是一種“本原行動”。在第一原理已經設定了“自我”,此時的“反設定”需要對“自我”展開直接的“反設定”。所以自我的“反設定”即“對設”只能是“非我”,它對自我進行否定和限制。這個“非我”就是作為對象出現在意識中的客觀世界。當絕對自我“設定”自我,又“對設”出非我,在此,費希特證明了“自我”中不僅包含知識的形式而且包含著知識的內容,此時已經完全消解了康德的“物自體”。
第三個原理:自我在自身中設定一個可分割的非我與可分割的自我相對立。“第三條原理幾乎是完全可以證明的,因為它不像第二條原理那樣有一個命題,而是由兩個命題規定的。所以,在第一原理中的無條件的“絕對自我”出發,設定“自我”的同時對設出“非我”,此時與“非我”相對立的那個“自我”必然受到限制,從而成為一個“有條件”的“自我”。而第三原理正是由先行的兩個原理所規定,“絕對自我”在自身中設定出一個有限的自我與一個有限的非我相對立。在意識的同一性中有限的自我與非我從屬于“絕對自我”,由“絕對自我”統一在一起。通過三條原理,費希特完成了將相互對立的“自我”與“非我”“先驗的”綜合起來了。完成了知識中最高的綜合,其他所有的綜合都必然包含在這個最高的綜合之中。費希特以主體為能動的出發點,闡發了三種活動。自波墨之后,費希特又一次將思辨的傳統融入哲學的體系中,將康德的消極“辯證法”改造為積極的“辯證法”,實現將康德靜態范疇體發展為一個互相推演發展的過程,從而形成了辯證法的一般形式——正、反、合。因此這三種活動正是同一性行動的三個方面,構成了正題、反題、合題,與之相對應的是“實在性”、“否定性”和“根據性”三個范疇。費希特提出了最高的綜合,并且在最高的綜合中尋找各種對立,從而推演出新的關聯,知道最后達到統一,在這個過程中完成了思辨邏輯的概念推演。所以知識學中運用“對立統一”的方法,解決“自我”與“非我”之間“可分割性”的量的關系,形成了主體辯證法。這樣費希特用動態演繹過程中的“自我”的獨立性,消解康德從靜態出發的“物”(物自體)的獨立性。運用思辨理性拆除了人認識的界限的同時,也形成了辯證法的雛形,為黑格爾到馬克思的辯證邏輯的開啟提供了方法論基礎,通過對知識學中三個原理的深入分析,探尋費希特知識學原理中的邏輯脈絡,及其對康德哲學的發展與超越,進一步豐富和深化對馬克思辨證思維方式的理解。
參考文獻
[1] 楊祖陶著.德國古典哲學邏輯進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48.
[2] [德]康德著.未來形而上學導論導論[M].龐景仁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8:9.
[3] 李秋零主編.康德著作全集.第3卷:純粹理性批判(第2版)[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48.
[4] 康德著.康德三大批判合集(上)[M].鄧曉芒譯.楊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1.
[5] 費希特著.全部知識學的基礎[M].北京:商務印書館, 1986:10.
基金項目:本文系2017年遼寧省社科基金課題資助項目,課題號:L17WSZ002;遼寧省社科聯課題研究成果,課題號:2019lslktwzz-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