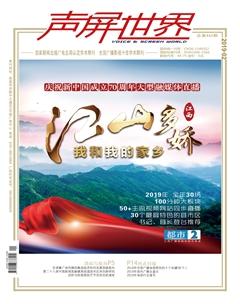淡化差異 尋找共通:新疆對外傳播的重要策略
劉福利
摘要:在新疆對外傳播的過程中,以故事化為手段,以“淡化差異性、尋找共通性”為傳播策略,不僅能夠讓新疆的故事能被受眾看懂和接受,還容易引起共鳴。同時,這種故事化和淡化差異的背后,實際上也彰顯著新疆故事的特色,這是新疆對外傳播中凸顯本地特點的體現。
關鍵詞:故事化 差異化 《我從新疆來》
《我從新疆來》是攝影師庫爾班江·賽買提籌備和拍攝的一部紀錄片,在中央電視臺播出后引起了較大的反響。而實際上,《我從新疆來》可以看作成是一個系列作品,從較早在網易圖片頻道中發布的圖片報道到出版圖書再到之后的紀錄片都是用的“我從新疆來”這一名字,其報道的內容和反映的主題也基本相同,都是通過展示到全國各地學習和工作的新疆的生活,展示新疆人的形象,糾正一些人的認知偏見。
隨著《我從新疆來》系列作品的影響,庫爾班江·賽買提籌備的另一個系列作品《我到新疆去》也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同名紀錄片于2018年5月20日在中央電視臺播出。從《我從新疆來》到《我到新疆去》,庫爾班江的這些作品對于提升新疆的正面形象,幫助受眾更全面地了解新疆和新疆人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以《我從新疆來》為例,分析這部紀錄片給新疆對外傳播帶來的啟示。
故事化的敘述技巧
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講中國故事是時代命題,講好中國故事是時代使命。在給《人民日報海外版》創刊30周年做出重要批示中,他希望海外版用海外讀者樂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語言,講述好中國故事,努力成為增信釋疑、凝心聚力的橋梁紐帶。在出訪活動中,習近平總書記也多次通過講故事的方式來闡述中國的主張。
在信息傳播過程中,受眾可能記不住那些枯燥的理論,但能記住那些簡短生動的故事。首先,故事因其本身的趣味性,很容易吸引人的關注。其次,故事實際上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尤其是在對外傳播過程中,由于傳播者和受眾之間存在很大的文化差異,如果僅僅是通過論證等方式來進行傳播,則受眾需要一個較長的知識消化和理解的過程。反之,故事化的敘述技巧就比較容易接受。因為很多故事實際上就是一個論證過程,這個論證過程在一定程度上能夠避免長篇大論和復雜的歷史背景的敘述,將復雜問題以一種簡單化的方式呈現,這樣受眾接受起來就不會有壓迫感。新疆的對外傳播,也需要更多依靠感人的、能讓人記住的、簡單而典型的故事來進行呈現。
具體到《我從新疆來》,這部作品通篇都是人物的故事,而且都是一些普通人物。這些故事也都不是復雜的故事,每個故事的主題都比較單一,讀起來非常容易理解。比如,在上海讀書的新疆“巴郎子”對足球的熱愛,來自新疆的大齡女青年等。這其中,艾力克·阿不都熱依木的故事非常感人和揪心,他靠賣烤肉給患了腦癱的兒子看病,父親對兒子的這種愛讓人感同身受。通過《我從新疆來》的眾多人物故事的展示,人們看到了各種各樣的新疆人,而不是只在制造恐怖事件的個別新疆人,也不是只會在各類文藝節目中跳舞唱歌的新疆人。這些新疆人有理想有追求,有煩惱有憂愁,他們生活的滋味與內地人沒有多大的差別。
淡化差異化的傳播思路
對于新疆,很多人實際上是以一種“探秘”的方式來了解的。而一些媒體的報道,也恰恰將新疆作為一種跟內地“不同的”人文景觀來進行呈現,將其塑造成“異域風情”。這種宣傳方式,在吸引游客來新疆旅游時,可能會有一定的作用,但負面作用也非常大,那就是將新疆進一步刻板化。
而實際上,在對外傳播過程中,不僅要注意差異性,還應該注重共性,比如愛情、友情、親情、對成功的追求、對公正的追求等。差異性主要是引起人們的好奇,而共性往往能引起人的感同身受,讓人獲得一種情感體驗,從而更容易讓人理解。在這方面,電影作品就是一個很好的體現。即便是一些探險類、科幻類抑或異域風情的電影,電影主題也是人類所共通的內容,比如人性、公平、正義等。這些主題不分國籍,任何一個國家的人都可以看懂。
同樣,在對外傳播中,一個地區的故事如何才能獲得更好的傳播效果?其中之一就是運用不同人共通的情感。在《我從新疆來》中,雖然報道的是來自新疆的人的故事,但這些故事在其他地區的人身上都會存在。比如第一集中追求個人夢想的阿布來提,第二集中追求個人夢想又舍得不自己孩子的清華夫婦,第四集中幾個大齡剩女的故事等。這些內容讓人們看到,新疆人不僅僅是打馕、烤肉、穿艾迪萊斯綢、跳民族舞等簡單化的刻板化的形象,新疆人擁有與內地人幾乎沒有差別的生活和情感經歷。正如庫爾班江在接受采訪時所說:“新疆人也不是境外媒體所說的‘被異化的群體,我們也通過自己的努力和知識創造了自己的社會價值。其實這就是最好的融合。新疆人沒有什么不一樣,我們都是為生活在努力,為家人在奮斗,為自己在爭取。”①
同時,這種共通的情感的傳播,也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新疆人作為“他者”的形象和傳播地位。單波認為:“要解決他者化問題,必須反思和超越認同,回到主體間、文化問平等交流的意義上,建立人類交流共同體。”②而《我從新疆來》則是作為來自新疆的少數民族攝影師庫爾班江自己講述本地人的故事,實際上就是一種平等的交流,也是一種相互的交流。這種交流有助于促進“我們”與“他者”的相互了解和認知。
在共性中展示特色
一個地方之所以吸引人,跟這個地方的特色顯然有關系。在對外傳播中,共性的作用是喚起共鳴,而差異則是展示個性與魅力。這就需要將差異穿插到共性當中。在《我從新疆來》中,這種共性為主、穿插差異的方法有很多體現。
首先,就是語言的表述風格。比如“巴郎子”這種說法就來源于維吾爾語。在第五集開頭有一個鏡頭,阿里木江的書架上有一本書《一個勺子》。而“勺子”是新疆的一個方言,指的是人很傻很憨的意思。其次,就是以新疆的自然和人文風光作為背景,比如大齡剩女一集中,其中一個剩女瑪麗娜新疆老家庭院的建筑特點、庭院里的葡萄樹等,都是新疆庭院風格的一種體現。而在瑪麗娜作為伴娘參加的婚禮上,婚禮舉辦地的地毯擺設、婚禮上大人和孩子跳起的舞蹈也具有濃濃的民族風情。最后,就是在反映新疆人的個性特點。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在新疆這片土地上,新疆人的性格與內地有些差別。比如第二集中,做烤肉生意的楊劍如何與不同民族的人相處。因為在內地,這種多民族的相處機會并不多,但在新疆幾乎處處可見,人們也逐漸學會了如何在多民族相處中達到和諧。另外,楊劍還要求員工在握手時使用雙手,這也是新疆一些少數民族的禮儀,顯得更莊重。
無論是楊劍還是創辦了英語學校的卡哈爾,其故事的主題都是奮斗,尤其是這兩個人都提到“一個人一輩子做好一件事”,這種理念以及他們的奮斗過程和感受,和其他地區的人的奮斗故事本質上沒有太大差別。所以,這是一種能夠讓人感同身受、能啟發人們思考的故事。但在這種故事的具體敘述中,也插入了差異化的元素。這種元素就是新疆給予的,比如楊劍經營的是新疆美食,卡哈爾的成長與自己青少年時期的經歷和家教分不開,而這些經歷主要來自家鄉阿克蘇和自己老家的父親等。因此,這種故事的講述方式,既突出了共性,也讓受眾看到了新疆的特色。這種敘述讓受眾看到,新疆人有與內地人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有相似的人生感受,也有特有的個性特點。
《我從新疆來》的啟示
《我從新疆來》系列作品在傳播上的成功,對新疆對外傳播有很強的啟示。首先,要精選故事,學會通過具體的、主題簡單的故事來達到傳播的目的。現在新疆部分媒體的故事報道比較簡單和模式化,比如關于民族團結的故事,就是報道一個類似于漢族幫助了維吾爾族鄰居致富的故事,套路化現象非常明顯。要想真正讓內容深入人心,需要在尋找典型故事上下功夫,把宣傳主題隱藏在故事中,通過故事來達到對外傳播的目的。《我從新疆來》系列作品總共采訪了100多個來自新疆的普通人的故事,但最后精中選精,在紀錄片中展示的是16位,選擇的也是最佳的故事。
其次,淡化宣傳味道,將傳播目的融入故事之中。其實故事本身就是一種宣傳方式,寓一定的道理在其中。通過《我從新疆來》,人們看到了更多活生生的新疆人的故事,展示了新疆各民族在內地的學習與工作、幸福與煩惱。這些故事本身就是在客觀地宣傳新疆形象,展示我國民族大家庭中的和諧相處。因此,只要故事選得好,沒必要特意在故事的基礎上加上口號式的宣傳字眼。
第三,就是多傳播那些共通的故事。不同人之間共通的情感和共識在傳播時能更方便受眾快速理解,還容易引起共鳴。反之,如果只是傳播一些地方特有的東西,那么別人就會以“奇觀”的視角來看待,缺乏深度的了解和理解。同時,在那些新疆特色的故事中,也要尋找那些人類共同的情感。比如哈薩克族訓鷹活動中人與大自然的和諧相處,新疆美食制作中的親情故事等。這些年來,新疆有關紀錄片在對外傳播中逐漸學會了使用這種敘述方式,比如紀錄片《新疆味道》就將關于家族手藝的傳承與父女親情的故事融入其中。
最后,要鼓勵非官方機構和個人來推動對外傳播。民間力量是推動對外傳播的重要支撐。《我從新疆來》系列作品最初就來源于民間,創作者庫爾班江從攝影作品開始,逐步完成了自己的系列作品,其中《我從新疆來》還采取了眾籌的方式,既籌的資金也擴大了宣傳。而實際上,進行這種嘗試的人遠不止庫爾班江一個人。比如就職于新東方教育集團的英語教師努爾艾力·阿不利孜在《超級演說家》欄目里對新疆的介紹,娛樂明星佟亞麗與李亞鵬等人對新疆的宣傳,維吾爾族女大學生麥孜燕在愛奇藝舉辦的娛樂節目《奇葩大會》上對新疆形象的糾正等。金玉萍、謝華鋒把這種民間的對外傳播稱之為“草根動員”。與官方層面的傳播相比,“草根”的傳播在故事的選擇、表達語言和呈現方式上可能更接地氣。金玉萍等認為,“政府在積極推動民間行為的同時,還應發揮組織動員的作用,使‘草根動員由自發、零散傳播走向整合傳播,通過全民參與,動員公眾的力量,塑造繁榮發展、開放創新、和諧包容、團結穩定的新疆形象”。③
在這方面政府至少可以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是利用民間已經形成一定影響的關于新疆對外傳播的話題,積極推動這種傳播進一步擴大規模,形成更強的影響力,《我從新疆來》系列作品其實就是這個路徑;二是政府積極推廣一些活動,然后吸引更多的公眾參與其中。比如新疆推出的“阿克蘇的蘋果紅了”等活動,就屬于此類。[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項目(項目編號13XJJC860001)《中外媒體關于新疆熱點事件報道的比較研究》部分成果]
(作者單位:塔里木大學)
欄目責編:楊 剛
注釋:①陳雪蓮,汪奧娜:《專訪〈我從新疆來〉作者庫爾班江:讓世界了解真實的新疆》,《國際先驅導報》,2015/09/30。
②單 波,張騰方:《跨文化視野中的他者化難題》,《學術研究》,2016(6)。
③金玉萍,謝華鋒:《草根動員:一種塑造新疆形象的新思路》,《青年記者》,2015(7)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