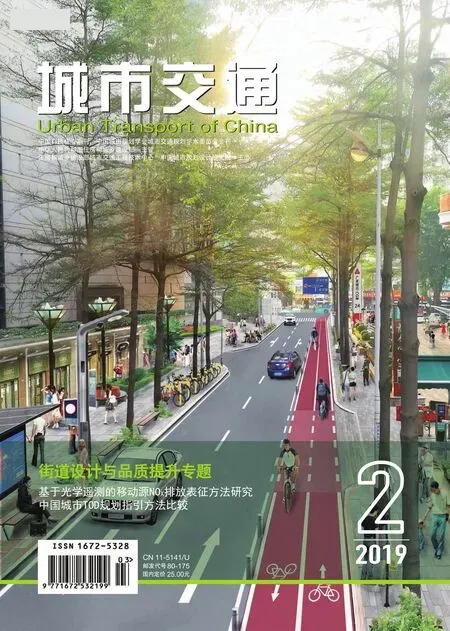讀書
《輕松開展停車改革》解讀 A Review of Parking Reform Made Easy
美國從20 世紀20年代開始設置停車配建標準,該標準已經成為區劃條例中的范式內容,意圖保證開發項目停車位能夠自給自足,避免外部影響。經過近百年發展,停車配建標準引發一系列城市問題,美國開始呼吁取消停車配建下限指標,但在實踐中遭遇強大阻力。理查德·威爾遜(Richard W.Willson)認為,停車配建標準在一定時間內有存在的必要。在2013年出版的《輕松開展停車改革》(Parking Reform Made Easy)一書中,威爾遜詳細論述了如何設定科學合理的停車配建標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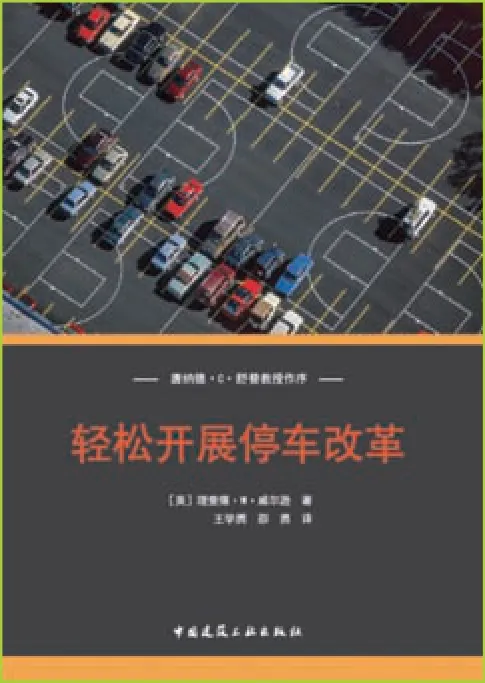
輕松開展停車改革作 者:理查德·W·威爾遜譯 者:王學勇,邵勇出版單位: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出版時間:2019年2月
停車配建標準的起源和發展
20世紀20年代,美國福特汽車公司發明的流水線作業,讓廉價的T型車迅速進入普通工薪家庭,隨之也帶來了愈發嚴重的停車難問題。當時的美國人期望在城市區劃條例中規定開發項目建設充足停車位,以滿足這種新型交通工具的需求并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
早期支持設置停車配建標準的理由包括:1)減少項目周邊交通擁堵;2)避免停車外溢;3)創造有序發展模式;4)能夠預測用地強度或用途的改變;5)為開發商提供公平競爭環境;6)通過增加停車供給鼓勵核心區增長;7)減少業主之間的停車沖突,從而減少不必要的停車管理;8)減少公共停車位建設需求,節省政府開支。
1923年,俄亥俄州哥倫布市為多戶住宅設置停車配建標準。1939年,加州弗雷斯諾市將其擴大到非居住類用地。1945年后,伴隨美國城市的郊區化和汽車擁有率增長,停車配建標準迅速推廣。到1972年,216 個城市中的214個實施了停車配建標準,停車配建標準成為區劃條例中的必備章節。
停車配建標準的反思和批判
在發展過程中,停車配建標準越來越僵化刻板。政府為了充分滿足停車需求,經常采用全年高峰時期的停車需求量作為下限指標。人們逐漸發現這些指標成為新開發的巨大束縛。例如,一些城市餐館停車配建下限指標超過每1 000平方英尺(約93 m2)10個車位。在進行老城更新開發時,最有吸引力的餐飲行業由于無法滿足該下限指標而不得不被放棄,只能選擇其他一些振興經濟效果不顯著、但下限指標較低的業態。
從20世紀90年代起,唐納德·舒普(Donald Shoup)教授開始系統總結停車配建下限指標問題。他將下限指標稱為“小汽車的催生劑”,認為下限指標本意是為了減少開發項目周邊的道路交通擁堵,但它實際上極大地刺激了小汽車出行,并起到降低開發密度的消極作用。
本書作者威爾遜正是舒普教授的早期博士研究生。他在書中總結了反對停車配建標準的理由,包括:1)停車配建標準鼓勵小汽車出行;2)不利于發展公共交通等替代方式;3)忽略了成本效益;4)減少城市密度;5)形成對人不友好的設計方案;6)阻礙開發和經濟活動;7)使可支付性住宅建設更困難;8)阻礙填充式開發和適應性再利用;9)直接和間接破壞環境;10)對非小汽車出行方式不公平;11)減少身體活動;12)不能反映實際的停車位利用率等。
是否取消停車配建下限指標?
既然停車配建下限指標存在如此多的問題,是否可以取消?舒普教授堅持取消,前提是全面普及停車收費并通過充分市場化的價格來調節停車位利用率。2004年,英國倫敦全城范圍內取消下限指標、改為上限,成為典型案例。
但是,到本書英文版出版時,美國尚未有全城范圍內取消下限指標的城市,僅僅在部分城市的核心區實施。在此之后,只有2個城市相繼實現了全城范圍內取消下限指標,分別是2016年12月紐約州布法羅市和2017年11月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
威爾遜完全同意舒普教授的理念。但是擁有25年停車咨詢經驗的威爾遜認為,通過完全市場化來解決停車問題可能面臨市場失靈問題。停車不是純技術問題,更多是一種政策決策問題。對美國來說直接取消下限指標這種改革方式太過激烈,應該采取一種漸進式的改革方法,通過公眾參與的形式,優化降低下限指標,達成多方共識。
威爾遜停車配建標準改革工具包
威爾遜認為下限指標的制定方法既不科學、也不透明,于是他決定在書中打開制定停車配建標準的黑箱子,讓規劃人員、政府和民眾能夠共同制定一個共識標準。
威爾遜提出改革停車配建標準的工具包,主要分為12個步驟:1)確定現狀停車位利用率;2)開發未來基準利用率;3)確定最佳基礎配建指標;4)考慮項目和背景環境進行調整;5)考慮停車收費、配建指標拆分、停車折現等方法對指標進行調整;6)根據公共交通、步行、自行車等交通系統規劃對指標進行調整;7)分析內部停車位利用率對指標的調整;8)考慮異地停車來調整場地配建指標;9)考慮內部共享對配建指標的折減;10)最后綜合以上因素,制定期望的下限指標,并對此展開評估,對有疑義的步驟重新迭代計算。
達成共識性停車配建下限指標后,威爾遜還繼續考慮了節省停車場地面積的步驟:11)考慮停車位尺寸的效率問題;12)探討子母車位、代客泊車和機械停車的可能性。在書中,威爾遜還分別采用居住、辦公、商業活動中心三類用地對工具包的使用進行了演示。
點評
總體而言,本書對國內停車配建標準制定有三點借鑒意義:
第一,停車配建下限指標的提出和取消均有其歷史背景。在機動化發展初期,需要有一種管理方法來保障秩序和公平;在機動化發展成熟后,應該采用更加彈性的管理方式。國內的城鎮化和機動化水平仍處在快速上升期,停車需求作為一種復雜的社會需求在一定時期內仍需妥善解決,即使采用市場化手段,也需要根據城市發展目標制定合理的供給比例。在此階段,下限指標仍是保持秩序和公平的重要手段,因此更需要保留。
第二,停車配建下限指標的制定要科學合理。美國關于停車配建指標的研究已經比國內時間更久、投入更大。例如,美國交通工程師學會發布的《停車生成率》報告詳細統計了各類用地的停車利用率情況。但是從這種統計中仍能發現數據的差異性較大,充分表明不同背景下的停車需求復雜性。我們對于現狀停車調查的投入尚淺,缺乏應對具體背景對配建指標調整的彈性,應該做更多基礎性研究工作,建議借助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城市交通規劃學術委員會或成立聯盟性組織來推動基礎數據調查與整合。
第三,停車配建下限指標的確定更多是一種政策決策過程,應該更加透明化。威爾遜方法的計算結果與現行配建指標可能差距不大,讓人覺得費這么大力氣糾結是每戶1.2個車位還是1.5個車位太不值得。但是,這種參與式規劃方法在制定政策過程中盡可能達成最大范圍的共識,能夠更廣泛的融合城市發展目標和更廣大的利益相關者需求。我們可以分區制定停車配建指標,這種分區可嘗試劃分至街道這一級別,以推動通過社區治理解決紛繁復雜的停車問題。
本書的中文版將于近期同讀者見面。對美國停車管理經驗有疑惑的讀者朋友,歡迎您到書中尋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