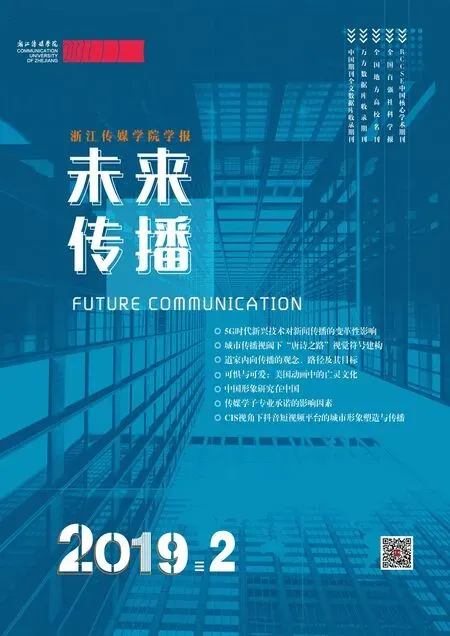中國形象研究在中國
——“中國形象”研究論文的主題元分析(2000—2018)
韋 路 姜加林 胡雨濛
世界如何看待中國?這個問題在閉關鎖國的歷史時期其實并未受到國人的關注——文人士大夫長久以來以天朝上國之民自居,沉浸在“萬邦來朝”的美夢中。直到中國被卷入現(xiàn)代化進程之后,才猛然醒悟“中國”已為世界“想象”和“表述”為一個愚昧而落后的形象。
于是中國開始邁向一條圖自強而弭禍患之路,并希望借此重鑄良好的國際形象。不過,形象的構造從來不止于我們“怎么說”和“怎么做”,也在于海外接受者“怎樣理解”和“怎樣評論”,以及兩者在國家、社會、民眾等各個層面“如何互動”和“如何博弈”。
隨著中國國力的提升,“中國形象”卻更為復雜詭譎:“‘中國威脅論’‘黃禍論’與‘中國救世論’‘漢學熱’同在,權力和新的知識系譜在中國的新面孔上形成激烈的話語,不但在政治、經(jīng)濟層面上有著明顯體現(xiàn),也在文學、電影、電視、日常生活等層面上得以重新表征。”[1]
然而,無論“中國形象”以怎樣嶄新的、多樣化的面貌呈現(xiàn),實質卻始終難以避免一個具有延續(xù)性的“他者”的鏡像。這種印跡深刻到即使我們在自我表述時,也或多或少帶有自我異化的傾向——不管是文學作品還是影視藝術,似乎只有這樣才能獲得世界的認可和榮譽。“他塑”與“自塑”的共同運作,使得關于中國的刻板印象愈演愈烈。
盡管從政府到媒體已有一系列針對改善國家形象的舉措,但顯然目前所為尚不足以徹底扭轉“妖魔化”的民族想象;此外,目前的國際環(huán)境為中國創(chuàng)造了難得的形象提升空間,國家身份和國民形象都亟待重新定義和規(guī)劃。要提出行之有效的對策,前提是對“中國形象”的歷史、現(xiàn)狀和問題進行全面的、深入的和透徹的研究。
國家形象的研究始于國際關系與政治、傳播學等學科,且已形成一定的研究規(guī)模。但隨著研究深入,當“中國形象”越來越與各行各業(yè)息息相關時,它就超出了學科邊界,凝聚了更多的精神內(nèi)涵。各個學科群策群力,學科間的壁壘雖未打通,但幾乎都對改善和提升國家形象的大議題予以了觀照。
藉由文藝作品、民調結果、媒體材料等素材,學者們紛紛對“中國形象”展開研究。為審視這些研究的概況,總結階段性研究成果,挖掘其中可改進和提升之處,筆者以“中國形象”為關鍵詞在中國知網(wǎng)的CSSCI數(shù)據(jù)庫中檢索,共獲得2000年至2018年共226篇相關研究論文。本文用SPSS和Rost Wordparser對該226篇論文進行內(nèi)容分析和詞頻分析,試圖探索國內(nèi)各個學科關于“中國形象”的研究現(xiàn)狀、熱點和趨勢。
一、研究概況
對“中國形象”的研究遍及不同的科研主體和學科,且在時間上呈現(xiàn)整體增加的趨勢,展現(xiàn)出多元合作的研究態(tài)勢。
(一)研究趨勢
縱觀歷年國內(nèi)各學科對“中國形象”的研究(見圖1),可見在2008年以前學界關注度保持在較低的數(shù)目水平,且從側面——往往是文學藝術方面——涉及對“中國形象”的討論。錢林森討論游記在西方漢學中的地位和作用;[2]尹吉男分析了中國當代藝術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資源的利用。[3]
直到2008年借北京奧運會的契機,探討“中國形象”的論文呈大幅度增加。如董小英等對五個奧運舉辦城市的相關報道進行跟蹤研究,分析議程設置對國家形象的作用;[4]巴庫林和沈昕以北京奧運會的相關報道為對象分析俄羅斯大眾媒體中的中國形象。[5]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意識到國家形象的豐富內(nèi)涵和重要意義,“中國形象”成為研究熱點。
隨后,相關探討一直保持較高的熱度,雖有波動,但整體上呈現(xiàn)穩(wěn)步增長的態(tài)勢(見圖1),并出現(xiàn)了這一領域的綜述性總結,如程廉對二戰(zhàn)時期美國的中國形象研究的述評等;[6]此外,學者相互間的對話交流愈加頻繁:如周云龍對周寧“跨文化形象學”系列研究提出質疑;[7]周寧對此作出了回應,提出表面上全球化的中國形象實際已被西方的中國形象程序所操控,這才是隱藏在全球主義中轉移病變的最危險的東方主義因素。[8]
(二)研究主體
考察“中國形象”的研究主體可發(fā)現(xiàn)(以第一作者所在的機構為依據(jù)),92.92%的研究者來自高校,6.19%的研究者來自研究機構,可見對“中國形象”的學術研究是當前的主流。與之相對的,傳媒機構的研究者只占0.88%,這類研究以實用性為主,站在媒體立場討論國家形象的問題;除此之外,更是沒有政府機構的相關研究者,說明當前對國家形象的討論往往是學界一頭熱,政府部門雖然已有一定的意識卻尚未足夠重視,不能形成較系統(tǒng)的、高質量的研究成果(見圖2)。
(三)學科分布
在學科分布方面,對“中國形象”的研究以新聞傳播學(27.43%)、外國語言文學(19.91%)和中國語言文學(18.14%)為主(見表1)。
媒體對建構國家形象的重要性無需贅言,這也是新聞傳播學大有可為之處。在缺乏國際化大眾媒體的時代,中國形象或建構于神話和文學典籍之上,或流傳在口耳相傳之中。在有了報紙和其他現(xiàn)代傳媒的時代,中國形象不管是被大眾媒體所左右,還是為人際傳播所建構,都是新聞傳播學的討論范疇。何海巍和包鵬程對美國國會選舉廣告的研究,[9]戴元光和邵靜對《紐約時報》涉華政治類報道的考察,[10]以及蔡馥謠對德國《明鏡》周刊封面中國符號的分析,[11]都是通過透視國外媒體的中國表述來研究中國形象的傳播。
文學作品對國家形象的傳播效果同樣不容小覷,有些作家通過個人創(chuàng)作所達到的國家形象建構力量,恐怕要高于刻意的、高成本的國家層面的宣傳。中外文學領域的學者通過對文學作品的鑒賞和文學流派的考證:研究作品所塑造的國家形象,如愛爾蘭小說《尤利西斯》[12];研究文人的中國觀,如魯迅[13]、老舍[14]、莫言[15]、日本作家村上春樹[16]、美國小說家馬克·吐溫[17]、葡萄牙小說家埃薩·德·克羅斯[18];研究一國或一個民族在一段時期內(nèi)文學流派對中國的想象,如中世紀德國文學[19]、19世紀美國文學[20]等。研究者關注文學作品中的中國形象變異,“研究一國形象是如何在異國被想象、流傳、重新塑造的流變過程”[21]。
此外,部分學者也從政治學角度(10.62%)探求中國形象的塑造。國家形象,本身就無法避開國際關系問題,自然也不能忽略政治的影響因素。與政治學相關的軟實力、現(xiàn)代性等概念也與中國形象的建構不無牽連。
其它研究分別從藝術學(8.85%)、世界史(4.42%)、社會學(3.10%)、中國史(2.21%)、哲學(0.88%)、教育學(0.88%)、法學(0.44%)角度對中國形象進行研究,雖然不成規(guī)模體系,但可見幾乎各個人文社會學科都考慮到了國家形象的話題。

表1 “中國形象”研究學科分布表(N=226)
二、研究內(nèi)容
對研究內(nèi)容的考察發(fā)現(xiàn)學者主要關注國家形象整體,注重考察中國在西方和歐美國家的形象建構,并主要通過文學作品和紙媒作為認知載體。通過內(nèi)容分析和更進一步的詞頻分析,本文試圖挖掘國內(nèi)中國形象研究的熱點議題和核心概念。
(一)議題分布
研究中國形象,“國家”被大多數(shù)學者們想當然地作為研究主體,大部分研究(96.90%)是以國家整體為切入點的(見圖3)。在大量該類研究的對照下,對個體和區(qū)域形象的研究顯得比較薄弱,僅有3.10%的研究討論人民形象,如徐艷蕊對好萊塢華人女性的形象研究,[22]除此之外,沒有專門討論政府形象、城市形象、媒體形象和企業(yè)形象的論文——而這些恰恰又是構成國家整體形象的關鍵要素。
將國家作為一個整體加以討論時,區(qū)域形象和個體形象的影響力被忽略了。政府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個國家的官方形象和政治形象,在中國語境下又與民主、平等、人權等概念相關聯(lián);人民形象是組成國家形象的重要因素,很多時候,它發(fā)揮的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的關鍵作用,只有人民形象是積極、友善、進步的,世界對中國的印象才會真正改觀;城市作為現(xiàn)代化進程的象征,尤其是一些具有“中國特色”和“全球化痕跡”的大都市,其城市形象亦是國家形象的一個側面;而隨著“中國制造”喜憂參半的國際聲譽,企業(yè)和品牌的形象可以讓世界公眾對中國產(chǎn)生直觀的認同或形成負面的評價。這些議題都是有所欠缺卻值得研究的。
(二)認知對象
形象雖然不是實體,但也不存在于虛無之中——一個國家形象必定是通過特定的受眾進行認知才完成傳播過程。考察“中國形象”研究的認知對象發(fā)現(xiàn),除33.63%的研究不指出特定的國家或地區(qū)來源外,大多數(shù)研究都注重中國形象在西方國家和亞洲其它國家的傳遞。其中,對歐洲國家(20.80%)和北美(16.37%)的考察是主流研究,因為中國作為東方國家的代表,經(jīng)常被學者用于與西方世界的比較研究之中來探討形象建構問題(見表2)。
此外,其它亞洲國家(16.81%),如韓國[23]、印度[24]、日本[25]、朝鮮[26]——大多是中國的鄰邦,或在歷史上與中國交往甚密,這些國家中的形象嬗變和民眾認知也是研究者重點關注的;10.62%的研究針對中國對本國形象的認知。
其它地區(qū)的中國形象是被忽略的,可見在國家形象的區(qū)域認知問題上,學界研究是嚴重失衡的,并且向西方國家傾斜。

表2 “中國形象”認知對象分布表(N=226)
(三)形象載體
在對其它國家的認知中,親身到過異國或接觸過該國民眾的畢竟是少數(shù),除了這類親身體驗和人際渠道的認知外,其它人對國家形象的認知都是通過一定的載體,從文字或鏡像中所建構的想象。研究發(fā)現(xiàn),除37.61%的中國形象考察并未指明形象載體外,最重要的傳播載體是文學作品(29.65%),可見文學的魅力所在(見表3)。
很多時候,文人的社會責任感和人道主義情懷使他們關注到中國曾遭受的苦難歷史,但其筆下的中國更突出反映的是作家本人所在社會和時代對中國的“集體想象”,同時帶有自我的文化立場。對外籍文人而言,囿于歷史文化語境和社會心理,其反映的中國形象不可避免地染上了偏見、輕視、排斥等痕跡;國內(nèi)文學作品則往往帶有懷舊色彩或者自我異化的痕跡。學者通過文學作品來分析國家形象,就是想探求這些作品的感染力和表現(xiàn)力,以及是否會造成形象的曲解與誤讀。
此外,報紙媒體(11.50%)也是研究者傾向選擇的形象載體。紙媒通過對議題的設置和對新聞事件報道框架的選擇來傳遞信息,長此以往,實則已經(jīng)勾畫了一個國家的媒介形象。大多數(shù)受眾通過媒體來了解遠方的、異國的消息,因而報紙建構的“擬態(tài)環(huán)境”很容易為傳播學者所關注。
其它研究所關注的認知載體零星涉及電影(5.31%)、書刊(6.64%)、民調(2.65%)、電視(2.21%)和紀錄片(2.21%)。值得一提的是,網(wǎng)絡新媒體作為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重要的國家形象傳播渠道,卻為大多數(shù)研究者所忽略(2.21%)。韋路等人發(fā)現(xiàn)與傳統(tǒng)美國大眾媒體所呈現(xiàn)的中國形象一直帶有負面偏見相比,互聯(lián)網(wǎng)上有關中國的多元內(nèi)容更有可能增進美國公眾對中國形象的正面認知,因為新媒體技術建構了一個更為開放的社會網(wǎng)絡,“為人們提供了更多的選擇機會和更少的重要程度提示”[27];張春波研究了YouTube視頻分享網(wǎng)站為中國形象塑造提供的契機,表明“視頻以彼此競爭的表征范式塑造了類別化的中國形象,但同時也為中國形象的多角度表征提供了傳播空間”[28];周萍對網(wǎng)絡媒體中涉華報道所引發(fā)的評論進行研究,探討西方網(wǎng)絡新聞中的中國形象;[29]梁云等人對社交網(wǎng)站VKONTAKTE關于中國的報道進行分析;[30]常江對中國網(wǎng)絡評論從“野蠻生長”到秩序化的發(fā)展歷程進行了分析。[31]但除此之外,目前對互聯(lián)網(wǎng)所塑造的中國形象研究未引起學者足夠的重視。

表3 “中國形象”形象載體分布表(N=226)
(四)詞頻分析
為深入討論“中國形象”相關研究所關注的熱點,本文將226篇樣本論文的題目、關鍵詞和摘要進行整理,并用Rost Wordparser軟件進行詞頻分析。在統(tǒng)計結果中選取頻數(shù)在10以上的詞匯,并去掉虛詞和與中國形象研究明顯無關的詞,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中國形象”研究詞頻分析(字數(shù):57939)
從詞頻分析上看,研究重點關注的中國形象認知對象以西方和歐美地區(qū)為主,此外包含中國的鄰邦,具體國家涉及美國(142)、日本(86)、印度(60)、俄羅斯(53)、英國(37)、德國(34)、法國(25)、朝鮮(19)、韓國(15),此外,西方(235)、歐洲(35)、阿拉伯(14)。
諸多研究所經(jīng)常提到的中國形象傳播渠道主要以文學(110)為主,具體包括小說(37)、游記(15)等;另外,媒體(105)渠道的認知包括電影(69)、周刊(21)、網(wǎng)絡(16)、廣告(10),但缺乏對電視等媒體的討論。
是什么構成了中國形象呢?國內(nèi)的研究所關注到的中國符號主要以人為主:中國人(31)、華人(19)、少數(shù)民族(18)、華裔(11)、留學生(10)。奧運會(21)作為傳播國家形象的契機,也是一次舉世矚目的儀式,吸引了學者的注意。北京(19)作為城市形象的代表被較頻繁地提及。漢學(15)、孔子(14)、絲綢(13)代表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精髓和沉淀。此外,社會主義(11)也成為中國形象的一個表征。
然而,形象的傳播不是簡單的如實傳播和全盤接受。學者關注到了這種形象傳遞的過程,在他們看來,中國形象是建構(102)的或構建(24)的,是通過話語(97)、敘事(43)、修辭(13)甚至隱喻(12)等手段來塑造(100)的。受眾則通過想象(83)來達成對他國形象的認知(61)和認同(30)。
此外,當討論中國形象時,有一些詞匯也被頻繁提及,如現(xiàn)代性(99)、意識形態(tài)(44)、刻板(11)等,它們經(jīng)常是國家形象研究的切入點,也是學者在關注國家形象之余希望探尋的問題。
為進一步探求研究內(nèi)容隨時間的變化趨勢,本研究按照年份,從2000年至2018年建立18個包含題目、摘要和關鍵詞的子語料庫(2002年空缺),依次檢索上述頻數(shù)在10以上的高頻詞匯在各年份語篇中的詞頻分布情況,并除以該年語篇字數(shù),以便進行歷時性的比較。通過線性曲線估計發(fā)現(xiàn),22個詞語大致隨時間推移越來越占據(jù)話語中心,3個詞語逐漸被淡化。其中,研究對西方的關注有所下降(F(1,16)=6.309,p<0.05),對日本的關注有所上升(F(1,16)=5.324,p<0.05)。隨著時間的推移,研究不再強調對相關“知識”的關注(F(1,16)=4.588,p<0.05),與此相反,國家形象的“傳播”日益成為研究的焦點(F(1,16)=24.800,p<0.001),尤其體現(xiàn)為通過對媒體(F(1,16)=4.734,p<0.05)、電影(F(1,16)=9.486,p<0.01)、圖書(F(1,16)=6.033,p<0.05)、紀錄片(F(1,16)=7.878,p<0.05)、網(wǎng)絡(F(1,16)=7.472,p<0.05)等媒介的研究。研究者們?nèi)找嬲J可,國家形象是通過“建構”(F(1,16)=19.228,p<0.001)或“構建”(F(1,16)=6.981,p<0.05)而形成的,并從話語(F(1,16)=4.590,p<0.05)、敘事(F(1,16)=7.389,p<0.05)中得以反映。議題方面,學者對“政治”(F(1,16)=13.071,p<0.01)和“經(jīng)濟”(F(1,16)=12.301,p<0.01)相關話題關注度增加,前者包括“政策”(F(1,16)=6.139,p<0.05)、“政府”(F(1,16)=5.344,p<0.05)等語匯,后者包括“實力”(F(1,16)=5.141,p<0.05)、“崛起”(F(1,16)=5.087,p<0.05)、“利益”(F(1,16)=20.545,p<0.001)等語匯。此外,研究對“民族”(F(1,16)=11.446,p<0.01)、“理論”(F(1,16)=6.555,p<0.05)、“絲綢”(F(1,16)=18.079,p<0.01)等話題的關注也呈上升趨勢。
三、研究過程
國內(nèi)各學科關于中國形象的研究,大多數(shù)沒有顯而易見的理論支撐,也沒有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可見研究的面雖然已經(jīng)撒開,很多相關問題都得到了關注,但是力度依舊薄弱,水平有待提升。
(一)理論
考察研究中所應用的理論發(fā)現(xiàn),83.63%的研究沒有理論基礎,以介紹與歸整見長(見表5)。其余的研究中,有4.42%使用到了東方主義的概念。王岳川以賽義德的“東方主義”為思考的出發(fā)點,提出“發(fā)現(xiàn)東方”以張揚文化多邊主義,從而在當代文論中發(fā)出中國的聲音。[32]何海巍和包鵬程研究競選廣告中的東方主義傾向,揭示廣告“通過符號化和二元對立的敘事結構,將中國作為美國的‘他者’”[9](59)的策略。郭忠華通過分析17—19世紀歐洲“頌華派”和“貶華派”思想家有關中國形象的論述,呈現(xiàn)出東方主義兩種對立的認識范式:積極東方主義和消極東方主義。[33]相關的,文化帝國主義理論(2.21%)也為一些學者所使用。
3.98%的研究以刻板印象為理論框架,這類研究集中在兩類話題上,一類是文學的“套話”,一類是媒體所建構的定型化的國家形象。自李普曼在《公眾輿論》一書中首次提出刻板印象以來,這一理論被廣泛應用于人文社會學科。云虹在對英國文學中的中國形象進行研究時充分使用該概念,發(fā)現(xiàn)中國在英國文學中表現(xiàn)為兩類完全不同的形象,“一個是樂園般光明的中國,另一個是地獄般黑暗的中國”[34]。周勇等人研究美國電影中的中國人物形象,發(fā)現(xiàn)人物形象雖已中性偏正面,但依然擺脫不了刻板印象的影響。[35]
框架理論(2.65%)在對報紙所呈現(xiàn)的中國形象研究中使用得比較普遍。戴元光和邵靜對《紐約時報》涉華報道進行分析,總結美國紙媒涉華報道的傾向、框架和姿態(tài);[10]張昆和陳雅莉對《海峽時報》和《雅加達郵報》關于南海爭端的報道進行以框架理論為指導的內(nèi)容分析,考查兩份東盟英文報紙報道南海爭端過程中的主導性框架、意見話語和對華態(tài)度。[36]此外,議程設置理論(1.08%)也為媒體建構的中國形象研究中提供理論視角。
另外,有3篇論文使用了認同理論,各有一篇論文使用了表征理論、新言語行為分析理論,可見在中國形象研究中理論可被挖掘的空間之廣。

表5 “中國形象”研究理論應用分布表(N=226)
(二)方法
研究方法方面,遺憾的是,27.43%的國內(nèi)中國形象研究沒有采用研究方法,使得研究原創(chuàng)性和創(chuàng)造性大打折扣(見表6)。
在其余研究中,大部分采用質化研究手段分析中國形象的傳播,其中話語(文本)分析(30.09%)和歷史分析(16.37%)的研究方法較為常見。前者如鐘馨以Fairclough的批評話語分析框架研究倫敦奧運會期間英國報紙的“葉詩文話語”建構的中國形象;[37]后者如李榮建對阿拉伯視野的中國形象變遷進行研究。[38]此外,7.08%的研究采用個案分析,分別有一項研究使用了訪談、焦點小組和法律分析的方式進行。
量化研究主要以內(nèi)容分析(7.96%)和調查(3.10%)為主。內(nèi)容分析作為新聞傳播學首創(chuàng)的研究方法,主要被用于對媒體內(nèi)容的量化研究,如對《新聞周刊》涉華文章呈現(xiàn)形式、圖片配置、體裁類別、所涉領域、消息來源、文章傾向等類目的分析。[39]民調則是學者了解民眾對話印象的重要手段,葉淑蘭對上海留學生對中國形象的認知進行調查,以了解親身體驗所形成的中國形象。[40]此外,劉偉乾用自由圖畫聯(lián)想測試法、自由詞匯聯(lián)想測試法等實驗法調查分析塔吉克斯坦民眾對于中國國家形象的基本認知和態(tài)度;[41]還有兩項研究采用了量化二次數(shù)據(jù)法。
有2.65%的研究采用了質化研究和量化研究相結合的方式,大多是對報紙文本的話語分析與內(nèi)容分析,如沈影、吳剛以《州報》《實業(yè)界》《烏拉爾政治網(wǎng)》報道為例對俄羅斯區(qū)域媒體中的中國形象進行分析。[42]

表6 “中國形象”研究方法分布表(N=226)
四、代表性觀點
正如Hodder所說:中國,作為一個悖論,一直以來都是一個被誤解的國家。[43]國內(nèi)學者在進行中國形象研究時——不管是歷史的梳理,還是對文學作品的賞析,抑或是關注具體的媒介報道行為——往往自覺地帶有揭示和糾正這種誤解的意圖。
(一)整體形象: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性
很多學者對中國形象持悲觀態(tài)度,在他們看來,中國的國家形象傳播在“別有用心”的塑造和“刻板”的認知下陷入困境。正如李希光等人對美國電影的形象研究所現(xiàn),中國形象在19世紀末是腐朽、愚昧的,20世紀初是貧困、“未開化”的,文革前后是“妖魔化”的。[44](235-259)
然而,中國畢竟曾是令四方稱羨的文明古國。在西方的現(xiàn)代性滋生彌漫之前,它作為遙遠的、神秘的國度,是一個地大物博、充滿財富的禮儀之邦。趙雪波提到:“明朝時期,中國形象變成了‘中華大帝國’,……中國的一切成為西方學習的典范。”[45](64)直到今天,即使中國形象面臨諸多負面評價,世界仍然對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心存好感。龍、長江、黃河、長城、春節(jié)、中秋等符號,作為民族文化的精神,不乏吸引力和號召力。
隨著時代的變化,中國形象發(fā)生了顛覆性的改變,落入了“泥足巨人”“東亞病夫”的負面指摘中。究其原因,也許正如王岳川所說“現(xiàn)代化等于西化的誤區(qū)和中國制度性衰退,使得中國的‘大國形象’逐漸發(fā)生位移而邊緣化”[32](109),在西方現(xiàn)代性的想象中,中國是邊國,西方是中心,這種差異與等級的關系造成了中國形象的現(xiàn)代性格局。
于是,為了迎合現(xiàn)代性的品位,中國努力從野蠻東方的泥潭中走出,卻又不小心落入了另一個陷阱之中。中國形象被扭曲為“‘未來核戰(zhàn)爭的狂人’‘偷竊知識產(chǎn)權的海盜’‘威脅全球經(jīng)濟的奸商’‘踐踏人權的警察’”[46]。值得慶幸的是,在經(jīng)濟危機、環(huán)境危機和能源危機的全球語境下,中國又扮演了“救世主”的角色,成為世界的“諾亞方舟”。然而無論如何,形象的建構仍然逃不開程式化的和為西方現(xiàn)代性所操控的痕跡。
(二)西方表述與投射
中國的綜合國力、民族素養(yǎng)和形象傳播策略的確會對國家形象產(chǎn)生深遠影響。但是除此之外,在西方主導話語權的今天,“中國形象”同樣也是由西方的思維和價值判斷來認定的,“是西方文化投射的一種關于文化他者的幻象,……是西方現(xiàn)代文化自我審視、自我反思、自我想象與自我書寫的方式”[47]。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中國形象”是反映西方想象性的建構物,“作為西方文化自我認同的他者,與其說是表現(xiàn)中國,不如說是表述西方”[48]。
因此,從“中國形象”中,我們不僅能看到世界對客觀中國的認知,也能看到各國對自我的關照,對西方文化自我認同的隱喻性表達,以及對中西關系的焦慮、想象和期望。
歷史上,“中國形象”在西方經(jīng)歷了各種變幻,但是無一例外,關照出來的都不僅是中國,還有“自我”。而且,這種形象的建構也帶有自我需求的色彩。葉淑蘭認為:在文藝復興時期,西方需要“孔夫子的中國”等美化中國的形象,隱喻地表現(xiàn)自身對世俗、現(xiàn)代性的追求。[40]但是隨著西方現(xiàn)代性的發(fā)展,其對中國形象的建構逐漸趨于負面。在中國崛起的進程中,“中國威脅論”“中國新殖民主義論”“中國傲慢論”等話語此起彼伏,用于西方維護自身制度和文化優(yōu)越性的需要。直到西方面臨危機,中國被想象為“田園詩般”的國度,詩化的傳統(tǒng)鄉(xiāng)土成為西方的烏托邦寄托。尤其是少數(shù)民族的生存空間常常在“異托邦”的建構下被賦予“‘桃花源想象’的文化邏輯和主體內(nèi)蘊”。[26](81)
其實,不唯西方如此,任何國家在想象中國時,都同時在自我呈現(xiàn)。中國形象不僅是各國根據(jù)其特定的、歷史的文化視角所形成的對中國的認知,而且也是各國從中國形象中看到“自己”。劉亞丁認為俄羅斯對中國的想象在18世紀下半葉、19世紀至20世紀中葉和20世紀50年代三個時期分別呈現(xiàn)“哲人之邦”“衰朽之邦”和“兄弟之邦”三種套話,它們是俄羅斯自我意識的外化形式;[49]田慶立提出,日本通過“他者”中國的映照確立“自我”的主體意識,從而在民族認同層面樹立信心和權威;[50]張燕通過對韓國電影的研究認為,對中國的塑造是為了折射出韓國自我的歷史焦慮、文化尷尬、民族情緒。[51]
(三)“他者”的他塑與自塑
中國希望向世界展現(xiàn)良好的、積極的國家形象,在國際輿論場上占據(jù)主流的地位;誠然,國家實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大幅提升。然而這一令國內(nèi)自豪的形象,在對外傳播的時候,與國際形象之間可能存在較大距離。畢竟國家形象在傳播——尤其是通過間接媒介傳播和被海外受眾認知的過程中——會存在著“走形”和“扭曲”。
蒙象飛認為:一國的國家形象形成于國家間的社會互動與博弈,是本國自我話語描述和他國話語描述相互博弈的結果。[52]按管文虎所說,國家形象包括“我形象”(內(nèi)部公眾心目中的形象)與“他形象”(外部公眾心目中的形象),而兩個形象之間的差距,正是導致中國形象“他者”化的重要原因。[53]我們在對一個民族進行認知時,大多是通過想象來達成的。安德森把“民族”視為“想象的共同體”[54],是社會與文化建構的產(chǎn)物。也就是說,“對異域的想象在辨識民族共同體的特性……中發(fā)揮扮演著至關重要的作用”[55]。在想象過程中,異域所指涉的“他者”形象成為一個民族的海外身份。
沈影、吳剛認為,國家形象的建構分為行為主體自己的塑造和其他行為主體的塑造,即常說的“自塑”和“他塑”。[42]從“他塑”的角度講,國家對自己的國家形象恐怕是難有作為的。“如果外界對一個國家的認識充滿了主觀判斷,該國無法從根本上扭轉這種局面,最多可以通過論爭、批判等手段減低他人對自己的判斷的偏差”[45](65)。從“自塑”來看,國家可以通過自己的行為方式來塑造自己的形象。盡管可能會陷入“當局者迷”的困境,但“自我審視的視角更有助于深度地認識中國形象的文化內(nèi)涵和底蘊”[56]。
然而,學者們普遍認為,國內(nèi)的形象“自塑”存在一個誤區(qū),即使是用自己的眼光審視自己,也難免帶有“他者”的色彩。不管是文學創(chuàng)作,還是影視詮釋,似乎只有那類能迎合西方人的對異國情調的詮釋,才可能獲得世界認同——“他者”的痕跡通過這種方式加諸到國人身上。按馬婷的觀點:“中國的精英知識分子與西方論述形成了合謀,共同發(fā)明創(chuàng)造了中國的國民性問題”[57]。換句話說,我們的“自我言說”大多是針對“他者言說”的一種屈服,由此我們“陷入到一個被動解釋、追求情感性共鳴、進行功利主義的現(xiàn)實選擇的陷阱之中”[58]。同時,盡管中國的知識精英致力于“文化輸出”,但“超越西方話語的意圖最終被解構,自我言說亦被納入西方價值體系之中”[59]。因此,學者們提出要警惕中國是否已經(jīng)喪失了表述自己的話語權,并應該樹立其“自我言說”的主體性意識來塑造自身的形象。
(四)大眾媒介策略
媒介如何呈現(xiàn)中國,關系著世界如何看待中國,關系著他國人民如何認知中國。不管是國外媒體還是本國媒體,都有很多可選擇的策略和可玩弄的伎倆。很多研究者關注到了國外媒體在涉華報道中所使用的框架和所持的傾向。
戴元光和邵靜研究發(fā)現(xiàn):《紐約時報》通過增加來自美國消息源數(shù)量和削弱中國方面的消息源數(shù)量來達成報道,尤其是在對中國政治問題進行呈現(xiàn)時,總擺出一副“旁觀者清”的姿態(tài),抓住每一次機會對中國所面臨的問題以及發(fā)展方向進行指點和評判。[10]黃敏則認為,《紐約時報》通過對各方話語的巧妙選擇和強調,為人民幣匯率議題建構了一個是非鮮明的道德框架,并在其中塑造了一個自私卑鄙的中國。[60]這些媒體策略都有意無意地扭曲了中國的形象。
當然,國內(nèi)媒體并非束手待斃,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媒體通過自己的題材選擇和報道方式來試圖呈現(xiàn)一個立體的、豐滿的中國形象。在“中國夢”的藍圖之下,習近平提出媒體要“講好中國好故事”,這也為國內(nèi)媒體的中國形象傳播提出了戰(zhàn)略性任務。趙新利、張蓉認為:“當前中國國家敘事依然面臨著形象上的‘高大全’、形式上的‘催淚彈’,以及人文關懷的缺失等困境”[61],因此提出要從個人故事、地方故事、國家故事三個層面來落實中國形象故事化傳播的策略。
(五)日常生活與娛樂建構
國家形象往往是以具體的敘事形態(tài)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因此,站在官方的立場傳播國家的、整體的形象,其效果可能不如“潤物細無聲”式的日常生活建構和娛樂建構。正如吳衛(wèi)華所揭示的好萊塢通過娛樂方式塑造的中國形象:“將有關中國形象的議程設置巧妙地具體化或簡化為丑化中國人的橋段,把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反華意涵與好玩刺激的娛樂形式捆綁在一起”[62]。為了對抗這種形象的扭曲,我們在國家形象傳播時除了注重“國家公關”和宏大敘事外,也要通過日常敘事來進行民間文化傳播。
不管是媒介敘事還是人際敘事,在對日常生活的娛樂化描述中,雖然缺乏明確的政治符碼和國家意象,但總能從具體的人物形象中抽繹出具有概括力的文化精神。以影視劇的敘事模式為例,雖然大多影視劇都是調用的日常生活素材,表面上,海外觀眾以一種輕松的娛樂心態(tài)觀賞中國影視劇,但是,“大量的影視作品在跨文化語境中連續(xù)、重復傳播后,逐漸積累起關于中國的印象、經(jīng)驗與知識,這種日常生活形態(tài)就開始發(fā)揮隱形的政治功能,演變成建構中國形象的基本元素,產(chǎn)生一種帶有情感傾向與政治判斷的中國形象”[63]。由此,研究者們認為中國形象傳播應該更多著力于微觀敘事,增加普通公民的日常形象,并更多地借力娛樂來達到傳播目的。
縱觀中國的國家形象傳播現(xiàn)狀,盡管其中有關傳統(tǒng)文化的某些內(nèi)容能夠被世界所接受,甚至受到推崇,但是在政治文化方面卻經(jīng)常遭遇抵抗。因此中國的形象傳播要善于利用自己的優(yōu)勢,“以網(wǎng)絡敘事和生活敘事融匯宏大敘事”[64],先文化走出去,再政治走出去,以日常生活和娛樂的方式加以形象建構,最終塑造一個豐滿的、立體的、多元的中國形象。
五、結 語
十余年來,伴隨著國家形象傳播意識的蘇醒和力度的加大,關于中國形象的研究也逐漸成熟。國內(nèi)諸學科雖然用力不均,但幾乎都對此有了初步的關切,除了對歷史的回顧、現(xiàn)狀的描述,還出現(xiàn)了一些帶有反思性質的聲音。
通過對中國形象國內(nèi)跨學科研究的內(nèi)容分析和詞頻分析發(fā)現(xiàn),當前研究中尚存在一些不足,需要得到正視和修正。
從研究概況上看,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之后,中國形象得到了普遍關注,相關研究風起云涌。在研究主體方面,大多數(shù)研究者都來自高校和研究機構,從學者的視角看待中國形象問題難免有些紙上談兵,對此有深切體會的傳媒機構和政府機構卻少有嚴謹?shù)难芯坑懻摚@種“學界一頭熱”的現(xiàn)象使得對中國形象的研究不接地氣。
從內(nèi)容來看,大多數(shù)研究都注重國家整體形象的討論,忽略了區(qū)域形象和個體形象。然而,不管是人民、政府、城市、媒體還是企業(yè),又恰恰是中國形象最直觀的載體。在認知區(qū)域方面,研究往往關注中國形象在西方國家和中國鄰邦的傳遞,非洲、南美等地區(qū)的中國形象是被忽略的,甚至中國公眾對本國形象的認知也鮮有學者關注。在認知載體上,網(wǎng)絡新媒體作為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重要的國家形象傳播渠道,卻為大多數(shù)研究者所忽略。
相關研究在理論建構方面也不容樂觀。現(xiàn)有理論過于單一,大多數(shù)學者在討論“中國形象”時傾向于單純的現(xiàn)象闡述或從“現(xiàn)象到對策”,既不能從理論中闡發(fā)現(xiàn)象,也不能通過研究抽繹和闡釋理論,理論不管是作為一種工具還是作為一種成果都是欠缺的。如傳播學者在討論中國形象時,往往局限在慣用的刻板印象或框架理論上,對其他學科理論少有涉及。因此,中國形象研究有著寬廣的理論提升空間。
在研究方法方面,從本文的內(nèi)容分析和詞頻分析來看,很多研究缺乏科學的研究方法,尤其是量化方法。國內(nèi)的學者一般通過對個案的觀察,或對文本的研究,總結出帶有一定普適性的結論。即使少數(shù)研究通過量化的手段考察中國形象,大抵也是對民調結果進行匯報,沒有考慮影響因素等問題。由于研究中實證材料的缺乏,又鮮有一手田野資料,很多研究結論都是在主觀的、經(jīng)驗的判斷基礎上得出的,總體缺乏說服力。
此外,縱觀學者們對中國形象的研究結論,大多只關注到中國在其它一國的形象塑造,并且聚焦于正面弘揚,缺少對自身不足的分析和批評。同時,國內(nèi)研究似乎默認西方天然占據(jù)主動地位,所關注的焦點往往是他們?nèi)绾闻で覀儯约拔覀冃枰⑶胰绾芜M行反抗,而缺乏關于中西方國家形象傳播的比較研究,也缺乏一個相對平等的、平和的視角。
綜上所述,未來中國形象研究具有較大的提升空間,在研究內(nèi)容上,除了國家整體形象之外,還應加強人民、城市、媒體、企業(yè)等形象研究;在認知區(qū)域上,除了歐美發(fā)達國家之外,也要關注亞洲、非洲、南美等發(fā)展中國家;在形象載體上,除了傳統(tǒng)媒體之外,更需加強網(wǎng)絡媒體研究;在理論建構方面,在描述公眾形象認知的基礎上,應該深入探索不同維度的中國形象在不同國家和地區(qū)的形成過程和機制,及其背后的宏觀社會力量和微觀影響因素;在研究方法方面,除了文本分析和個案研究之外,還應加強量化研究,特別是通過大數(shù)據(jù)的方法,充分利用網(wǎng)絡數(shù)據(jù)的時空信息,對社交媒體時代的全球中國形象進行更加準確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