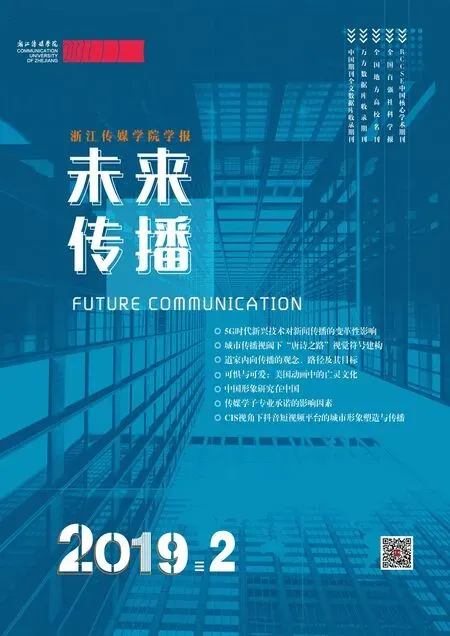回顧與反思:國內英尼斯傳播思想研究述評
汪 旭
自1998年9月媒介環境學派的制度化組織——媒介環境學學會由波茲曼一手創立算起,這一年輕的、從不缺乏爭議的研究范式歷經了從“邊緣”到“廟堂”的過程。在幾代學人共同的建設下,媒介環境學派已然成為傳播學領域與經驗學派、批判學派并列的三大學派之一。媒介環境學會的20周年年會也回到學派思想重要的誕生地——多倫多大學舉辦,會議主題為:“媒介倫理:互聯世界中的人類生態(Media Ethics:Human Ecology in a Connected World)”[1]。之所以說多倫多大學是媒介環境學思想最重要的誕生地,是因為早在學會組織正式成立之前,多倫多大學就匯聚了當時的“多倫多雙星”——英尼斯與麥克盧漢,其中英尼斯更是后世媒介環境學派的思想奠基人。
正如美國傳播學者羅杰斯(E.M.Rogers)在《傳播學史》中所說,任何涉入一條新的河流的人都想知道這里的水來自何方,它為什么這樣流淌。本文試圖對作為日益壯大的媒介環境學派的源頭的英尼斯的傳播思想進行重新觀照、整理,并將國內對于英尼斯傳播思想研究劃分為三個階段,發現研究現狀中存在的問題,并提出一己之見以求教于方家。
一、20世紀90年代:英尼斯傳播思想的傳入、介紹階段
1989年,我國學者徐達山譯介了多倫多大學麥克盧漢文化及技術研究所朱迪斯·拉扎爾的文章《傳播科學往何處去?》一文,文中提到:“傳播研究的歷史向來是與技術發明相呼應的……英尼斯這位傳播理論大師曾經說過,傳播技術方面發生的變革必然會引起思維方式和社會組織方面的變革。”[2]這是英尼斯最核心的思想與中國新聞傳播學界的初次會面。以此為始,國內一批具有高度學術敏感與前瞻的學者開始在著作與論文中介紹英尼斯的傳播思想。上海大學戴元光、張詠華教授與浙江大學邵培仁教授是其中的代表,他們分別在《傳播學原理與應用》(蘭州大學出版社,1988)、《大眾傳播學》(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2)和《傳播學導論》(浙江大學出版社,1997)等著作中對英尼斯的“傳播偏向論”做了簡要介紹。而與此同時,時任暨南大學教授陳衛星在《麥克盧漢的傳播思想》(新聞與傳播研究,1997.4)一文中以麥克盧漢的“啟蒙者”和“理論先行者”的角度對英尼斯進行了介紹,文中開辟了專門的篇幅闡述英尼斯“傳播的傾向”與媒介和權力“相互決定”的關系兩個概念對麥克盧漢的啟發。其中提及了《帝國與傳播》(EmpireandCommunication)與《傳播的傾向性》(TheBiasofCommunication)兩部著作,但或許由于時代與文章主題偏向的原因,作者僅將“帝國”理解成“英國和美國對加拿大的支配”,而非我們后來認為的更具概括性的宗教性組織與世俗權力國家。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王怡紅教授在《“憂慮的時代”與不憂慮的麥克盧漢》(國際新聞界,1997.1)中同樣從英尼斯對麥克盧漢的影響入手,簡要介紹了英尼斯的研究方法。需要提出的是,作者在文中將英尼斯與麥克盧漢表述為師生關系至今仍未得到有力的證明。香港浸會大學李月蓮教授發表《外來媒體再現激發文化認同危機》(新聞與傳播研究,1998.4)與北京廣播學院王緯《哈羅德·英尼斯傳播理論與美加文化戰》(現代傳播,1999.2)以英尼斯的“中心—邊緣”與“傳播的偏倚”理論為依據,從電視與廣播發展的實際情況分析了美國對加拿大的文化滲透現象和加拿大所做出的反滲透的努力,較早地關注了英尼斯傳播理論中美國文化滲透這一現象。
回顧這一時期的英尼斯研究我們可以發現,20世紀90年代英尼斯的傳播思想被正式引入中國傳播學界,無論是教材著作還是期刊論文中所提及的英尼斯,都與麥克盧漢有著緊密的聯系,甚至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麥克盧漢研究展開后的衍生物。根據中國知網數據庫新聞傳播學科條目下關于英尼斯研究的計量化可視分析的文獻關鍵詞共現網絡顯示(見下圖),在國內的英尼斯相關研究文獻中,“麥克盧漢”始終是最主要的關鍵詞之一。
但事實上,早在英尼斯轉入傳播研究領域之前,他已經憑借著關于鐵路、木材、鱈魚等“大宗商品”研究成了加拿大頗有名氣的政治經濟學家,當他沿著木材——紙漿——報紙這一路徑在生命的最后10年投入傳播研究時,并沒有引起世人足夠的重視。而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多數人對于英尼斯和他的傳播思想的了解,往往要經由他在多倫多大學的“明星”同事麥克盧漢這一渠道。英尼斯的兩本傳播學著作《帝國與傳播》《傳播的偏向》均由麥克盧漢作序并大力推崇,序中麥克盧漢謙虛地說:“我樂意把自己的《谷登堡星漢璀璨》看成是英尼斯觀點的注腳。”[3]
二、21世紀第一個10年:英尼斯研究的上升階段
時間進入21世紀,以互聯網為技術支撐的各項新媒體技術在我國蓬勃發展,人們越來越重視媒介技術在社會文化和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國內對于英尼斯的研究也從最初的傳入、介紹,進入了上升、探討的階段,形成了一次研究小高潮。其中十分重要的現實前提是英尼斯的傳播研究著作《帝國與傳播》《傳播的偏向》被正式引進國內。
2003年,由深圳大學何道寬教授翻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英尼斯的重要代表作《帝國與傳播》《傳播的偏向》在國內面世,這標志著英尼斯的主要傳播思想較為系統、完整地引入中國,為國內學者對英尼斯的研究與探討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如果說20世紀90年代由于時空距離、語言障礙等原因帶來的“時差”,國內英尼斯研究還屬萌芽初期,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誠然是英尼斯研究逐步鋪開、熱度提高的上升期:北京工商大學徐佳權在2004年第3期《國際新聞界》發表的《傳播圖景中的制度——由英尼斯的媒介理論談起》中以英尼斯的媒介理論為基礎,從制度分析的角度將傳播現象劃分為“媒介形態、媒介—社會機構和媒介—社會文化”[4]三個維度進行分析,進而為傳播媒介和社會生活的關系提出了一個“去魅”的解釋。蘭州大學唐克軍的碩士論文《哈羅德·英尼斯的傳播思想研究》是對英尼斯傳播思想較為完整的一次梳理。復旦大學李潔在博士論文《傳播技術與共同體:文化的視角》中,作者剖析了英尼斯與麥克盧漢的傳播思想與研究路徑,試圖回答“傳播技術能否促成人類社會實現共同理想”這一元命題,其中將研究對象與加拿大這一民族國家的獨特歷史文化背景進行深層聯系,提出了“技術民族主義”的國家悖論,具有很強的現實價值。張廣生則在《媒介與文明:伊尼斯傳播理論的政治視野》中試圖從政治學視野入手,認為“帝國是傳播及其媒介在一個文明中最終政治效果的表征”[5],但全文仍以對英尼斯傳播理論的描繪為主,同時將英尼斯對于口頭、印刷傳統的偏好與德里達的“音位中心主義”與邏各斯中心主義相聯系,提供了具有價值的思考。深圳大學李明偉在《作為一個研究范式的媒介環境學派》中以庫恩的“范式”概念論證了媒介環境學派的合法性,認為英尼斯“開啟了對媒介本身及其重要社會歷史意義的研究新領域”[6],并且對麥克盧漢產生了巨大影響。李明偉隨后在《凡勃倫對伊尼斯傳播理論的影響研究》(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5)一文中專門梳理了英尼斯具有的經濟學背景以及制度經濟學家凡勃倫在整體、動態性的研究方法論和“壟斷”“偏向”等關鍵概念上對英尼斯的啟發。
三、2011年至今:英尼斯研究的成熟期
2010年以來,在前人探索的基礎上,國內對于英尼斯的研究進入了成熟期,越來越多的學者跳脫出理論闡釋、全面出擊的研究框架,開始對英尼斯思想從不同側面進行深入剖析,進行了一系列的創新。這一階段英尼斯的著作《帝國與傳播》《傳播的偏向》(雙語版)以及他最后一部作品《變化中的時間觀念》(ChangingConceptsofTime)均由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出版。《變化中的時間觀念》的出版標志著英尼斯的“傳播學三部曲”悉數引進國內,而雙語修訂版的出版則使得國內讀者對于英尼斯的傳播思想有了零距離接觸的機會。與前兩部著作不同的是,《變化中的時間觀念》不再繼續闡釋有關時間、空間和媒介的理論,用英尼斯的原話來說:“(《變化中的時間觀念》)書中收錄的文章試圖將《傳播的偏向》和《帝國與傳播》的主題用于解答現實的問題。”[7]其中最重要的是對美國帝國主義傾向的深刻揭示與批判,這也為新時期的英尼斯研究提供了更加深入的方向。
這一時期研究最大的創新或特征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一是人們開始反思對英尼斯研究的完整性,并思考他在媒介研究學術譜系中的定位。廈門大學劉東萊博士在英尼斯帝國論與偏向論之外強調英尼斯在大宗商品原材料生產、運輸、流通,即物質生產而非物質特征的重要性(湖北大學學報,2011.3)。華東師范大學魏少華博士深入考查了英尼斯的學緣背景,討論了英尼斯媒介論與傳播學三大流派的相互關系(社會科學家,2013.3)。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湯文輝《出版自由與傳播壟斷——論哈羅德·英尼斯對媒介帝國主義的批判》(現代出版,2013.6)一文沒有過多地將關注點放在英尼斯的“偏向論”上,而認為英尼斯是“最早發現傳播體制中的帝國主義的學者”[8],將文章的重點放在英尼斯對美國所強調的出版自由所帶來的傳播壟斷的批判上。二是運用英尼斯傳播思想作為理論基礎,進而對其他研究對象或領域進行探索的研究開始出現,這也意味著國內對于英尼斯的相關研究進入了從介紹到闡釋、從探討到應用的成熟期。華中師范大學鮑立泉在《新媒介群的時空偏向特征研究》(編輯之友,2013.9)中運用英尼斯的媒介偏向論與萊文森的技術補救論為理論依據,審視今天以數字傳播技術為基礎的媒介集合(文中稱之為“新媒介群”)的發展趨勢與演進邏輯。中國人民大學李沁在《泛時代的“傳播的偏向”及其文明特征》(國際新聞界,2015.5)中,在新時代的背景下重新闡釋了英尼斯的“偏向論”,提出在互聯網文明下沉浸傳播的模式中,傳播的偏向是“人”這一全新命題。南京大學唐利在《百度百科的知識傳播偏向研究》(南京大學碩士論文,2014)中,從波茲曼劃分的“符號環境、感知環境和社會環境”[9]三個層次上,考察百度百科在知識傳播中的媒介特性和技術偏向,這也是運用傳播偏向等理論進行新時代具體對象研究的成功案例。
四、結語:對于英尼斯研究現狀的反思
通過對國內英尼斯主要研究的階段性劃分進行回顧可以發現,雖然英尼斯的思想地位及研究方式較最初引入時已經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我們認為,目前國內對于英尼斯的研究還遠遠稱不上到達“黃金期”“爆發期”,人們雖已從不同角度談及英尼斯的思想理論、發表觀點,但卻沒有更多的反思或者碰撞,形成高度集聚活躍之勢。作為英尼斯思想的重要推廣人,何道寬在2013年修訂版《傳播的偏向》序言中就曾呼吁國內學界應當重新重視英尼斯的傳播思想以“挽回因我們曾經的怠慢而造成的損失”[3](9)。但從現實情況來看,國內研究仍存在以下幾點不足:
(一)對英尼斯學術背景的忽視。英尼斯有著不可分割的政治經濟學家與傳播學家雙重身份,十分善于運用跨學科的研究方法,英尼斯本人也極力反對“專家化”“專門化”這一趨勢。英尼斯的傳播學研究是他前期經濟學探索的自然延伸,他在論及加拿大政治經濟形成時期的研究成果為后期的傳播研究做了鋪墊,而后期的傳播學著作又是前期經濟學研究的進一步展開和闡述,而貫穿始終的是他對制度權力關系、技術文化演進以及對于集中化控制與西方文明危機的關注。在目前的研究中,多數學者都已經認識到英尼斯經濟學背景的重要性,所做研究中均有所提及,但在實際情況中,能夠對英尼斯政治經濟學背景進行深挖,細致探索他從經濟學至傳播學轉向并闡釋其中聯系的研究依然缺乏。這其中存在文獻資料的原因,相關英尼斯的權威傳記,如海耶爾(Paul Heyer)所著的HaroldInnis,華生(Alexander Watson)的MarginalMan:TheDarkVisionofHaroldInnis及其他重要相關著作尚未引入國內,這在某種程度上也阻礙了我們對于英尼斯學術生平與研究方法的全面深挖與理解。
(二)對英尼斯學術歸屬的糾結。學派的劃分為我們系統了解有著共通理論背景、相似研究方法和共同現實關懷的學者群體提供了極大的幫助,也讓我們更好地理解和梳理某一學科領域的格局版圖。但由于學派的劃分,也使得少數研究者易對特定對象形成“標簽化”的印象。以英尼斯為例,麥克盧漢認為:“他應該是以帕克為首的芝加哥學派的最杰出的代表。”[3](33)而詹姆斯·凱瑞則否定了英尼斯與帕克的師承關系,并認為英尼斯不應當劃歸為任何一個學派。而媒介環境學會的創始人波茲曼則將英尼斯奉為學派的思想奠基人,稱其為“現代傳播學之父”[10],這也是我們對于英尼斯學派歸屬最普遍的看法。對于英尼斯這種學科背景復雜、研究領域廣泛的學者而言,既不宜草率地將其劃入“技術決定論”的范疇,更不能忽視他在其他方面,如批判思想、社會關懷等方面的突出貢獻,任何簡單的標簽化解讀和過多學派歸屬上的糾結與爭辯都將對英尼斯思想的深刻性與全面性造成巨大的傷害。
(三)對英尼斯思想理論與方法論貢獻的探索仍待提高。眾所周知,對傳播學科有著初創之功的拉扎斯菲爾德、拉斯韋爾、霍福蘭、盧因均來自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其他領域,他們憑借著原始的理論基礎、跨學科的視野以及對傳播現象的關注,使得傳播學在創立之初便成為一門涉及面極廣、包容性極強的學科。但遺憾的是,這四大奠基人在傳播學領域綻放光彩之后旋即回到了最初的研究領域。傳播學自身的研究理論與方法在發展中卻很少與其他學科產生聯系,同樣缺乏直接的方法論貢獻。這或許不僅是英尼斯個人思想理論面對的問題,且極有可能是整個傳播研究領域所面臨的困境,此處僅將英尼斯的傳播理論作為個案代表舉例。1999年,美國著名新聞傳播刊物《新聞與大眾傳播季刊》(Journalism&MassCommunicationQuarterly)冬季號曾經綜合調查眾位行業專家意見,評選出35本“20世紀最重要的新聞與傳播學著作”[11],其中就包括英尼斯的《傳播的偏向》、羅杰斯的《創新與擴散》等。可見英尼斯傳播思想的理論價值已經從最初人們談到麥克盧漢時附帶提及,上升為世人公認的最重要的傳播思想理論之一。但有學者通過美國社會科學文獻檢索系統(JSTOR)檢索發現:“除了羅杰斯的創新擴散理論被社會學、營銷學和農業推廣學之類學科廣泛引用之外,其他的傳播學著作被傳播學之外的學科引用的量并不大,有些著作甚至從未被引用過。”[12]
因此,通過對英尼斯傳播思想研究的回顧與反思,如何突破既有文獻積累與研究框架,是否能在英尼斯相關研究中進一步探索更加具有現實價值與意義的銳利方向,乃至提供跨領域方法論的創新與貢獻,都是在未來的研究中保持英尼斯傳播思想鮮活力與生命力所將面臨的嚴峻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