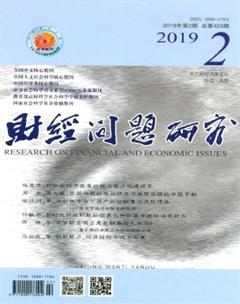流動性沖擊下資產折價銷售與風險傳染
宗計川 李紀陽 張睢



摘 要:理論研究與現實觀察均表明,流動性沖擊具有高度不確定性和傳染性。如何防范流動性沖擊觸發資產折價銷售進而演變成系統性風險,是當前金融監管的重中之重。以往的研究主要基于銀行間市場,很少針對資本市場。對于那些面臨贖回壓力的基金而言,當遭遇流動性沖擊時,市場極易形成“贖回壓力—拋售股票—股票價格下跌—贖回擴大—拋售股票”的正反饋,致使股票價格偏離基礎價值而持續下跌。基于此,本文首先針對股票型基金在贖回壓力下的資產折價銷售進行市場檢驗。繼而,在實驗室的市場環境下,采用協調博弈實驗,對流動性沖擊下的資產折價銷售進行了檢驗。實證和實驗結果均表明:在贖回壓力下,流動性沖擊極易觸發資產折價銷售,并通過資產拋售將這一風險傳染到所有的市場參與者。本研究事實上提出了一種監管干預思路:在折價銷售循環開始之初,監管部門介入資產市場以阻止資產價格的螺旋下降,進而防止基金融資能力的下降,以期阻斷因折價銷售而引起的風險傳染。
關鍵詞:流動性沖擊;資產折價銷售;風險傳染;實驗室研究
中圖分類號:F832.5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9)02-0043-10
一、引 言
防范金融系統性風險的發生是當前金融市場監管的重點,而防止流動性沖擊演變成系統性風險則是重中之重。理論研究與現實觀察均表明:流動性沖擊具有高度不確定性和傳染性。世界范圍內的金融危機表明:債務違約與減價出售往往同時發生,并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單獨的資產負債表債務關聯渠道難以造成大規模的傳染,而資產價格渠道卻可以引發大規模的金融機構接連倒閉。始于直接傳染的流動性沖擊在資產折價出售的作用下,誘發流動性傳染正反饋,進而觸發系統性風險[1]。
當流動性沖擊形成或危機出現時,由于對未來流動性稀缺的預期,使得資產持有者(投資者)一致性地采取兩種策略:貯存流動性與超規模的資產銷售,進而引起資產的重新定價,此即為資產折價銷售的本質。資產的重新定價(折價)進而引發更大規模的資產拋售行為,進一步加重未來流動性稀缺的預期,導致所有市場參與者,無論是否一開始受到流動性沖擊,均加入到資產折價銷售中,并通過資產價格的急劇下跌,將流動性沖擊的風險傳染到市場所有個體。因此,不管是否源自違約,只要發生流動性沖擊,則存在很大的概率出現資產折價銷售,并將風險傳染給其他市場參與者。
對于流動性沖擊引發資產折價銷售,進而導致風險傳染并引發系統性風險這一問題,學術界主要從銀行間市場進行了較為廣泛的研究[2]。然而,基于對2015年中國資本市場短期巨幅下跌情況的觀察,學者開始關注資本市場流動性沖擊與資產折價銷售之間的關系。特別是中國股市存在日10%的漲跌幅限制,很容易在正常交易日中由于股價的迅速下跌而使交易停止,導致流動性枯竭。受到流動性沖擊或面臨流動性約束(如基金面臨贖回)的投資者在當日無法獲得所需流動性,其策略除了在其他市場上出售資產之外,唯一的選擇是在接下來的多個交易日連續低價出售資產,直至滿足其流動性需求。2015年,在短時期內連續出現的十多次“千股跌停”,為這一判斷提供了現實證據。
特別是對于那些面臨贖回壓力的基金,當市場處于單邊下跌階段,為了獲得所需之流動性,市場極易形成“贖回壓力—拋售股票—股票價格下跌—贖回擴大—拋售股票”的正反饋,使得股票價格偏離基礎價值而持續下跌。更為嚴重的是,由于投資理念趨同及投資風格模糊,基金間存在較為嚴重的資產重疊,這使得持有相同資產的基金也會遭受贖回,并加入到資產折價銷售行列中來,造成股票價格螺旋下跌。在上述渠道和機制作用下,相對較小的沖擊也可能引起流動性迅速枯竭,從而將這一風險外溢到其他資本市場,進而可能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因而需要引起高度重視。
目前對于開放式基金流動性風險的研究主要集中成因、度量和管理等方面,而較少討論其風險傳染機制。鑒于此,本文首先實證檢驗了基金是否會因流動性約束而被迫出售股票,從而對持有這些股票的其他基金帶來壓力,由此導致市場的折價銷售,其核心在于判斷被出售的股票是由贖回壓力而非信息驅動所致。進而在實驗室環境中,研究受流動性沖擊的個體如何通過資產折價銷售,將流動性風險傳導到其他個體,以及在給定不同程度和結構的沖擊下,資產折價銷售價格曲線如何變化,并檢驗在此過程中參與人的預期與協調。實驗結果表明:在流動性沖擊條件下,參與人之間是否能有效進行協調是決定資產折價的主要因素,而資產折價銷售曲線的形態受制于參與人之間的協調及流動性沖擊的規模與結構。此外,參與人在實驗中表現出一定的學習效應,通過改變參與人的預期可以增強參與人之間的協調,從而有效阻斷流動性風險的傳染。
本文研究的起點是在已經發生流動性沖擊的情況下,市場主體間預期協調和一致性行動對資產折價銷售和流動性風險傳染的作用機制。具體地,以市場參與個體的一致行動為邏輯切入點,在給定流動性沖擊的條件下,觀測實驗個體的預期與協調,并進而對比分析在有無贖回壓力下,資產折價銷售價格曲線的變化。這對危機管理具有針對性的借鑒意義。
二、文獻綜述
現有的理論研究與現實觀察均表明:當金融機構或投資者之間存在資產與債務互聯,一個較小的流動性沖擊亦可能導致投資者采取一致性行動(拋售資產),從而加速風險傳染[3]。當市場上吸收該資產的流動資金有限時,就會引發資產重新定價。這種資產的重新定價也被稱為折價出售。
早期的研究多數集中在銀行間市場,核心問題是:流動性風險(沖擊)的傳播主要源于銀行間的高度關聯,以及銀行間采取的一致性行動,前者是風險傳染的具體渠道,而后者則是渠道傳染或正反饋機制形成的必要條件。陳冀等[4]認為流動性效應對危機的擴散起著“催化劑”的作用,即使存在非常小的流動性效應也會顯著地提高系統損失。但這一現象并非銀行間市場所獨有,在任何金融機構網絡中,只要存在風險傳染的正反饋機制,那么一個局部沖擊就存在較大概率演變成系統性風險。
基于銀行間市場流動性沖擊與資產折價銷售的研究框架同樣適用于解釋資本市場,特別是關于基金公司在面臨流動性沖擊的條件下,一致性地選擇出售股票并引發資本市場的螺旋下降,這一風險傳染正反饋機制同樣存在于資本市場。當資本市場出現單邊下降時,部分基金公司在贖回壓力下,迅速受到流動性沖擊。此時對于股票型基金而言,唯一的選擇是折價出售股票資產,因為此時在正常價格下難以出清。由于基金公司持有股票資產的同構性,使得此類資產價格迅速下跌,在贖回壓力下,那些一開始未受流動性沖擊的基金公司也不得不加入到資產折價銷售中。當預期未來流動性價格上升和資產價格持續下跌成為公共知識時,所有的基金公司和資本市場投資者無一例外地選擇拋售股票。
在10%的跌停幅度限制下,市場流動性迅速枯竭,并導致這一資產拋售行為持續進行,即贖回壓力及突然的降杠桿,限制了投資者的融資流動性,而市場的跌停制度則限制了投資者的交易流動性,二者共同導致了市場流動性的枯竭,并引起股票市場價格的持續螺旋下降。在這一過程中,可明確觀測到:大量股票持續、無量跌停,市場的流動性供給功能喪失。Brunnermeier和Pedersen[5]檢驗了資產市場流動性和交易者融資流動性之間的關系,指出:交易者提供市場流動性的能力取決于其融資能力,而融資能力又取決于其資產的市場流動性。
對于這一正反饋機制,2007—2009年的美國次貸危機提供了很好的現實證據。由雷曼公司破產倒閉而引發的資產折價銷售,導致基金和銀行等金融機構大面積違約,進而使其持有的證券大幅減值,極大地弱化了銀行和基金的融資能力,最終造成系統性違約[6]。在此情況下,資產自身的基礎價值或資產組合本身的優劣并不能解釋資產價格的持續下跌,資產價格“雪崩”的唯一解釋是:贖回導致流動性沖擊,進而引發資產折價銷售,傳染到其他投資者并進一步加劇贖回壓力,在跌停限制下,整個市場的融資流動性和交易流動性枯竭,資產價格完全不能反映實體面特征,變成了凱恩斯所說的完全的貨幣(即流動性)現象。
有關基金贖回行為的研究主要從基金的業績表現與行為金融兩個方向展開,現有的研究表明,并非只在股票價格下降階段時才出現大規模贖回現象,隨著基金業績增長, 贖回率不但沒有下降反而上升,即存在“贖回困惑”現象。張家萃等[7]、陸蓉等[8]的研究也得到了一致的結論:基金業績與資金流入呈負相關,即基金凈值增長率越高,面臨的贖回壓力越大,遭遇贖回的份額越多。這也說明,基金遭遇贖回的壓力并不一定發生在股價單邊下跌階段。而蘇曉萌[9]也從經濟學視角研究指出:在開放式基金面對的風險當中,流動性風險是最為顯著也是最為突出的一個。
資本市場普遍存在的羊群行為(Herd Behavior)則進一步加大了上述正反饋機制形成的概率。Lakonishok等[10]通過對769家股票型基金進行檢驗發現:基金在交易小市值股票時的“羊群度”高于大市值股票。Wermers[11]以 1975—1994 年間美國股市的所有基金為研究對象,通過改進羊群度量方法[10]對美國基金進行研究,發現整體存在羊群行為,且成長型基金和投資小盤股票基金的羊群行為更為明顯。陶瑜等[12]對中國2005年1季度至2014年2季度證券投資基金的投資行為進行研究發現,相比發達國家,中國證券投資基金在策略交易時存在明顯的羊群行為,基金在交易中,小盤股票和市場壓力大時,羊群行為更為明顯。基金經理中普遍存在的羊群效應,致使其資產組合存在高度的交疊性,而這種資產組合的重疊所形成的市場關聯成為流動性風險的傳染與放大渠道。Coval和Stafford[13]通過研究美國共同基金資金流與其交易行為之間的關系,證實了股票市場中資產折價銷售行為的存在性。Pedersen等[6]、Ellul[14]分別對可轉換債券和企業債券市場進行了研究,他們發現在這些債券市場中同樣存在著資產折價銷售行為。
在此基礎上,陳國進和胥愛歡[15]分析了中國57只開放式股票型基金在2008年1月—2010年12月每個季度公告持有的前十大股票,結果表明,在中國股票市場中存在著資產拋售行為。陳玉罡和王偉洲[16]對 2004—2010年中國的開放式基金拋售股票的行為進行研究后發現,基金在面臨贖回壓力時傾向于拋售市凈率低、換手率高的股票,拋售時會引起這些股票產生顯著的折價。Larrain等[17]分析了一個小的新興市場(智利股票市場),由于監管條例改變——降低養老基金最高持有股票占基金總資產的比例,導致養老基金開始出售股票,致使股票價格下跌,由此觀察到一個清晰可識別的股票折價銷售。
上述研究盡管在研究切入點、國別及數據選取等有差異,但所得結論均支持以下兩點:一是股票市場存在明確的羊群效應和羊群行為,且在其影響下,投資者之間在資產持有上存在重疊;二是基金面臨的贖回壓力并非只出現在股票市場單邊下跌的情境下,對基金公司特別是股票型基金公司而言,贖回壓力下的流動性沖擊隨時可能發生。市場處于一種“生態環境失衡”的狀態:機構投資者具有高度的同質性,他們通常關注同樣的市場信息,采用相似的經濟模型、信息處理技術、組合及對沖策略,機構投資者可能對盈利預警或證券中介的建議等相同的外部信息作出相似的反應。
然而,限于研究方法和數據的可得性,無論是從銀行間市場還是基金的角度,針對流動性風險傳染及資產折價銷售等問題的研究,多數停留在“面上”,較少有從行為的角度進行微觀刻畫。而要揭示當流動性沖擊出現時,投資者(基金)間的預測與協調行為如何影響資產拋售數量和價格,歷史數據很難回答,實驗室研究是一種可行的方法。正如Heinemann[18]指出:“理論是實驗室實驗與金融市場之間的橋梁,通過實驗可以檢驗理論預測并發展行為理論以進一步應用到更大的市場。”在本文的實驗設計中,正是基于基金間對流動性沖擊及其他基金間可能采取的行動和預期,并結合資產折價銷售等行為設計實驗,其理論內核則是不同基金間的協調博弈。
三、市場檢驗:股票型基金贖回壓力下的資產折價銷售
股票型基金在經歷較大的資本流出后會因流動性約束而被迫出售股票,從而對持有這些股票的其他基金帶來壓力,由此可能導致股票的減價銷售。對于該問題的市場檢驗,其核心在于如何判別被出售的股票是由贖回壓力而非信息驅動所致。本文擬采用先驗與后驗相結合的方式對其加以識別。具體而言,首先構建先驗指標對被基金出售的股票進行識別,然后根據不同屬性股票的價格走勢加以驗證:如果是因為基金被迫出售股票導致股價下跌,那么在基金度過其金融困頓期后,股價很可能出現反轉;而由信息驅動所導致的股價下跌則不會隨著基金贖回壓力的顯著降低而出現回彈。據此,借鑒Coval與Stafford[13]的基本思想,本文為股票型基金的贖回壓力導致股票減價銷售構建檢驗框架。
(一)面臨贖回壓力基金的識別
由于基金申購與贖回份額中包括的分紅轉份額并非資金流動,本文不使用凈申購份額而使用資金凈流量率作為基金所面臨贖回壓力的測度,定義為:Flowratej,t=[TNAj,t-TNAj,t-1(1+Rj,t)]/TNAj,t,其中,TNAj,t表示基金j在第t期末的資產凈值,Rj,t表示基金j在第t期的凈值回報率,即凈回報與當期基金凈值的比值。由定義可以看出,資金凈流量率反映了基金的資本流出水平,資金凈流量率越小說明基金的贖回壓力越大。
(二)股票被出售壓力指數的構建
將樣本基金按照資金凈流量率由小到大排序后等分為M組。第一組是資本流出水平最高的基金,即面臨贖回壓力最大的基金組;第M組則是贖回壓力最小的基金。對于贖回壓力最大的基金組,股票被出售壓力指數定義為:Pressurej,t=(∑i∈GroupMBuyi,j,t-∑k∈Group1Sellk,j,t)/AvgVolumej,t,其中,Buyi,j,t表示第M組中的基金i在第t期購買股票j的數量,Sellk,j,t表示第一組中的基金k在第t期出售股票j的數量,AvgVolumej,t表示股票j在第t期的平均市場成交量。股票被出售壓力指數即為贖回壓力最小基金組的購買量與贖回壓力最大基金組的出售量二者之差所得到的凈交易量與市場平均成交量之比。因而股票被出售壓力指數越小,該股票被出售的壓力越大。對于贖回壓力最小基金組,股票被出售壓力指數定義為:Pressurej,t=(∑i∈Group1Buyi,j,t-∑k∈GroupMSellk,j,t)/AvgVolumej,t。
(三)股票減價銷售的后驗分析
本文采用平均超額回報率 (Average Abnormal Return,AAR)與累計平均超額回報率 (Cumulative Average Abnormal Return,CAAR)對被出售股票的市場表現加以測度,計算公式如式(1)、式(2):
其中,Rj,t表示股票j在第t期的回報率,Rj,m,t表示股票j所在市場第t期的回報率,N表示基于被出售壓力指數所選出的股票個數。基于股票被出售壓力指數,由贖回壓力最大基金組與贖回壓力最小基金組所選出的股票,比較各期的平均超額回報率與積累平均超額回報率,據此對由贖回壓力所導致的股票減價銷售加以識別。
本文選取2016年1月1日前成立的開放式股票型基金作為研究對象,研究的時間期限為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數據來自于Wind數據庫和CSMAR國泰安數據庫。研究樣本中剔除債券型基金、貨幣型基金、混合型基金、FOF、股指期貨型基金,QDII基金和指數型基金。同時,剔除在研究期限內資產凈值、當期回報率、持有現金、投資組合等數據有缺失的基金。最終得到的基金數量為283只。根據計算出的資金凈流量率,可以將樣本基金按照贖回壓力由高至低分為五組,各組基金的特征如表1所示。從表1可以看出,贖回壓力較大基金組的當期回報率普遍較高,反之亦然。已有研究發現,中國開放式基金的資金流動與業績之間呈現負相關,面臨較大贖回壓力的往往是業績良好的基金而并非業績較差的基金,即存在所謂的“贖回困惑”現象。贖回壓力最低的基金組比贖回壓力最高的基金組具有更高的現金持有比重。這表明贖回壓力最高的基金組用以應對贖回的現金儲備可能并不充足,從而可能被迫出售股票以滿足其流動性約束。相較于贖回壓力較小的基金組,贖回壓力較大的基金組通常持有更少的股票種類。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贖回壓力較大的基金更傾向于通過出售股票以緩解其贖回壓力。
以表1的分組為基礎,本文選取贖回壓力最高基金組與贖回壓力最低基金組的半年報與年報所披露的持倉股票作為樣本,并根據以下指標篩選樣本:股票回報率和市場回報率等數據沒有缺失,股票買入與賣出次數總和不小于10,股票被出售壓力指數小于0。最終得到滿足以上條件的贖回壓力最大基金組所出售的股票70只,而相應的贖回壓力最小基金組所出售的股票為26只。基金半年報中包含了6個月的基金信息,本文將所研究時間范圍的前6個月視為股票的拋售期。表2總結了贖回壓力最大基金組所出售的股票與贖回壓力最小基金組所出售的股票在拋售期與拋售期后6個月的平均超額收益和累計平均超額收益。
由表2可以看出,贖回壓力最大基金組所出售股票的CAAR在拋售期內持續下降,在拋售期最后一個月開始回彈,且在拋售期后第6個月基本達到拋售期初的水平。贖回壓力最小基金組所出售股票的CAAR在拋售期內一直下跌且在拋售期后繼續呈現下跌趨勢,并未出現回彈。這表明面臨巨大贖回壓力的基金在短期內可能通過出售股票來獲得流動性,而持有相同股票的基金也同樣面臨相同的困境無法買入該類股票,導致股票價格下跌,在基金金融困頓消失后,又會重新買入此類股票,使得該類股票的價格回歸基本面價格。
綜合以上分析可知,由于贖回壓力所導致的股票減價銷售在中國股票市場是普遍存在的。基金在面臨贖回壓力時并沒有提高現金持有比例,導致在遭受大規模贖回時,短期內只能通過出售股票來獲得流動性。且由于開放式基金存在較嚴重的羊群行為,投資理念趨同及投資風格模糊使得基金間資產重疊度加大,這就導致某些基金在出售股票時對持有相同資產的基金造成影響,進而也會遭受贖回壓力,形成正反饋效應,進一步使得股票價格偏離基礎價值形成股票折價銷售,加劇市場波動,在極端情況下則會引起系統性風險。
需要指出的是,諸如以上的實證檢驗通常只能對基金贖回壓力與股票減價銷售之間的相關性進行分析,卻難以揭示其背后的機制。具體而言,采用實證方法研究贖回壓力下基金的行為決策與股票減價銷售的風險傳導有很大局限性。中國開放式基金按季披露數據,且在第一、三季度只披露前十大持有股票,數據的有限性與不確定性對構建實證模型提出了巨大挑戰。與之相比,實驗研究以理論模型假設為基礎將現實場景抽象化,通過實驗設計對無關因素加以控制,從而保證研究結論的內部有效性。因此,本文采用實驗方法研究贖回壓力與減價銷售之間的聯動機制。
四、流動性沖擊與資產折價銷售聯動機制實驗室檢驗
(一)實驗設計
本文設計實驗構建基金公司受到沖擊(遭受贖回)以后,通過出售資產應對沖擊的仿真市場環境,據此研究流動性沖擊與資產折價銷售的交互作用,進而形成風險傳導的內在機制,以及該機制的主要影響因素。主持人向參與人詳細講解了實驗說明、實驗程序截圖及注意事項,并針對實驗說明進行簡單測試,通過隨機抽簽分配計算機進行上機操作。結束后,按照一定比例將實驗中得點數兌換成現金當場支付給參與人。實驗在東北財經大學實驗經濟學實驗室進行,所有參與人均來自大連地區在校大學生,每位參與人只允許參加其中一場實驗。
實驗中,所有24位參與人隨機分為4組,每組6人。每一組相當于一個市場,市場之間彼此獨立,互不影響。本次實驗共進行24期,每12期為一個完整實驗,共進行兩個相同獨立的12期實驗,即第一個12期結束以后,重新分組并重新開始實驗,參與人在前一個實驗中的得點數不會對下一個12期實驗有任何影響。實驗一開始,每個人有兩個賬戶,資產賬戶和貨幣賬戶。初始資產賬戶有2 000單位資產,貨幣賬戶有100單位貨幣,初始資產價格為1單位貨幣。
一輪單期實驗共分為三個階段,分別為:擲色子決定當期是否受沖擊,根據受沖擊的情況決定賣出資產數量,進行流動性檢查。第一階段,所有參與人擲色子(色子有6個數字為:1、2、3、4、5、6),每個參與人只知道自己擲色子的結果。擲色子的過程由計算機完成。第二階段,當所有人確認擲色子的結果后,選擇出售資產的數量,當期資產的市場價格取決于參與人及與參與人在同一個市場中的其他參與人出售的資產數量,以及上一期資產價格。假設同一組成員投入的資產數量為Xi(i=1,2,3,4,5,6),則本期資產價格為:Pt=? [1-(∑6i=1Xi-400)/11 600]×Pt-1。根據這一價格及每個人賣出的資產數量決定在當期所獲得的流動性數量。第三階段,所有在本期擲色子的結果為2、3、4、5的參與人,在當期期末會被自動扣除100單位貨幣,即面臨100單位的流動性沖擊。同時,每一期結束時,電腦會檢查所有人的貨幣數量,若連續兩期某參與人貨幣賬戶余額小于100單位,則將會終止實驗。終止實驗的參與人的剩余資產將會在下一期由電腦全部出售,并在終止實驗的當期及以后各期均無法獲得任何點數。本項目實驗設計的一個貢獻在于單邊資產池子的設計,在本實驗中,資產價格的決定并非由買賣決定,而是由所有參與人投入到資產池子中的資產數量決定,即所有人清楚地知道投入的資產數量越多,當期實現的資產價格越低。也就是說,資產價格是所有參與人協調的結果。這一設計,一方面滿足實驗簡單化要求,盡量減少交易復雜性對實驗結果有效性的影響;另一方面,不失一般性,本實驗檢驗的核心問題是當沖擊到來時,市場參與個體之間的協調如何影響資產價格的變化。即通過參與人投入資產池子中的資產數量來分析其行為策略與預期。
對于那些選擇大量賣出資產的參與人而言,無非體現的是其對未來價格的悲觀預期,采取以鄰為壑的策略,大筆出售資產。據此,這種大筆出售資產的行為通過資產價格將這種風險傳染到整個市場,并通過正反饋使所有參與人采取相同的策略,形成系統性風險。事實上,本實驗設計的參數保證了如果所有參與人能夠成功協調:不受沖擊、不出售資產并按受沖擊比例出售資產,市場是能夠保證資產價格不變甚至上升,但實驗結果表明這種完美協調難以達成,說明正是由于參與人之間的協調失敗導致了資產折價的發生。
此外,本文實驗分為兩個不同的設計,分別為有強制贖回市場(Treatment)和無強制贖回市場(Control)。其區別在于:在有強制贖回實驗中,要求當資產價格高于0.80時,參與人受到一個隨機的流動性沖擊,而如果市場資產價格低于0.80,此時所有參與人都將面臨200單位貨幣的沖擊,以此來刻畫贖回壓力。
(二)實驗結果分析
1.資產折價銷售與流動性風險傳染
在現有實驗設計下,各期資產價格是流動性沖擊與資產折價聯動機制的直接反映。為了消除由清算機制所產生的尾部效應,本研究只選取每場實驗的前10期實驗數據。有強制贖回市場與無強制贖回市場的資產折價銷售價格曲線如圖1所示。相比于無強制贖回市場,有強制贖回市場的資產折價銷售價格曲線更為陡峭。在資產的市場價格未達到強制贖回線之前,兩種市場的資產價格均呈現出比較平穩的變化趨勢。而當資產的市場價格降至強制贖回線之后,正反饋效應使得有強制贖回市場的資產價格出現大幅下降,其與無強制贖回市場的資產價格曲線呈現出較大差異。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有強制贖回市場第三組所有參與人截至第9輪全部被清算。
為了進一步明晰正反饋機制對資產價格的影響,本文分別對對照組與實驗組在第一輪、第二輪及總體的每期資產價格差異進行統計檢驗。鑒于樣本大小難以滿足正態分布要求,本文還采用Wilcoxon Rank-Sum Test對價格差異進行檢驗。檢驗表明,價格差異統計顯著時,實驗組的資產價格更低。
由此可見,在第一輪實驗中,實驗組在第二期的資產價格顯著低于對照組,顯示出正反饋機制使得實驗組傾向于貯存更多的流動性;而自第七期開始,實驗組的資產價格顯著低于對照組,其成因一方是由于強制贖回所引發的沖擊強度提升,二是清算機制所導致的資產拋售。在第二輪實驗中,對照組與實驗組在每期資產價格上均不存在顯著差異,這表明第一輪實驗提供了學習機制,由此使實驗組與對照組在第二輪試驗中的表現更為趨同。而總體來看,實驗組在前兩期與后四期的資產價格均比較顯著地低于對照組,說明整體而言,正反饋機制促進了資產價格的下跌。
從另一個方面看,資產折價銷售曲線也可以反映流動性的傳染深度,即在市場中獲取流動性的成本變化情況。具體而言,本文將流動性的傳染深度定義為第t期與第0期為獲得1單位流動性所需出售資產之差,即(ContagionDepth)t=1/Pt-1/P0。
有、無強制贖回市場的傳染深度曲線如圖2所示。可以看出無強制贖回市場的流動性傳染深度顯著低于有強制贖回市場。在正反饋效應的作用下,隨著資產價格的降低,實驗參與人傾向于在流動性成本更低時貯存更多流動性,而這使得流動性的傳染深度進一步增強。
2.最優資產出售數量與群體協調測度
由上節分析可以得出,貯存過多的流動性是加劇資產折價銷售與流動性傳染的關鍵。在組內所有參與人完全協調一致的條件下,存在每期的最優資產出售數量。最優資產出售數量如式(3):
其中,OASt表示第t期的最優資產出售數量,NLSt表示第t期的凈流動性沖擊,即實際流動性沖擊與市場中具有足夠流動性應對沖擊(滿足本次流動性沖擊且期末仍保有足夠的流動性)的參與人所受到的流動性沖擊之差。
如果實際資產出售數量和最優資產出售數量相差比較小,則說明協調程度高。有、無強制贖回市場的實際資產出售數量和最優資產出售數量如圖3所示。大部分市場第1期實際資產出售數量明顯高于最優資產出售數量,其原因為在價格高的時候出售資產能夠貯存更多的流動性以應對未來的沖擊。當參與人對未來資產價格存在下跌預期,會傾向于通過出售資產儲存更多的流動性,進一步導致資產價格下跌,引發大量拋售資產。整體而言,有強制贖回市場中,實際資產出售數量偏離最優資產出售數量的程度,明顯大于無強制贖回市場。為進一步測度群體的協調程度,本文構建實際資產出售數量與最優資產出售數量的絕對偏離度(AD)和相對偏離度(RD),定義為:ADt=(∑10t-1|OASt-AASt|)/10,RDt=(∑10t-1|OASt-AASt|)/10。其中,AASt表示第t期的實際資產出售數量。如果AD與RD都比較小,說明市場協調度比較好;當RD較小而AD較大時,說明市場出現實際資產出售數量低于最優資產出售數量,此時正負抵消。不論是有強制贖回市場還是無強制贖回市場,實際資產出售數量對最優資產出售數量都有很大的偏離。
組內協調程度高則表現為資產折價銷售價格曲線比較平穩,通過有強制贖回市場和無強制贖回市場的對比,市場內參與人對未來可能受到沖擊的預期影響了組內協調,在未來可能遭受更多沖擊的情況下,有強制贖回市場的參與人更傾向于出售資產應對未來的沖擊,這一行為滿足個體理性,但不滿足整體理性。
本文進一步采用Wilcoxon Rank-Sum Test對有、無強制贖回市場在第一輪與第二輪RD與AD差異方面進行檢驗,其p值分別為0.11、0.34、0.06與0.89。在第一輪試驗中,實驗組的RD與AD均顯著高于對照組,表明在正反饋機制下優化資產配置更為困難,也意味著協同一致更加難以達成。而在第二輪試驗中,實驗組與對照組的RD與AD均不存在顯著差異,這表明第一輪的實驗帶來了一定的學習效應,使得實驗組與對照組在第二輪試驗中的表現更為趨同。
五、結論與研究展望
本文的研究結果表明,基金面臨贖回壓力時,將更容易誘發資產折價銷售并導致流動性傳染。由于開放式基金存在“贖回異象”特征,遭遇贖回的基金公司往往是業績良好基金,其資產配置比例較高,交易流動性往往不足。加之基金之間的投資策略一致性和資產組合的交疊性,在面臨贖回時,一致性地采取出售資產策略以獲得流動性,從而將風險傳染到整個市場。形成“贖回—拋售股票—股票價格下跌—贖回擴大—拋售股票”的正反饋效應,進一步使得股票價格偏離基礎價值,形成股票折價銷售,加劇市場波動,極端情況下會引起系統性風險。
金融系統性風險的發生具有難預測、難預防的特點,守住不發生區域性系統性風險的底線是必要的,但具有不可測性。當前的研究關注點主要集中在事先預防上,但在經歷了近40年的高增長后,需要高度關注可能的源發性金融危機。系統性風險的發生有其必然規律,關鍵在于事中干預。因此,當前需要前瞻性的研究并未雨綢繆地提出系統性風險事中干預對策。探討市場的穩定性條件和觸發機制,著力從監管層面提出可操作的宏觀審慎監管政策和不同沖擊條件下的干預手段選擇,這是目前學術界和監管層關注的焦點。
本文針對折價銷售和流動性風險傳染的實驗研究表明,資產折價銷售曲線形態取決于流動性沖擊的結構和規模及市場參與人之間的協調,通過改變參與人的預期可以增大參與人之間的協調,從而可以有效阻斷流動性風險的傳染。事實上,本文提出了一個新的政府干預思路:在折價銷售循環開始之處,政府介入資產市場以阻止資產價格的螺旋下降,進而防止基金融資能力的下降,能夠阻斷因折價銷售而引起的風險傳染。正如Shleifer和Vishny[1]指出,當危機發生或折價銷售開始出現時,對政府而言,最簡單有效的做法是通過直接購買折價資產以盡快阻斷折價銷售循環,而不是救助那些績效差且瀕臨倒閉的金融機構。
參考文獻:
[1]?Shleifer, A., Vishny, R. Fire Sales in Finance and Macroeconomics[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11, 25(1): 29-48.
[2]?李曉偉,宗計川. 金融穩定視角下的流動性風險傳染研究新進展[J].經濟學動態,2018,(4):138-147.
[3]?Allen, F., Gale, D. Bubbles and Crises[J]. Economic Journal, 2000, 110(460): 136-255.
[4] 陳冀,陳典發,宋敏.復雜網絡結構下異質性銀行系統穩定性研究[J]. 系統工程學報,2014,(2):171-181.
[5] Brunnermeier, M.K., Pedersen, L.H. Market Liquidity and Funding Liquidity[J].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09, 22(6): 2201-2238.
[6] Pedersen, L.H., Mitchell, M., Pulvino, T. Slow Moving Capital[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7, 97(2): 215-220.
[7] 張家萃,丘曉堅,戴鶴鵬. 我國開放式基金投資者贖回的影響因素[J]. 統計與決策,2006,(4):126-128.
[8] 陸蓉,陳百助,徐龍炳,等. 基金業績與投資者的選擇——中國開放式基金贖回異常現象的研究[J]. 經濟研究,2007,(6):39-50.
[9] 蘇曉萌.經濟學視角下我國開放式基金流動性風險探究[J]. 財稅金融,2016,(30):84-85.
[10] Lakonishok, J., Shleifer, A., Vishny, R.W. 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al Trading on Stock Price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92, 32(1): 23-43.
[11] Wermers, R. Mutual Fund Herding and the Impact on Stock Prices[J].The Journal of Finance, 1999, 54(2): 581-622.
[12] 陶瑜,劉寅,彭龍. 中國證券投資基金羊群行為及其影響因素研究[J]. 北京郵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5):60-67.
[13] Coval, J., Stafford, E. Asset Fire Sales (and Purchases) in Equity Markets[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07, 86(2): 479-512.
[14] Ellul, A. Regulatory Pressure and Fire Sales in the Corporate Bond Market[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1, 101(3): 596-620.
[15] 陳國進,胥愛歡. 我國股票市場是否存在資產被迫拍賣——基于開放式股票型基金的研究[J]. 證券市場導報,2012,(4):34-40.
[16] 陳玉罡,王偉洲. 開放式基金的資產拋售與股票折價套利[J]. 上海金融,2012,(5):77-81.
[17] Larrain, B., Muoz, D., Tessada, J.Asset Fire Sales in Equity Markets: Evidence From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J]. 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2016,30 (6): 1-15.
[18] Heinemann,F. Understanding Financial Crises: The Contribution of Experimental Economics[J].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2, 7(107/108): 7-29.
(責任編輯:鄧 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