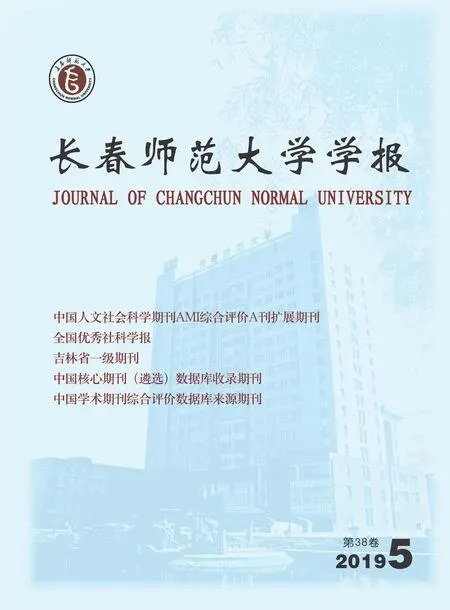出土文獻與《世本》對讀札記兩則
原 昊
(大慶師范學院 文學院,黑龍江 大慶 163712)
《世本》一書是記述世系、氏姓及制作等內容的譜牒之書,該書《作篇》等部分保存了許多先秦舊說。將《世本》與出土文獻進行對讀并從文化學視角加以探析,可證明其文獻的久遠性及可靠性,清晰地感知該書記載的原始性特質以及其中所蘊含的上古文化意蘊。此略舉兩則。
一、說“史皇”
《世本·作篇》載:“史皇作圖。”宋衷注:“史皇,黃帝臣也。圖謂畫物象也。”《作篇》此則記載論及圖畫的起源。宋衷認為史皇是黃帝之臣,便將圖畫的起源追溯至黃帝時期。縱觀新石器時代,陶器的大量制作為繪畫的產生提供了需要,也為繪畫的發展提供了便利,從考古發現中所見陶瓷器皿上新石器時代的繪畫及紋飾中可見一斑。出土于陜西西安的半坡陶盆“人面魚紋盆”是仰韶文化畫作的杰出代表,出土于河南汝州的“鸛魚石斧圖”是廟底溝文化畫作的杰出代表,出土于青海省大通的“舞蹈紋彩陶盆”是馬家窯文化畫作的杰出代表。近年來原始巖畫、地畫的發現,使我國繪畫產生的時間大大前提。
《世本·作篇》中,圖畫的產生歸于史皇。其他傳世文獻也略載史皇之事,如《呂氏春秋·勿躬》:“史皇作圖。”《淮南子·修務訓》:“史皇產而能書。”高誘注:“史皇,蒼頡。生而見鳥跡,知著書,故曰史皇,或曰頡皇。”漢儒高誘在注釋中認為史皇就是倉頡。清華大學所藏戰國竹簡《良臣》記載了黃帝至春秋時期的著名良臣,按照順序進行編排,敘及夏代之時有“史皇”之載:
堯之相焌=(舜,舜)又(有)禹=(禹,禹)又(有)白(伯)(夷),又(有)嗌(益),又(有)史皇,又(有)咎囡(囚)。[1]
《良臣》全篇除了人物名號之外都極其簡略,開篇在敘及女和等黃帝師之后便敘及舜為堯之良臣,禹為舜之良臣,而對禹的良臣提及四位:伯夷、益、史皇和咎囚。這是極其珍貴的出土史料,因為以往傳世的《世本》《呂氏春秋》和《淮南子》等先秦兩漢文獻中提及的史皇均與圖畫的發明相聯系。但除了三國時期宋衷在《世本》注中將史皇歸于黃帝之臣,其他文獻未提及史皇的時代歸屬。清華簡《良臣》則明確將史皇的時代歸屬定為大禹之時,這對文字的發明創制也十分重要。郭永秉先生精辟歸納道:“禹臣有史皇,為我們研究中國文字的創制起源時代,提供了一條東周人觀念中的可貴史料……似從來沒有見到將‘倉頡’或‘史皇’至于夏代始祖禹麾下為臣的說法,《良臣》此條材料的重要性、特異性可見……至少反映出春秋戰國時代一部分人心目中,文字的創制時代大概在夏初。”[2]
對于史皇為臣,《呂氏春秋·勿躬》在講述圣王不用事必躬親,使臣子各盡其才、各司其職便可治天下這一道理的時候,列舉了二十則例證,其中一則即為“史皇作圖”。《淮南子·修務訓》提及史皇,因其生來能書。《淮南子》雖為漢代之書,但此則記載對“產”字的應用,顯系從古書中沿襲下來的先秦舊說[2]。雖然史皇與倉頡是否為一人無法確考,但可知最遲戰國秦漢時期便流傳史皇發明圖文之說。而根據《世本·作篇》另載“倉頡作書。蒼頡造文字。沮誦蒼頡作書”,可以推知倉頡與史皇應非一人。《作篇》將發明創制之功常歸功于一人,顯然并非客觀事實,但如此做法一定有其緣由,即某一人物在某方面的獨特造詣。正如《荀子·解蔽篇》所言:“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好稼者眾矣,而后稷獨傳者,壹也。好樂者眾矣,而夔獨傳者,壹也;好義者眾矣,而舜獨傳者,壹也。”將文字創制之功歸于倉頡,將圖畫創制之功歸于史皇,其締造思維是一致的。至于《世本·作篇》宋衷注文中所言史皇為黃帝臣子,這種觀念或形成于戰國后期,而此時也是《世本·作篇》《大戴禮·帝系》等篇所主要表現的黃帝大一統世系形成的關鍵時期。大到帝系傳承的共同源頭,小到制度器物的發明創造,都被依附于黃帝,這種依附源于文化認同的追溯與記憶附加的需要。根據《良臣》之載,戰國早期及中期,史皇被視為禹的臣子。至戰國晚期,伴隨著黃帝大一統思潮的席卷,史皇或被視為黃帝的臣子,與沮誦、蒼頡同階。至漢代,史皇其人其事并不昭著,故而逐漸被淡忘。甚至基于文字與圖畫關系極為緊密,無需強行分開并細致區分,出現以史皇與倉頡為一人的說法。史皇并非大禹諸多臣子中的重要史官,但也在戰國末期的造神運動中被依附于黃帝麾下,成為黃帝臣子,其所處時代也隨之前移。
此外,《良臣》載禹臣益,也是極為重要的記載。關于益,《世本·作篇》載:“化益作井。”宋衷曰:“化益,伯益也,堯臣。”《呂氏春秋·勿躬》載:“伯益作井。”《淮南子·本經訓》載:“伯益作井。”高誘注:“伯益佐舜,初作井,鑿地而求水。”伯益最突出的貢獻就是佐禹平治水土,這點見于《史記·夏本紀》及《秦本紀》。除了伯益之外,文獻所見禹臣大約有后稷、契、伯益、伯夷、史皇、咎囚、皋陶、直成、橫革及之交:
(1)后稷。《史記·夏本紀》:“禹乃遂與益、后稷奉帝命……命后稷”。上博簡《容成氏》:“后稷既已受命,乃食于野。”(2)契。《史記·殷本紀》:“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3)伯益。《尚書·堯典》:“益曰……禹曰”。《史記·夏本紀》:“而后舉益,任之政。”《孟子·萬章上》:“益之相禹也。”《列女傳》:“陶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注:“陶子者,皋陶之子伯益也。”(按:此處伯益為皋陶子,誤。)清華簡《良臣》:“禹……有嗌(益)。”(4)伯夷。《國語·鄭語》:“伯夷能禮于神以佐堯者也。”清華簡《良臣》:“禹有伯(夷)。”(5)史皇。清華簡《良臣》:“禹……有史皇。”(6)咎囚。清華簡《良臣》:“禹……有咎囡(囚)。”(7)皋陶。《史記·夏本紀》:“帝禹立而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上博簡《容成氏》:“咎(皋)(陶)既已受命。”(8)直成。《荀子·成相》:“禹……得益、皋陶、橫革、直成為輔。”《呂氏春秋·求人》:“得陶、化益、真窺、橫革、之交五人佐禹。”盧文弨謂真窺即直成也,《呂氏春秋》傳寫誤作“真窺”。《呂氏春秋·尊師》:“禹師大成贄。”陳奇猷謂大成贄即直成。(9)橫革。《呂氏春秋·求人》:“得陶、化益、真窺、橫革、之交五人佐禹。”《荀子·成相》:“禹……得益、皋陶、橫革、直成為輔。”(10)之交。《呂氏春秋·求人》:“得陶、化益、真窺、橫革、之交五人佐禹。”
另外,楊棟、劉書惠先生經過考證提出《良臣》帶有部分“世系”性質,與《呂氏春秋·尊師》所記人物在“世系”上多有相合,而對賢臣記載更為詳盡[3],這是非常精當的結論。
二、說“獻侯蘇”
《世本·諸侯世本》載:“(晉)獻侯蘇。”《史記·晉世家》載:“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釐侯十四年,周宣王初立。十八年,釐侯卒,子獻侯籍立。獻侯十一年卒,子穆侯費王立。”出土于山西曲沃北趙村晉侯墓地的晉侯蘇編鐘銘文中多次出現關于“晉侯蘇”“晉侯”及“蘇”的記載:

晉侯蘇編鐘銘文與《世本》記載一致。通過這則出土文獻的印證,足見《世本》史料之珍貴。唐司馬貞在《史記·晉世家》索隱中指出晉獻侯之名,《史記》所作“籍”,而“《世本》及譙周皆作‘蘇’。”后世章宗源等輯佚家據此,在《龍溪精舍叢書本》中對譙周《古史考》輯本中輯入“《晉世家》武侯‘寧族’作‘曼旗’,獻侯作‘蘇’”之句。至于“籍”與“蘇”,有學者提出二字相通,如高亨先生《古字通假會典》“蘇與籍”條:“《史記·惠景間諸侯年表》:‘江陽,康侯蘇嘉。’《集解》引徐廣曰:‘蘇一作籍’。《史記·晉世家》:‘子獻侯籍立。’《索隱》:‘《世本》及譙周皆作蘇’。”張華等先生認為,晉侯蘇即《世本》所記獻侯蘇,“蘇、籍二字古音相近,籍可能是蘇字之誤”[5]。雖然依據現有文獻無法明確斷定“籍”與“蘇”二字是否相通,也無法確考《史記·晉世家》中晉獻侯名籍這一說法是否為太史公誤記,但從與晉侯蘇編鐘銘文與《世本》的印證,至少可以肯定晉獻侯名蘇。這為傳世文獻記載的證真及鐘鼎銘文內容的考訂提供了堅實基礎。
在天馬——曲村遺址東部發現的晉侯墓地發現晉侯及其夫人的墓葬,按照時代依次排列,連接緊密,當為依世系繼承的八代晉侯。出土銅器銘文已經發現六位晉侯的名字,根據各組墓的先后順序,結合《史記·晉世家》所載晉侯世系,可以確定八組墓的墓主為父子相承的八代晉侯,即:武侯、成侯、厲侯、靖侯、釐侯、獻侯、穆侯和文侯。由于是后世輯本,所以無從得見《世本》記述晉國世系的全貌。從現有輯本看,涉及從武侯到靜公的16代晉君,具體為武侯、厲侯、獻侯、穆侯、鄂侯、武公、定公、出公、昭公、雍、忌、驕、幽公、烈成公、孝公、靜公。上述晉君記載中,《世本》與《史記》載錄12代晉君名號:
(1)武侯之名,《世本》作“曼期”,《史記》作“寧族”。(2)厲侯之名,《世本》作“輻”,《史記》作“福”。(3)獻侯之名,《世本》作“蘇”,《史記》作“籍”。(4)穆侯之名,《世本》作“弗生”,《史記》作“費王”。(5)鄂侯之名,《世本》《史記》俱作“郄”。(6)武公,《世本》稱武公為“莊伯子”,《史記》稱武公名“稱”。(7)定公之名,《世本》《史記》俱作“午”。(8)出公之名,《世本》《史記》俱作“鑿”。(9)幽公之名,《世本》無載,《史記》作“柳”。(10)烈成公之名,《世本》《史記》俱作“止”。(11)孝公之名,《世本》作“傾欣”,《史記》作“頎”。(12)靜公之名,《世本》作“俱”,《史記》作“俱酒”。
三、結語
《世本》之中的“史皇”之載,應是春秋至戰國早期關于圖畫形成于大禹時期這一觀念的記錄。從圖畫及文字源起角度而言,該記載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發明創造歷史的久遠,但我們也應正確認識其作為史影而承載社會觀念的價值所在。《世本》中“晉侯蘇”之載得到晉侯蘇編鐘銘文的印證,足見主體史料編纂于戰國時期的《世本》一書的珍貴,特別是該書史料中所存留的先秦舊說應引起足夠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