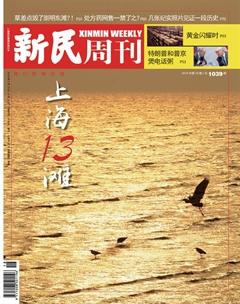好劇無法擁有第二季
最近很迷道格拉斯·亞當斯這位作者,就是那個寫《銀河系搭車客指南》的英國人。科幻外殼包裹之下,本本都是英國腔滿溢的諷刺小說,比如《全能偵探社》用淡筆如此描繪一位路人甲:“他的冷酷表情庫存豐富,從最底下確實非常陰沉的冷酷開始,一路向上可以數到疲憊而聽天由命、僅剩一絲的冷酷,那是為他兒女生日準備的。”英國人好像天然擅長三翻四抖,一通婉轉曲折之后才跌宕出一個脆生的包袱。
《倫敦生活》(Fleabag)第一季就是如此婉曲,觀眾要看到結尾才突然醒悟,真的被女主觸動感情。之前種種不過是同病相憐,茨威格所謂“心靈的焦灼”——畢竟誰沒經過原生家庭的苦楚,誰沒有奇葩詭異的親人家長,誰沒掉過鮮花插糞的情感大坑。在鋪平墊穩方面,英國文藝界真是舍得下本兒。然而這也導致第二季文章難作。
當初聽說本劇還有第二季非常吃驚,以至于頭一個蹦出來的想法是因為演員之一,奧利維婭·科爾曼,加冕本屆奧斯卡最佳女主角。《倫敦生活》里繼母這個角色確實讓她演繹得熠耀生輝,活脫是張愛玲所說那種“晚娘臉”,溫馴親切里藏著絲縷崢嶸的殺心。可是第一季已經把話說盡,第二季就難以向更深處走,原本閃光的人物就有流于跳梁小丑的風險。女主角的情形也是一樣,第一季結尾已經跌到人生谷底,第二季難道要開講“發現無論現在情況有多糟,都還有可能變得更糟時才會有的冷靜”?
我愛你。但是我好像沒辦法一直喜歡你。
人物難以成長是很多劇集的限制。成長的意思不是社會意義的成熟,而是人物性格的豐滿和深入。《倫敦生活》第二季的走向是和解,然而溫情注定會削減女主古靈精怪的個性,也就導致人物崩塌,無法為繼。當她理解了自己的姐姐和父親,再從他們那里受到傷害就顯得矯情。“我愛你。但是我好像沒辦法一直喜歡你。”話說得通透,但安排在故事結尾倉促說出,還是一種偷懶。
作為本季強行塞入的男主,安德魯·斯科特(更為人知的名字是由飾演《神探夏洛克》之莫里亞蒂而得的“莫娘”)無功無過。愛他是因為他好看,這個理由強大到無可爭辯,觀眾也樂于吞下這種設定。然而這場感情戲自始至終讓人感到相當隔膜,甚至體會不到第一季里女主因為對前男友求之不得,由卑微而生出的各種痛癢。她在這場感情里所受的傷,怎么看也不過是愛他而最終沒有得到回應;那就不得不承認,男主在結尾的臺詞“It'll pass”,盡管戳痛,卻是兩人之間的真實寫照。為愛刀山油鍋,是青年人灑的熱血,美國式的熱烈;英國故事對浪漫感傷的嘲戲往往不遺余力:人世輕薄,我愛你固然動情,實在也不是多了不起的事。“生的門答”的情緒,要其他情節的有力支撐,說服力才能得到認可。不然就像我的靈魂之書《愛麗絲漫游奇境》里,面對公爵夫人的無端感慨:“是愛,愛是讓世界運轉的力量!”愛麗絲一個小姑娘也會理智作答:“也有人說是靠每個人管好自己的事情。”

張愛玲(不好意思,一看英國人就老想起張愛玲)講過她的一個夢,女校的修女對她態度奇差,令她很是委屈。醒來一想,自己也奇怪怎么把周圍的人夢得那樣惡毒,“他們何至于要那樣待我”。人物的原地踏步就會令觀眾有同樣的疑惑,第一季還有心想想女主哭花妝時的美麗口紅是什么色號,到了第二季,只忍不住奇怪為什么每個人跟女主相處時都神經兮兮、刻薄無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