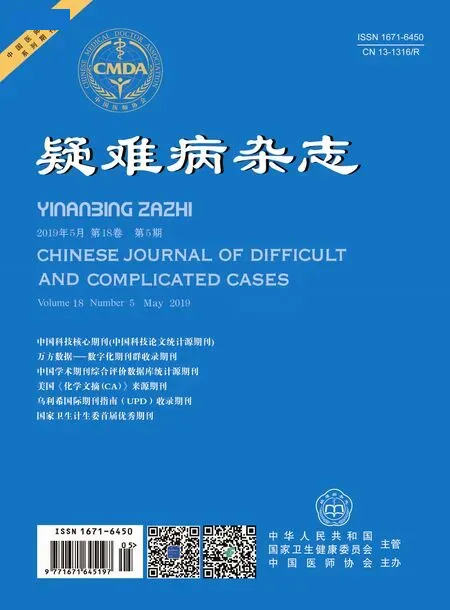超聲引導下微通道經皮腎鏡取石術治療腎結石的療效及對機體應激反應的影響
楊小杰,李友芳,王茜,張棟,雒啟東,張鵬
近年來,隨著人們飲食結構的改變,腎結石的發病率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多以劇烈腰痛并伴有不同程度的血尿為臨床表現[1]。據統計,我國是腎結石的高發國家,發病率在5%左右,同時每年以25/萬人的比例發病,而其中大約有25%的患者需要進行臨床治療,如治療不及時,可能引發腎積水,嚴重者并發尿毒癥,危及患者生命[2]。既往臨床上多采用開放手術取石、體外沖擊波碎石以及藥物保守治療等方法進行治療,效果欠佳[3]。隨著各種內鏡技術以及微通道技術的發展,經皮腎鏡取石術(percutaneous nephrolithotomy,PCNL)具有創傷小、結石清除率高以及術中出血量少等優點,其被臨床廣泛應用[4]。PCNL通常又可被分為標準通道經皮腎鏡碎石術(sPCNL)和微通道經皮腎鏡碎石術(mPCNL)2種,PCNL手術成功的關鍵是經皮腎穿刺通道的建立,由于X射線輻射大、并發癥多等缺點,臨床反饋較差[5],故采用超聲進行穿刺引導。目前臨床研究大都集中于2種術式的臨床效果,但是隨著臨床上對患者術后生活質量要求的提高,手術本身對機體產生的應激影響也逐漸引起了重視[6]。sPCNL和mPCNL均為微創手術方式,其對機體的應激反應以及刺激程度是否一致有待研究[7-8]。故本研究探討超聲引導下經皮腎鏡取石術治療腎結石的療效及對機體應激反應的影響,為腎結石的臨床治療提供參考,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選擇2016年1月—2018年7月西安交通大學第二附屬醫院泌尿外科收治的腎結石患者150例作為研究對象,按照隨機數字表法分為對照組和觀察組,各75例,其中對照組患者給予sPCNL治療,觀察組患者給予mPCNL治療。2組患者在性別、年齡、BMI、結石直徑以及結石類型等一般資料方面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見表1。本研究經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核通過,患者及家屬同意并簽署知情協議書。
1.2 選擇標準 納入標準:(1)ASA分級Ⅰ~Ⅱ級者;(2)經泌尿系統彩色超聲以及腹部CT等檢查證實為多發或者單發腎結石者。排除標準:(1)合并有呼吸系統或者循環系統障礙者;(2)合并有惡性腫瘤、甲亢、糖尿病以及心臟病者;(3)存在免疫治療以及輸血史者;(4)合并腎功能不全以及其他腎臟疾病者;(5)尿路解剖結構畸形;(6)合并精神系統疾病者;(7)手術藥物過敏者;(8)依從性差,中途退出者。
1.3 手術方法 所有患者取截石位,給予硬膜外阻滯麻醉,經尿道將輸尿管鏡植入膀胱,在德國KARL STOR 11278A1軟性輸尿管鏡下找到輸尿管口,將輸尿管導管逆行插入到腎盂中,植入尿管并給予固定。在醫護人員的幫助下,患者取俯臥位,墊高腹部,將人工腎積水慢慢經導管推入,根據患者腎積水情況以及結石部位,選擇穿刺點,通常是選擇腋后線和肩胛下線、第12肋下和第11肋間之間的區域,穿刺腎盞并在B型超聲的輔助下,將穿刺針刺入結石所在的腎盞,穿刺部位正確的判別方法為有尿液從穿刺針中流出。完成穿刺后,沿著穿刺針置入斑馬導絲將皮膚切開9 mm左右。再通過筋膜擴張器進行擴張。對照組患者擴張器由8 F擴張至24 F;觀察組患者擴張器由8 F擴張至18 F。留置塑料薄鞘建立通道,采用30W鈦激光系統(意大利quanta Litho)擊碎腎結石,碎石通過灌注泵灌注的生理鹽水進行清理。最后通過超聲對患者的耐受以及結石清除情況進行觀察并記錄。術后常規止血、引流管留置以及創口閉合。
1.4 觀察指標與方法 (1)手術相關情況:觀察記錄2組患者術中出血量、手術時間、下床活動時間、住院時間,并采用超聲系統對結石清除率進行測定。(2)尿液腎損傷分子1(KIM-1)水平測定[9]:術前將尿管置入,通過輸尿管于術前1 d、術后1 d收集患者尿液,3 000 r/min,離心15 min,取上清液,采用酶聯免疫吸附法進行測定,試劑盒購自上海康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操作方法嚴格按照說明書執行。(3)腎功能及氧化應激指標水平測定:于術前1 d、術后1 d抽取所有患者清晨空腹靜脈血5 ml,3 000 r/min,離心14 min,取上清-70℃條件下備存待測。采用酶聯免疫吸附法對血清皮質醇(Cor)、腎上腺素(AD)、去甲腎上腺素(NE)以及丙二醛(MDA)、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谷胱甘肽過氧化酶(GSH-Px)水平進行測定,試劑盒購自上海語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操作方法嚴格按照說明書執行。

表1 2組患者基線資料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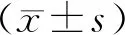
2 結 果
2.1 2組患者手術相關情況比較 觀察組患者術中出血量明顯低于對照組,手術時間長于對照組,結石清除率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均<0.01);2組患者下床活動時間及住院時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2.2 2組患者手術前后尿液KIM-1與腎功能指標變化比較 與治療前相比,2組患者手術后尿液KIM-1以及血清Cor、AD、NE水平均明顯升高(P均<0.01);觀察組患者手術后尿液KIM-1升高高于對照組,血清Cor、AD、NE水平升高低于對照組(P均<0.01),見表3。
2.3 2組患者手術前后氧化應激指標水平變化比較 與手術前相比,2組患者手術后血清GSH-Px、SOD水平明顯降低,MDA水平明顯升高(P均<0.01),且觀察組患者上述指標改善優于對照組(P均<0.01),見表4。
2.4 2組患者術后并發癥和復發率情況比較 對照組患者術后發生腎出血1例、敗血癥2例,觀察組患者發生敗血癥2例,經過相應保守治療均痊愈;對照組術后復發率12.00%(9/75), 觀察組術后復發率9.33%(7/75)。2組患者并發癥發生情況及復發率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

表2 2組患者手術相關情況比較

表3 2組患者治療前后尿液KIM-1與血清腎功能指標變化比較

表4 2組患者手術前后氧化應激指標變化比較
3 討 論
PCNL經歷了多個發展階段,從最初的傳統型PCNL(24~34 F超寬取石通道)逐步向標準型PCNL(sPCNL,取石通道為24~26 F)發展[10]。曾國華等[11]在國內首次報道了名為“超微經皮腎取石術(mPCNL)”的微創技術,其主要用于治療軟鏡、標準PCNL術后殘留結石以及兒童腎結石治療失敗的腎結石患者。Haider等[12]首次報道了通過超細通道(13 F)的經皮腎鏡對2 cm以下的腎結石進行治療,開創了腎結石微創治療的新領域。隨著人們對微創技術認識的不斷加深,更為狹窄的取石通道PCNL技術逐漸被廣大患者接受[13]。研究顯示,PCNL取石通道的狹窄不僅與手術操作便捷情況、術中出血以及手術時長關系密切,還與腎功能、機體應激反應以及并發癥發生情況息息相關[14]。
本研究結果顯示觀察組結石清除率明顯高于對照組,其可能與觀察組患者使用更細的輸尿管鏡有關,由于其通道相對較窄,術中使用更細的輸尿管鏡,可以更大幅度地完成相應擺動,并順利到達腎結石所在的目標腎盞,清除結石效果更佳[15]。另外,由于均為微創手術,患者術后住院時間差異不顯著,而觀察組患者實施的mPCNL手術通道較為狹窄,操作難度增加,同時完成碎石以后可能還需要手動進行取石,手術持續的時間相對長于通道較寬的對照組患者[16]。由于mPCNL手術過程中通道較窄,擴張器對筋膜的擴張強度較輕,可以降低出血等并發癥的發生風險,但是由于其具有較慢的循環灌注速度,在處理結石較大的患者時,手術時長會相對增加[17]。本研究中2組患者術后均出現了敗血癥,為預防敗血癥的發生,需要注意以下情況[18]:(1)術后監測患者血壓,血壓平穩時,應給予利尿藥物呋塞米,加速排出體內菌尿;(2)不過分追求對于腎結石的碎石粉末化,降低結石內毒素和細菌的釋放;(3)手術過程中盡量減少灌洗液的壓力,可對腎內壓力有效降低,減少毒素和細菌的吸收[19]。本研究還對機體應激反應以及腎功能損傷方面進行了研究,KIM-1是一種在健康機體內很少表達的跨膜糖蛋白,最早于腎損傷的大鼠體內發現[20]。當人體腎功能發生損傷時,其腎小管上皮細胞中會大量表達KIM-1,且尿中表達程度與腎損傷關系密切,可作為早期腎損傷的標志性因子[21]。本研究結果提示,觀察組患者腎功能損傷相對較重,這可能是由于mPCNL手術取石通道較為狹窄,灌洗液流經時阻力相對較高,而碎石后通常需要采用經過加壓的灌注液沖洗取石通道[22];另外,手術過程中為保持清晰視野,也需要沖洗通道,具有較高的灌注壓,因此觀察組患者腎功能損傷更為嚴重[23]。尿液KIM-1水平變化與趙淮平等[24]研究相一致。結果中對照組患者應激反應更為劇烈,這可能是由sPCNL取石通道較寬,對周圍的腎血管產生較大的損傷造成的,術中出血量也相對高于mPCNL治療的觀察組,患者機體應激水平相對較高[25]。
綜上所述,mPCNL治療腎結石患者,具有較高的結石清除率,且可以明顯降低機體的應激反應,而sPCNL手術對腎功能損傷較小,臨床醫師可根據患者病情選擇更為適合的治療方案。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聲明
楊小杰:整理資料,分析資料,論文撰寫;張鵬:提出研究思路,修改總指導;李友芳、張棟:收集整理資料,分析數據,圖表設計;雒啟東:收集整理資料,查找參考資料;王茜:收集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