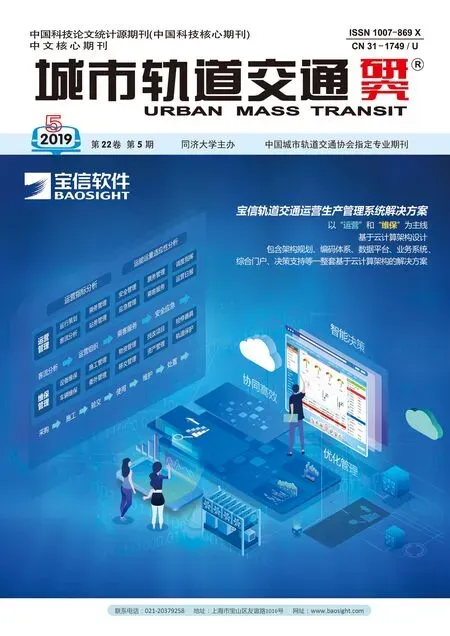淤泥質土及粉細砂地層盾構施工地表沉降監測分析
王呼佳 鄒 育 劉川昆 李 策 伍偉林
(1.中鐵二院工程集團有限責任公司,610031,成都;2.西南交通大學交通隧道工程教育部重點實驗室,610031, 成都//第一作者,高級工程師)
地鐵隧道施工多采用盾構法。淤泥質土及粉細砂層是盾構隧道施工常見的不良地層,是引起地表沉降的關鍵因素。為此,分析地層沉降原因,總結地層沉降規律,變得尤為重要和迫切。
文獻[1]對淺埋三車道大跨度隧道施工引起的地表沉降變形特征進行現場監測,探討淺埋大跨度隧道的開挖方式,分析采用三臺階七步平行線流水開挖引起的隧道地表沉降變形特征;文獻[2]通過對地表沉降和深部土體水平位移的實測和分析,得出富水砂卵石地層盾構隧道施工引起地層變形的基本規律;文獻[3]通過理論預測計算得到的沉降值與西安地鐵某區間隧道的地表沉降實測數據進行了對比分析;文獻[4]以成都砂卵石地層中地鐵1 號線的土壓平衡式盾構掘進施工為研究背景,采用室內試驗及數值模擬的方法,揭示了土壓平衡式盾構穿越砂卵石地層的失穩機制和沉降規律,并結合實際施工參數和實測地表沉降數據進行了對比分析;文獻[5]分析了城市淺埋隧道開挖引起地表沉降的主要影響因素,并建立了基于遺傳算法的神經網絡淺埋隧道開挖地表沉降預測模型。
以上研究主要從理論分析及數值模擬對盾構掘進引起的地表沉降進行分析,而對淤泥質土及粉細砂層地表沉降采用現場實測的分析方法甚少。為此,本文依托佛山地鐵2號線工程,根據現場監測數據,對盾構掘進在淤泥質土和粉細砂層中造成的地表橫斷面沉降和縱斷面變形進行分析。
1 工程概況
1.1 工程概述
花卉世界站—仙涌站區間線路出花卉世界站后,沿佛陳公路向東北方向前行,先下穿文登河,然后依次下穿2座文登河公路箱涵。區間隧道采用土壓平衡式盾構,左線隧道先施工,右線隧道后施工。隧道內徑5.4 m,管片厚度300 mm,平面最小曲線半徑為600 m,左、右線線間距12.0~14.4 m。區間縱斷面為V型坡,最大縱坡24‰,豎曲線半徑為5 000 m,隧道拱頂埋深為6.0~20.5 m。
擬建區間附近地表水主要為線路北側的文登河,寬約14.7 m,水深約4.4 m,常年有水,水流緩慢,水量豐富。
1.2 地質條件
區間斷面地層從上至下依次為:素填土、粉質黏土、淤泥質土、淤泥質粉細砂、中粗砂、全風化砂質泥巖、強風化砂質泥巖。區間盾構主要穿越淤泥質土及粉細砂地層,其典型斷面地質條件如圖1~2所示。

a) 斷面1

b) 斷面2

c) 斷面3

d) 斷面4

a) 斷面5

b) 斷面6

c) 斷面7

d) 斷面8
2 施工監測方案
監測點縱向沿隧道中軸線間隔布置,橫向以左、右隧道中軸線為中心等間距布置。主要對淤泥質土和粉細砂層8個典型斷面(見圖1~2)進行分析。各典型斷面概況見表1。淤泥質土和粉細砂層典型斷面的線間距分別為14.4 m及12.0 m,監測點的布置分別如圖3和圖4所示。

表1 各典型斷面概況
3 淤泥質土層沉降監測分析
以斷面3監測數據為代表,對淤泥質土層橫斷面沉降槽進行分析。
3.1 單線掘進橫斷面沉降槽分析
盾構刀盤位于監測斷面3后方3環時,地表產生微隆起,最大變形量為1.2 mm,如圖5所示。當刀盤位于監測斷面3前方10環時,盾構通過監測斷面,管片脫出盾構機,地表變形量迅速增加,地表最大沉降值為5.2 mm;隨著盾構繼續推進,由于淤泥質土受前期盾構施工的擾動,后期固結沉降量大,持續時間長,地表沉降持續增大,最大沉降值達到5.2 mm。在淤泥質土層中,單線隧道施工引起的地表橫向沉降曲線近似為V型分布,最大沉降發生在線路中線。隧道掘進引起的橫向地表沉降主要分布在隧道中線兩側1.5D范圍(D為隧道直徑),距中線2.0D以外區域幾乎不受影響。

圖3 淤泥質土層典型斷面的監測點布置方案

圖4 粉細砂層典型斷面的監測點布置方案

圖5 淤泥質土層單線掘進橫斷面地表沉降實測曲線
3.2 雙線掘進橫斷面沉降槽分析
單線盾構掘進時,地表橫向沉降主要分布在距各自隧道中線1.5D范圍內,當隧道線間距為2.3D時,左右線隧道主要影響區相交,理論上最終的沉降曲線仍為V字型,且沿中軸線對稱分布;而實際地表累計沉降曲線對稱軸偏向左線隧道(先行隧道),如圖6所示。左線隧道(先行隧道)地表累計沉降大于右線隧道(后行隧道),最大沉降量分別為5.6 mm和7.2 mm。主要原因是成型隧道通過在管片壁后進行同步注漿和二次注漿,改善了隧道周圍的土體,減少了土體的孔隙率和含水率,整體上提高了土體的強度和穩定性,使得后行隧道對先行隧道的影響小于先行隧道對后行隧道的影響。

圖6 淤泥質土層雙線掘進橫斷面地表沉降實測曲線
3.3 變形過程分析
地表沉降除與地層有關,盾構姿態、土倉壓力、掘進速度、同步注漿和二次注漿等盾構施工參數也起著控制性作用。對于不同的斷面,由于盾構參數的差異,地表沉降會有所不同,但沉降曲線趨勢基本一致。根據刀盤與測點的位置可將地表沉降劃分為先行沉降、開挖面沉降和隆起、盾尾沉降、盾尾空隙沉降、后續沉降等5個階段[6]。
盾構刀盤在淤泥質土層中,土倉內壓力容易控制,施工過程中一般控制土倉內壓力稍大于掌子面土體壓力,盾構前方土體受到一定擠壓,使得開挖面前方地層有少量隆起,如圖7所示。盾構機通過階段,地層逐步退出土倉壓力擠壓影響范圍, 同時由于盾構姿態調整、管片拼裝時的千斤頂回縮以及盾殼與地層間摩阻力引起的“背土”等原因, 地層會發生較小的沉降。由于淤泥質土靈敏度高、含水量大,管片脫出盾構機盾尾后,受擾動地層固結、漿液凝固、孔隙水壓力消散等引起位于該區域內的斷面地層損失率總體呈線性增大,表現為地表沉降逐漸增加,所產生的地層沉降占施工導致的地層沉降的絕大部分。同時因盾構施工擾動的淤泥質土固結時間長,后續地表沉降會持續增大。

圖7 淤泥質土層左線縱向地表沉降時程曲線
4 粉細砂地層沉降監測分析
以斷面5監測數據為代表,對粉細砂層橫斷面沉降槽進行分析。
4.1 單線掘進橫向沉降槽分析
盾構刀盤位于監測斷面5后方11環到后方7環時,所有監測點幾乎沒有變化,表明盾構掘進還未對監測斷面產生擾動;盾構刀盤位于監測斷面5后方3~4環時,由于掘削面土體因土艙壓力不足而向盾構內移動時,盾構前方土體將發生向下和向后的移動,造成地表產生沉降,最大沉降為5.0 mm;當刀盤位于監測斷面5前方3環時,左線隧道上方發生明顯的地表沉降,最大沉降量達到10.5 mm;當盾構管片環脫離盾尾時,盾構殼體與管片之間存在空隙,而同步注漿施工和漿液硬化存在的滯后性,建筑空隙不能及時被填充,同時粉細砂自穩性差,從而引起地層突然產生較大的沉降,最大沉降量達到21.7 mm。隨著漿液的硬化,盾構施工對監測斷面的影響越來越小,而粉細砂層后期沉降量又較小,最終地表沉降保持穩定。
在粉細砂地層,單線施工引起的地表沉降曲線形態近似為V型分布曲線,最大沉降發生在線路中線。隧道掘進引起的橫向地表沉降主要分布在隧道中線兩側1.0D范圍,距中線1.5D以外區域幾乎不受影響,如圖8所示。

圖8 粉細砂地層單線掘進橫斷面地表沉降實測曲線
4.2 雙線掘進橫向沉降槽分析
單線盾構掘進時,地表橫向沉降主要分布在距各自隧道中線1.0D范圍內,當隧道線間距為2D時,左、右線隧道主要影響區不相交,疊加的沉降曲線呈W型分布,雙線最大地表沉降量較單線最大地表沉降量變化不大,如圖9所示。左、右線地表最大沉降發生在各自中線偏內側(左、右線隧道間為內側),隧道間的地表沉降大于隧道外側地表沉降,且左線隧道(先行隧道)地表沉降大于右線隧道(后行隧道)地表沉降,最大沉降累計量分別為25.3 mm和23.4 mm。

圖9 粉細砂地層雙線掘進橫斷面地表沉降實測曲線
4.3 變形過程分析
由于粉細砂沒有黏聚力,土倉、螺機內渣土的和易性差,流速不穩定,容易引起掌子面土壓力波動劇烈,從而導致同一地層不同斷面先行沉降,與開挖面沉降差異很大,如圖10所示。粉細砂自穩性極差,無法形成坍落拱,在刀盤與盾殼、盾殼與管片之間的空隙中土體失去支撐,容易發生較大變形,故在粉細砂地層中,地表沉降主要發生在盾構開挖和盾尾脫出盾構機階段。

圖10 粉細砂地層左線縱向地表沉降時程曲線
5 不同斷面地表沉降對比分析
5.1 淤泥質土層沉降槽對比
通過Peck公式對地表沉降進行擬合,如圖11所示。除了斷面2外,其他3個斷面的擬合結果都比較好,表明Peck公式擬合淤泥質土層地表沉降與現場測試實際值偏差不大。由表2的統計數據可知,在淤泥質土層中,盾構埋深越深,最大地表沉降量越小,且沉降槽寬度越小。這是因為盾構埋深越淺,地表離盾構越近,地表土體受到的擾動就越大,因而造成的地層損失、沉降和隨后的固結沉降也越大,沉降槽也越大。
5.2 粉細砂地層沉降槽對比
通過Peck公式對地表沉降進行擬合,如圖12所示,除了斷面7外,其他3個斷面的擬合結果都比較好,表明Peck公式擬合粉細砂地層地表沉降與現場測試實際值偏差不大。由于粉細砂層無黏聚力,下層土體的坍塌會引起上層粉細砂的失穩,故盾構埋深越深,最大地表沉降量越小,而沉降槽寬度越大,如表3所示。

a) 斷面1

b) 斷面2

c) 斷面3

d) 斷面4

表2 淤泥質土地層監測斷面擬合結果
6 結論
(1) 在淤泥質土和粉細砂地層中,后行隧道對先行隧道的影響小于先行隧道對后行隧道,施工中可以對靠近重要建筑物的隧道先施工。

表3 粉細砂土層監測斷面擬合結果
(2) 在同一埋深條件下,盾構施工對粉細砂地層的影響大于對淤泥質土層的影響。
(3) 對于淤泥質土層,盾構埋深越深,最大地表沉降量越小,沉降槽寬度越小;而對于粉細砂地層,盾構埋深越深,最大地表沉降量越小,而沉降槽寬度越大。
(4) 在淤泥質土層中,地表沉降主要發生在管片脫出盾尾和后期的固結沉降階段;在粉細砂地層中,地表沉降主要發生在盾構掘進和管片脫出盾尾階段。

a) 斷面5

b) 斷面6

c) 斷面7

d) 斷面8
圖12 粉細砂地層各監測斷面沉降槽對比
(5) 當線間距大于2倍盾構主要影響范圍,最終的沉降槽成W型;當線間距小于2倍盾構主要影響范圍,最終的沉降槽成V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