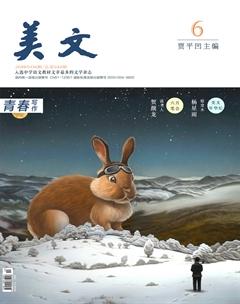王荊公的教育理念
陳楠
王安石那一句“春風又綠江南岸”讓無數人為之嘆服,一個“綠”字,讓春意從江邊蔓延到人們眼前,讓嫩綠的春在緩緩的風中一點點浸潤。這句詩可能是我們最開始對王安石的了解吧!再繼續了解,就知道了他做過宰相,搞過變法。其實王安石很忙的,他在很多方面、很多領域都有不小的成就,文學方面成就尤其大。
如果僅僅從文學角度去看待王安石的作品并給出一個評價的話,不往遠說,他位列唐宋八大家,就在唐宋比吧,或者就在宋代比一下看看,北宋有蘇軾,南宋有陸游,雖然王安石的詩、文、詞都不錯,但他拔不了尖。因為他是一個嚴肅認真的人,嚴肅認真到無趣,他的人生信條是“實用”。曾有一則軼事,說王安石同僚的夫人對王安石夫人說,我家大人看到您家大人喜歡吃鹿肉,王安石夫人微笑不語,待到下次宴請,她安排仆傭調整菜肴擺放位置,王安石就不吃鹿肉了,原來他只吃自己面前的一盤菜。
唐代古文運動取得了巨大成就,可是經歷了五代十國的浮糜一片后,宋初的文風也沉浸在秀精巧與炫學問之中,歐陽修倡導并帶頭實踐的宋代詩文革新運動中,王安石是有利的支撐與推動。但是,由于他個人性格的限制,王安石的文學主張過于強調“實用”,往往忽視了藝術形式的積極作用。
在我的印象中,王安石一直是個古板大叔,但這個古板大叔也可愛極了,他愛思考,也喜歡著述。王安石有兩首《明妃曲》被廣為贊譽,其一寫道“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其二寫道“漢恩自淺胡恩深”,他對歷史與人的雙重角度思考,思考昭君的悲劇,不僅來自于“計拙”的和親,更來自于一個女子在歷史風浪中漂泊的故事,是對一個被侮辱被損害的形象的解讀。王安石還寫過一本《字說》,他認為漢字以音、形包含著萬事萬物之理,這本書現今已亡逸,片段有存于其余書中。此書內容多為穿鑿附會,例如解釋“波”為“水之皮”,蘇東坡聽聞道:“滑者,豈非水之骨乎?”再錄一則趣聞。徐健《漫笑錄》載,東坡聞荊公《字說》新成,戲曰:“以竹鞭馬為‘篤,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又曰:“鳩字以‘九從鳥,亦有證據。《詩》曰:‘鸤鳩在桑,其子七兮;和爹和娘,恰是九個。”雖是善意調笑,但可以看出知識分子們對這個一根筋學者的嘲諷,但王安石在位期間,這本書還是頗受追捧的,嘲諷也擋不住它的瘋狂傳播,可隨著新政失敗,書被廢禁,再無傳世版本。
這樣的性格和他摒除浮糜文風的態度,導致他的不少詩文常常表現得議論與說理過重,瘦硬而缺少韻味,但總體上不失大家風范。王安石還是個政治家,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他把文學創作和政治活動密切地聯系起來,始終強調文學的作用首先在于為社會服務,主張文道合一,強調文章的現實功能和社會效果。
王安石的散文多短小,少見長篇大論,文中直陳己見,簡潔峻切,形成了“瘦硬通神”的獨特風貌,其所書《讀孟嘗君傳》:“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短短四句話不足百字,然而層次分明,議論周密,對我們歷來所推崇的“能養士”的孟嘗君提出了質疑,“雞鳴狗盜”之徒與真正的可堪一用的“士”如何能相提并論?一國如得英才,絕非此類。
這一篇《慈溪縣學記》同樣簡潔直白,雖然在為縣學作記,實則包含了王安石的教育觀念。北宋前期學校衰廢,各地只立孔廟,并無教育,甚至到了孔廟壞廢也沒有修繕的地步。時至慶歷,朝廷雖下詔興學,卻又限定生員滿二百始可設學。慈溪的縣學久久不能設立起來,而新任縣令是個實干家,他令民眾募捐籌集資金,修整校舍,招收生員,聘請了學與德均佳“學行宜為人師”的學者——杜醇任教席,深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成也”。王安石之所以為之作記,是因為他認為學校十分必要,經過培養而明白治國之道的古代士人,則可成為官吏的后備之選的理念。而林肇絕對是一個有辦法的“循吏”,既不違反國家政令,又想辦法使教化興盛起來,作為一個實用的變法者,他欣賞林肇的所作所為,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學校不僅培養“智仁、義圣、忠和之士”,亦為傳授“一偏之伎,一曲之學”之所,是國家儲備人才的倉庫。歷代統治者“立學之本意”皆為此。
王安石在文中抒發了自己的教育見解,毫不客氣地指出,教育要培養的是實用型人才,包括“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考藝選言之政,至于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出于學”,各行各業都要有專業知識作為依托,他反對教育只是“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于先生的選任,王安石主張“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于位而去者,以為之師”。
文中諸種教育觀念不僅僅在宋代顯得十分突出,就是拿到現今,也仍舊很實用,不管是從一個實用改革家的角度,還是從一個傳統士大夫的角度去看,“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后至于善”,慈溪縣學的設立都是會使人“至于善”的。人善,于國于家,都有大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