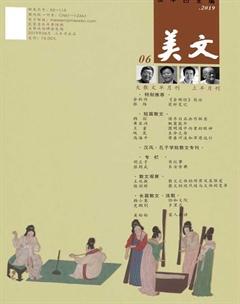2000至2015年
史鵬釗
再回村莊
2015年11月6日,農歷九月二十五。爺爺去世三周年紀念日,我再一次地回到了史家河。冰冷的秋雨已經淅淅瀝瀝地下了幾天。回村之前,聽說60多歲的大姑病了,且病得不輕。還有,我的小姑奶奶都80多歲的人了,身體也不是很好。我、父親、姐姐和弟弟一起,前往大姑家所在的永樂鎮漢坡村。彬永二級公路上漫天迷霧,車在緩慢地爬行。進入村莊的生產路上,雨大了起來,坐在弟弟的車里,能見度不到幾百米,急著落下的雨敲在了擋風玻璃上,噼里啪啦地響個不停。
父親和我已經記不清大姑家的具體位置,父親這些年在外務工,家里與親戚之間人情世故都由弟弟來操持。誰家孩子結婚,誰家女兒出嫁,誰家孫子過滿月,誰家老人棺材落成,誰家新房建好,誰家老人去世,等等,都會給弟弟打電話或者捎話去,弟弟就會代表父親去參加親戚家的紅白喜事。就是因為血緣和婚姻的關系,農村親戚一年中的交往才算是得以聯系。親戚之間,已經沒有原來時候,在農閑或者過年之間相互走動的興致。遠房親戚見面,基本都是在別人家的紅白喜事上,見了面,打個招呼,相互之間已經沒有原來那種血緣之間的親近和熱乎。常年下來,親戚之間的關系也就越來越淡漠。
到了大姑家,推門進去,整個院落鴉雀無聲,大姑因病在炕上躺著,前幾天才出的醫院,人老了,身體就不那么硬朗,老年病也就日漸凸顯。姑父蹲在炕頭上抽著旱煙,正好天雨,莊稼地里也沒有多少農活,他們老兩口有一句沒一句地說著些陳年舊事。我們走進了房間,他們才回過神來。大姑已經基本上不認識我,姐姐再三給說我是誰誰,她才慢慢地想起來,說咋都這么大了。大姑家還是老房子,農具、家具、糧食囤都在房間的地上擺著,房間墻上的相框里,掛著一些陳年的老照片。最珍貴的一張是,奶奶帶著她幾個兒女的一張合影,照片已經有些褪色和腐蝕,但依然可以看清她的面龐。這張照片,在奶奶的孩子里面,唯一就缺了父親一個人,父親作為長子,分家早,過早地承擔起了那個大家庭的責任。父親和大姑、姑父三個人聊著,說著這些年的農事和生活。大姑家這些年種植了些蘋果樹,一年有一些產量,能賣上一點錢。大姑家有四個兒子,其中三表哥快40歲了還沒找上對象,后來就給別人做上門女婿了,三表嫂是個小50歲的女人,在爺爺去世時,我見到過她在廚房里幫忙;四表哥是1974年左右出生的人,30多歲在西安打工時,自談戀愛,娶到了一個四川女人,女人算不上很漂亮,但是個機靈人。他們結婚時,我還和家族的人一起,參加過他的婚禮。婚后生了一個女兒,四表嫂就外出不歸,至今好幾年已不知去向。四表哥還在外面打工,留下的女兒由大姑照看著,在鎮中心校上學。家里的墻壁上,貼著三五張紅彤彤的大獎狀。
窗外的雨慢慢地停止,我們告別了大姑,順著盤山的柏油路向安家河的川道里下去。鄉間的道路雖這幾年基本上都得到了硬化,廣大農民出行的條件略有改善,但走的人越來越少,路兩邊被長瘋了的柴草所吞沒。溝邊上,低頭的野雞都在爭先恐后地覓食。車過來,野雞們緊張地飛起,又落下,在品嘗著野草籽的美味。車子順著高安公路,經過馬家河、林家河,一直走到史家河村的吃水溝,柏油的路就斷了頭。車子進入了泥濘的土路,左右搖擺。這些年,走路的人少了,路就變得更加高低不平,荒草叢生。雨水像一條條小溪,匯聚在一起,順著低低洼洼的路,肆意流淌。弟弟緊緊地握著方向盤,不敢輕易地快速行進,稍有不慎,車子的尾部就擺個不停,我們坐在車里,也像過山車。花了近半小時,才走到了爺爺老房子的路邊,下車后穿上雨靴,深深淺淺地走在荒草堆里。
雨又下了起來,淅淅瀝瀝。家族遠遠近近的人都身穿白色的祭服,頭戴孝圈。進門,下跪,祭奠,磕頭,起身,作揖。三周年前,爺爺去世時,我踏進了這座老屋。三周年后,我作為孫子輩的老大,再次回來,就是為了參加這最后的集體祭奠。祭服,是老人去世后用白粗布做成的孝衣,而今在農村,已經沒有人來專門招呼著去裁裁剪剪,每當有喪事,在外的人回鄉時,都會給自己找上一件白衣攜帶,白衣大多都是來自醫院的白大褂,白大褂的左上方印著“北極醫院、西坡醫院、彬縣醫院”等等字樣,儼然每個穿白大褂的人,都好像成了醫生、護士,來為逝去的親人,消減著最后的病痛。中午時分,雨暫停了下來,我一個人踩著枯草,向村廟和河邊走去。村頭的大廟就好像村莊的地理航標和精神祠堂,一直威嚴地屹立在那里,見證著村莊千百年來的風風雨雨。村廟俗稱“老爺廟”,官稱“關帝廟”,初建年代不詳,清宣統年間重修。坐西向東,土木結構,硬山灰瓦頂,五架梁,面闊9米,進深6米,內有金柱,二副梁上有駝峰,中檁上題有“大清宣統己酉年二月二十二日喜逢黃道立柱上梁大吉大利閣舍全義重修”字樣。廟內有一通清代道光二年(1822)所立的功德碑,記錄了數百商號雅館主人的捐贈善款,如“恒靜館、仁義館、永盛居、興盛堂、清盛館、仁和靜號”等字樣依然清晰可見。南北兩側墻上殘留有彩繪壁畫,畫中人物肖像栩栩如生,色彩線條艷麗明快。廟門和窗欞已歷經風雨,殘朽不堪。
沿河灣而下,蘆葦在河邊伸長了脖子,在斜風細雨中不停地搖曳著,這些《詩經》里的“蒹葭”,從幾千年前的《詩經》里來,一歲一枯榮,在水一方的我,頓時變得溫暖而又悲傷起來,溫暖的是,這一歲一枯榮的植物,它們不棄不離,始終與這長流的紅巖河水緊緊地抱在一起。水是蘆葦的血液,蘆葦被水滋養著,在春夏季節一截截地生長,層層密密,緊言慢語;而到了秋冬,它又在細水流光里靜默不語,踮腳守護著村莊的孤獨與蒼茫。我踏進了河水里,雖隔著雨靴,但深秋河水的冰涼依然從腳底傳遍全身。村莊里的每道山山溝溝里的溪水,都越過了礫石和草木,流到了紅巖河里。紅巖河的清水在雨滴中泛著波紋,黨家溝里的溪水有些渾濁,兩條水路交匯在一起,一清一濁,一寬一窄,逐漸交融,流向遠處。就是這條河,才讓我們的祖先們傍河而居,繁衍生息,直到今天。飲用,就來河邊取水;洗衣,就來河邊搓洗。夏季的深夜,收割完麥子的人也會在河里,擦洗掉自己的疲困。
河南岸的高渠山、十二洼籠罩在茫茫的白霧之中,巍巍聳立,默默無語。百樹落葉,千草枯萎,正在秋雨中歷經著“一歲一枯榮”。高渠山、十二洼的每條鹼畔里,我都曾走遍。放牛,割草,挖柴胡和遠志這類野生藥材,是暑假唯一的生活。十二洼下的砂巖崖壁下,有三窟石窯。據陜西有關文物方面史志的記載,為唐代遺存。窟口呈方形,2號、3號窟口用土坯封堵。石窟高1~3米,寬2.5~3米,進深5~6米,其中最大窟面積約18平方米,最小窟面積約14平方米。為何用土坯封堵,至今成謎。有老年人說,土坯封堵是舊社會為了躲避土匪,當聞有土匪入村時,村里的男男女女就搭著高高的木梯子,爬進石窯里后,將梯子拉進窯里;待土匪過村后,人們再從梯子上爬下來,繼續著自己的生活。而如今,這些石窯里已經成了鳥兒的安樂窩。我站在石窯下的河北岸,見一群群的鳥兒,啾啾地叫著,站在石窯的土坯上,為悄然無聲的村莊,帶來了一聲聲音符。
時近下午3時,天色暗沉,烏云在山頂森羅密布,便折身向祖父生前的老房子里走去。老房子建于20世紀90年代,部分屋頂已有些塌陷,可以看到拳頭大的一片天空。人不住了,房子變得空落落的,沒有了生機,院落里長滿雜草。最后的祭奠儀式開始,磕頭作揖,姑姑們哭出了聲音。悲戚而莊重,我始終認為,在城鄉二元結構的今天,農村最有傳統且有儀式感的,莫過于老人們去世后,祭奠埋葬的禮儀。喪事活動從何時而起,已無可考,但隨著社會的文明進步,已大大從簡,一些迷信的做法已逐漸淡出,但如奔喪、喪服、吊孝、祭日等祭祀的傳統禮節仍綿延流傳。祭奠結束,要去墳地。順著濕滑的小路,盤旋而上,走到墳地里去。逝者如斯,祖父的墳頭,幾棵松柏青翠,他已經在這向陽的大地,睡去了三年。從老房子走到墳地,跨過了半個村子,除參加祖父三周年祭奠的人外,只遇到了一個村人。他正提著籠,從已經霜凍了的地里,撿回來幾把青辣椒。溝溝洼洼的柿子樹,星羅棋布,紅彤彤的柿子掛在枝頭,已經沒有了人去采摘,任憑其熟透,成了灰雀們飽餐的口糧。
離開了祖父的墳地,我們需要沿著山路走,幾千米后才能到塬上的柏油路,有車在等。一路的泥濘,深一腳淺一腳地向前邁著腳步。我與二姑和三姑同路,聽她們說著這些年的陳年舊事。三姑一家人早年去了臨潼,在外當廚師做涼皮生意十幾年,積攢了一些財富。年齡大了,有病在身,回來在縣城買了房,安了家。但是她閑不住,現在還在一家工地給工人們做飯。在外這些年,她的觀念更新快,許多家長里短的事情都不掛在心底,人活得也通達豁亮一些。走著走著,二姑掉了隊。二姑嫁給新民街道的姑父,姑父有修車的手藝,在自己門前開了個修車鋪子,主要修理各種農機。他人勤快,話不多,來人修車,不分黑明晝夜,從車底下爬進去,到修好出來時已滿身油污,30多年來,小有名氣,已經形成了趙師修車的良好口碑。二姑在家照看三個孫女,他的二兒子前幾年出過車禍,右腳有些殘疾,經營著一家農機配件店,這是她這些年來的心病。她和我們在路上時,就絮絮叨叨地說著,二兒子經常外出吃飯,還沒有生下兒子,等等。我和三姑都在勸她,應該正確地面對這些,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活法,況且年輕人的生活行為方式,和他們那輩人相比,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二姑口上答應,但是心里還是一團苦愁,她的眉頭始終緊皺著,無法舒展開來。
我一步步地離開村莊,村莊也一點點地遠離著我,漸漸地淹沒在溝底的深處。到了文家坡村,站在塬上,看著村莊在深秋的蕭瑟中,像一位耄耋的老翁,溝溝壑壑的皺紋,布滿面龐,那條永不停息的紅巖河,緩緩地流淌著,成了故鄉無法訴說的眼淚。雨又下了起來,急急地落下,向每個人踩下的泥窩窩里,如受驚的蛇一樣,蜿蜒著匯聚成溪,它們要流向溝下的村莊,順著各溝渠向紅巖河里去。它們不知道,我的祖先埋葬在這里,我的祖父埋葬在這里,我的痛苦和惆悵也在這里,這里還埋葬有母親生我的胎盤,這里有我20年生活舞臺最優美的布景,而我卻成了故鄉的叛逆者,不聽話地逃跑了,跑得很遠,很遠。甚至在異鄉的夢里,又開始追尋歸鄉的路途。
故土難離
故土難離,始終是千百年來積淀在中國百姓心中的情結。
2016年5月10日,初夏。在這天中午,弟弟打來電話,說在史家河小學外的磚墻上,貼出了關于紅巖河庫區移民搬遷的公告,并附有征地補償分配到戶花名冊,每戶人家賠償的金額都算得清清楚楚。公告要求5月6日至11日完成征地補償款的分配,5月12日至16日完成庫區搬遷戶的搬遷,5月17日至21日完成房屋、窯洞的拆除。
公告貼出后,寂靜的村莊,頓時變得沸騰起來。這些年,許許多多的年輕人,都離開了村莊,在外面的世界里,經營著自己的生活。但是他們的身份證地址還是史家河。史家河的村莊里,還有他們留下來的破舊的房屋、荒蕪的田地,他們的戶籍還與史家河這個即將要消失的村莊,緊緊地維系在一起。當看到搬遷公告時,還廝守在村莊的老年人慌了手腳,搬遷的期限是多么地緊迫,一輩子的家業都在這里,他們收拾了那么多的柴火還整整齊齊地堆在家門口,他們種了別人荒下來的土地里,還長著已經灌滿了漿的麥穗。有人低下頭,撓著頭說,能不能把這茬莊稼收了呀?莊稼是農民的命啊,莊稼爛在了地里,這是要被人戳脊梁骨的啊。他們就去蹲在田間地頭上,抽著煙,看著麥草稈兒已開始發黃,離收這最后的一茬莊稼,時日不多了。
這些年,靠天吃飯的村莊,原來在村莊里生活的能干人,基本都加入到了外出務工的大潮里去,他們到了城里,靠著自己的力氣和手藝吃飯。村莊里僅剩下了幾個村干部和已經沒有勞動能力的人。史家河村和千千萬萬的農村一樣,人心離散,人去地荒。這些年,修路修橋,無人牽頭;貧弱鄉鄰,無人過問;水利興修,無人去管;鄰里糾紛,無人幫其出面解決;紅白喜事,無人幫著操持。綿延了幾千年傳統農耕文化的村莊,突然成了斷線的“風箏”,失去了親情、鄉情,失去了向心力,轉型中的廣大農村,鄉村秩序越來越紛亂,鄉村社會的紐帶也越來越松弛。
就是史家河搬遷的這件事,村干部也是想盡了辦法,讓每個家族里選一名代表,代表的作用就是做本家族親屬的思想工作,并參與分配到戶的全過程。我們家族,選了我的大哥作為代表。他原來在稅務機關工作,后來下海,在縣城里經營過食堂,開辦過旅社,后來趕上了房地產開發的大好時機。他雖然這么多年沒有在村莊里生活,但是在村民鄰里之間有一定的口碑和威望。2015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創新鄉賢文化,弘揚善行義舉,以鄉情鄉愁為紐帶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鄉建設,傳承鄉村文明。在村莊搬遷的過程中,各家族選出的代表或多或少都有些鄉賢的味道。2016年6月12日,狗和大哥在北極街因搬遷的事情從爭吵,到雙方大打出手,到后來人進了醫院,無不表達著個人和集體利益的碰撞和糾葛。
2016年11月,我再次踏進了這片生我養我的土地。
史家河村,地處渭北黃土高原的溝壑地帶,唯一通往縣城的高安公路因為水利工程已經無法通行,從塬上的鄉村公路繞山而下,群山環繞,植被落葉,沿途一眼望去,丘壟、溝沿、樹枝、草垛……所有一切,都安靜了下來。因搬遷賣掉的樹,已被伐掉,剩下的是與大地平行的樹根,還深深地扎在土地里,一圈圈年輪是那么刺眼。弟弟說,我們家的三棵大楊樹,長了30多年,總共賣了300多元,就這樣還給木材廠的人說了不少好話。弟弟說,你想啊,人家買了樹,還要找人來鋸掉,還要找車來拉走,這些都是不少的費用。殘垣斷壁,這個成語最恰當不過。鎮上的搬遷政策出臺,同意的人簽字后,拆遷的“大家伙”(設備)就進了村。屬于房子的,都被推倒在地。長滿苔蘚的瓦礫和土坯交織在一起,無不言說著村莊最后的留戀。
我們還沒有走到村中的老學校院里,就聽見一陣狗叫。走進院子,見有人來,我的一個遠房長輩站了起來,她已經不認識了我。弟弟在一邊介紹,她說,以為又是拆遷的人來了。
她說:“我在咱村已經生活快50年了,現在老了,舍不得離開村子,就留下來種地。這里是我們的根。”她家原是依山而居,住在鑿的窯洞里,窯洞已幾近坍塌。為了安全,加之搬遷,村里的干部就動員她搬到學校的公房里來住了。我沒好意思問她,她將來要搬到哪里,也不知道她是否用拆遷的補償款在城里登記了經濟適用房。
她的大兒子,已經去世好幾年。二兒子今年已經快50歲,還是單身漢。在傳統的農業社會里,人們都喜歡生兒子,可是生的兒子,如今找不到媳婦。究其原因,還是因為窮。他的兒子很少外出打工,靠著莊稼的收入也極為有限,貧困的問題始終還沒有得到解決。就在我回去的那天,史家河四組馬家底傳來了嗩吶的哀樂聲。這些年,我聽到最多的就是,村里的哪位老人去世了,生老病死,再正常不過。馬家底有人已經因為拆遷搬到了縣城里,但是老人去世后還得拉回來埋葬。在農村,喪葬一直被視為莊嚴的大事舉行,設靈堂、出殯、埋葬和祭奠等環節極為講究。出殯環節為整個喪葬禮儀的高潮。孝子先祭,眾親友接著祭祀,出棺后,長子捧靈牌,長孫肩扛“引魂幡”在前引路。嗩吶吹奏哀樂,棺木一般由10多個青壯年肩抬,后面親屬緊跟,同族鄰里幾十至上百人同赴墓地。
而如今,已經搬遷的人已經沒有了家,就只有在城里給老人辦喪事,莊嚴的儀式已經再簡化不過。馬家底的人在縣城的小區里,搭了帳篷,舉行了祭奠儀式。聽回來的人說,這樣的做法也引起了同小區住戶的強烈不滿,因為舉辦喪事,影響了人家的正常生活。祭奠完了后,去世老人的棺材就用車拉了回來,還是埋在了史家河的土地上,這也是長期一段時間來,村里所有兒女給老人送終時,要面臨的一種方式。老人們生活在村子里,卻在自己老去時,去縣城里轉了一圈,最后又回來落葉歸根。
出生的兒子
2015年8月30日中午,杜陵塬,初秋。妻經近十月懷胎,小家伙還差幾天就要來到這個世界,在子宮里躍躍欲試,摩拳擦掌。經檢查,醫生說羊水偏少,遂住院留觀。一陣忙活之后,托熟人,找關系,才在326床住下來。
晚飯過后,太陽落下地平線,塬上的秋便變得安靜起來。草木郁綠,蟋蟀啁啾,我們在燈火通明的產二科三病區來來回回地邁著步子,不能自由地外出……
守門的護士說我可自由來回,妻不可,入院了醫院就得為產婦負責,她挺著大肚子,踮起了腳尖,便笑著向外張望,夜來風的世界里,自由而彌漫。她說還是家里好,舒服,想干啥都好。就是的,家里好,我們兩個人的世界里,白天都在外忙忙碌碌,回到家一起窩在偌大的沙發上,或在廚房里練習著在某某大廚小宴里看到的菜肴,這也是我們普通人的幸福。
回了病房,同房間的床友在打電話,別人問醫院遠不遠,她說在三兆,說完了又覺得三兆是個不吉利的地方,手拿著電話對著窗外,“呸呸呸”地向夜空吐灑著口腔的分泌物,然后問一旁的老公:這怎么說呢?杜陵?哦,哦,雁翔路,雁翔路……
夜深了,已過了11點,三病區的房間里不時傳來新生兒的聲聲啼哭,或清脆,或沉悶,或遠或近,產婦虛弱的身體,卻無法阻止來自兒女人生的第一口吮吸。聽著孩子們遠遠近近的哭聲,我躺在簡單的陪護床上,想起了今天一起在病區遇見的一家四口人,孕婦懷孕3個月,有可能是大三陽,且小孩保不住,她不到20歲的臉上,聽見醫生還沒說完的專業術語,眼淚就止不住地流淌了下來。
8月31日,第二夜。一早,6點爬起來,滿眼迷糊。走在婦產科的通道里,竟已有20多人在婦產科門診口排隊。人估計已站累了,所以有水杯、手提袋、檢查表,甚至是一袋豆漿,一溜兒地代替著主人,悄然無聲地排隊。回到病房,給妻說,妻笑,說看來我們原來一直都是來得算晚的。是啊,自從1月10日來醫院初檢,到8月30日的最后一次門診,我們從來都是第10位以后。周內從來沒來過,原來人這么多。人常說,早起的鳥兒有蟲吃。早早來掛號的人,當然就排在前面,早檢查早結束,說不定回到家了還能睡個混沌覺。
早8點后,護士就專門帶著妻去做全面B超。羊水卻從昨天的75mm上升到今天的90mm,已從羊水偏少回歸正常值,一陣竊喜。問醫生,讓回房間里等待。看著B超單上的各項指標,妻已開始用手機軟件概算小家伙的體重。算完了,咧嘴笑著,說是個胖小子。這十月懷胎以來,她是最辛苦的,看看她的肚子從小變大,從大變圓,到某個時辰“缷貨”,然后再開始撫育的階段。
同房間的孕婦已經哭了好幾次,她是二胎,第一胎就是剖宮產,說是今天的手術約到了9時。她的眼淚里有恐慌,甚至也有喜悅。直到快16時,護士才來請她去手術,不一會兒,6斤重的丫頭就陪著她回到了病房。小丫頭粉嘟嘟的,來到了這個世界,躺在媽媽身旁,攥著小手打哈欠,甚是可愛。
夜晚的走廊里,傳來的都是嬰兒們的啼哭。他們用哭聲表達著自己的全部,餓了困了拉了尿了,他們的聲聲啼哭,都召喚著初為父母的人們,開始著手忙腳亂。
護士常常入房來,查體溫,測胎心,問胎動,無微不至,以職業的素養為迎接一個個新的生命,在病區穿梭著。晚飯過后,陪妻在走廊散步,她說昨晚夢見小黑豬崽,我開玩笑,說是不是夢見是在窗外的杜陵塬上撒歡呢?她大笑,夢是好夢,夢隨心生,我知道她也是期待著自己肚子里的小可愛,也早早地出來,給她驚喜,讓她的母愛泛濫起來。
是父母,都愛自己的孩子,哪怕是阿貓阿狗,何況我們即將為人父母,也是要在自己30多年的人生旅途上,開始走另外一條“養兒方知父母恩”的路子呢。
9月1日上午,羊水深度88mm。一切指標正常。醫生檢查,小生命的到來,尚有幾天,就出院回家等待。9月6日晚,正準備洗漱了換衣的妻子,突然感覺體內羊水破,遂趕快又進了醫院,又是一陣抽血,檢查各項指標,監聽胎心。9月7日凌晨2點零5分,妻子二次被推進產房。母親、大姐和岳父、岳母在產房門口的條椅上左右不安,期待著小生命的到來。凌晨2點58分,允許家屬進產房陪產。當我穿上專門的防護衣站在產房門口,心里一陣緊張。3點33分,兒子出生,堅強得沒有幾聲哭啼。助產士用手敲著孩子的小腳掌,小家伙才半睜開小眼睛,看著這個世界,嚶嚶地哭了起來,我的內心一陣柔軟。忽想起,孩子出生前每月一次的檢查,雷打不動。每當我們走到醫院里,通過B超,看著孩子一月月長大,通過醫生聽胎心,聽見他的心跳像擂鼓般咚咚咚地響著。妻子也成了家里的重點保護動物,她每天下班回來,總是會說起孩子一天來的“表現”。每天定時地在子宮里翻騰,或是在里面呼呼大睡。聽醫生說,孩子的活動是豐富多樣的,瞇眼、伸展四肢、轉身、蹬腿、翻跟斗等等,母體的溫室,儼然成了成長的天地。她每天都穿著寬寬大大的衣服,就擔心衣物束縛了孩子馳騁的自由;她不再像原來那樣臭美,不化妝從不出門,而是接觸到每件物品時,都會尋找是否有“孕婦慎用”這四個字。為了讓孩子快快成長,我們除了把空氣、陽光和水作為最好的營養素之外,每天還不重樣地有各類水果、奶品。
2015年12月,我去西安曲江的某派出所為新生的兒子上戶口,看到戶口本上他的身份證編號是“610101”開頭,心中不禁多了一些感慨。我從高中畢業考上大學,才將自己的農村戶口轉到了城里,而15年前,作為農村出生的孩子,要想改變自己的命運,只有參加高考這一條道路,而我的孩子,他不會再像我一樣,有在山溝溝里生活的經歷。在西安這座古老的城市里,我已經生活了10多年,還將繼續生活下去。這10多年間,我工作,成家,買房,生子,住所搬了四五次。單身時,我一個人住在城南叫作“瓦胡同”的民房里,與來自不同地方的“蟻族”擠在一起,共用衛生間和洗臉池,每到冬天,西北風將不結實的窗子刮開來,有雪成了訪客,落在角落。結婚后,我們在城內叫作“集賢巷”的地方,租住了兩年,房子是個單位家屬院的頂樓,20世紀60年代的磚混結構。每當下雨天,只有推著床找不漏雨的角落,或者是盆盆罐罐擺滿地。后來實在沒辦法,就又搬到了緯二街,又住了一年,才搬到了貸款買來的新房子里。兒子出生后,我們作為父母,給予的環境,是我們小時候做夢也想不到的,因為我們小時候真不知道,山的那一邊是個什么樣的世界。
安居,安居
對像我的父母這樣的農民來說,失去了村莊,跟著兒女,到了城里,他們有關村莊的所有信息,都來自村干部給我兄弟的電話。自從移民搬遷賠償的事兒啟動以來,當了十幾年村干部的他們,和村民的關系也隨之遠了起來,因為賠償款是觸碰每個人神經的問題。村干部與村民之間的不信任成了大事兒。
自從賠償款明細公布以來,村子里的不穩定因素就多了起來。網絡上出現了反映村干部問題的帖子,民生熱線上有了村民的信,還有就是非正常上訪等,這也讓基層政府的人忙活了起來。村干部是村民的唯一指望,因為他們肩負著一個村莊的責任,也是國家權力在農村基層的體現啊。雖然史家河村的人都因為搬遷而四散,但是他們的名字還在史家河村的名單里,一個也不能少。2017年8月3日,彬縣紀委通報了四起侵害群眾利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典型案例,其中史家河村黨支部書記、村主任和村文書聯合侵吞惠農資金問題赫然在列。通報稱,其三人于2003年和2007年,將村集體105.4畝林地和76.57畝糧食種植面積分到三人及其親屬名下,共同侵吞退耕還林資金和糧食綜合補貼10.71萬元,2017年6月,縣紀委給予三人開除黨籍處分,并將三人移送司法機關。
古人言:千里之堤,潰于蟻穴。近年來,鄉村基層“小官貪腐”問題嚴重。基層群眾自治組織的村干部,已經成了小官巨貪的典型代表,每天紀檢監察部門公布的案例舉不勝舉。重要的是,村干部作為國家權力在基層落地開花的神經末梢,看似無關緊要,實則大權在握。他們是國家意志的擴音器。村干部被移送司法機關,有些年齡大的村民們又開始唏噓不已。說那村支書都快60歲了,剛上任之初,還爭取來資金給村里修了路;那村主任,雖然愛打麻將,但人還是個好人,最小的兒子才結婚不久。淳樸的村民,以為村干部們要被判刑,要有牢獄之刑。可是他們不知道,當前的小官貪腐已經不再局限于蠅頭小利了,已經不再明目張膽地向自己兜里弄一點小錢,而是已經利用了大量基層行政的復雜性、制度監管的漏洞、政策實施的缺陷,冥思苦想著謀取巨額利益了。
十九大報告中指出,要在市縣黨委建立巡視制度,加大整治群眾身邊腐敗問題力度。強化不敢腐的震懾,扎牢不能腐的籠子,增強不想腐的自覺,通過不懈努力換來海晏河清、朗朗乾坤。
縣城的北灘里,原來是縣城農業人口的莊稼地。而今已經成為縣城最為鮮亮和活力的地方之一。隨著越來越多的人流動到了縣城,安居工程住房成為政府為人民群眾住有所居、安居樂業的民生工程。從史家河搬遷出來的農民,按照安置的要求,都在這里登記了屬于自己的房子。村子里的一草一木、一房一田,已經不屬于被賠償過了的農民。
在城里遇見了軍娃,他屬于年輕一代的農民工,盡管和父輩一樣,出身于農村,他卻有著與父輩完全不同的精神面貌和未來預期。他最初打工來到了西安,后來又去了深圳,聽他說這幾年又在上海。他念了一些書,但早早走向了社會,沒有獨立干過農活。對于農活,我們這代人沒有了在田地里勞作的吃苦精神,當然在社會的大熔爐里,曾經的工作也是揮汗如雨,但是至少不會再種地。我和他說笑著,他回來就是參加分房子,這是村莊給予他這個戶口還在村莊的人,最后的福利和饋贈。他在遙遠的城市打工,成家立業,卻始終沒有安家落戶。在深圳、上海那樣的大城市靠著打工置業,對他來說基本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很珍惜這次村里的選房活動。他要親自選,選自己最喜歡的樓層和戶型。他笑著說,這是他的歸宿之地。如果他有一天回到了縣城,在他的人生規劃里是要過上像城里人一樣的生活,因為他已經融入了城市。
有句話說,農村穩則天下安,農業興則基礎牢,農民富則國家盛。史家河的這些農民,和中國千千萬萬的農民一樣,都在上層制度的設計下,進入了轉型時期。年輕的一代,歡欣雀躍,期盼向往著能盡早離開偏遠的鄉村;老年的一代,痛苦無奈,覺得告別了田地,就斬斷了自己謀生的雙手。父母的一代,他們是中國傳統農耕文明的主力軍,但是今天卻向現代的城市文明不斷行進著,他們無法丟棄窮鄉僻壤的村民艱苦樸素的生活傳統,他們對在縣城里生活的路,還需要繼續適應著。他們中甚至有些人一輩子沒來到過城里,沒有坐過電梯,沒有聽過什么叫作“物業”,但是他們如今知道,單元房里不能燒柴火,每月還要繳納物業費,他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吃飽穿暖不得病,手頭還有點余錢花。還有那些我已經叫不上名字的孩子,已經開始了在縣城小學的求學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