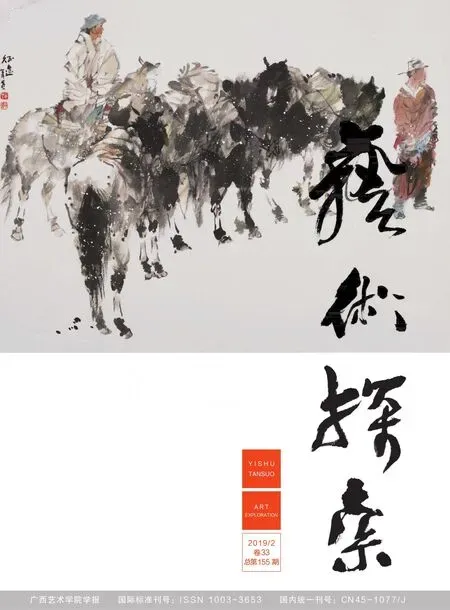音樂創作中歌謠式主題的呈現
——以吉雅·坎切利的交響曲為例
任 佳
(江蘇師范大學 音樂學院,江蘇 徐州 221000)
《新格羅夫辭典》對“主題”的界定是:“一部作品或作品的一部分中最根本的音樂素材,通常擁有一段具有特點的旋律。主題有時可以作為一個完整的音樂表達獨立于所屬作品。”[1]352由此可見,主題是一部音樂作品的基本樂思,篇幅長度不定,完整性是其最基本的特點。
在交響樂作品中,主題的意義更勝于室內樂作品。因為在交響樂創作過程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創作問題是主題構造形態的表現力問題。主題一系列外在的表現,如音高、節奏、力度、音區等所呈現的風格特征直接指向作品的創作內容與主導思想,展現出作品的內在屬性。除此之外,對一部完整的音樂作品而言,主題由于被多次強調,它的地位是高于其他段落的,聽者對主題的記憶也是比其他段落要深刻的。主題只要清晰鮮明,就會牢牢地印在聽者的腦海中。
坎切利對主題在一部音樂作品中的重要性有著清晰的把握,因而他對每一部交響樂主題的設計都非常準確到位,主題也自然成為其作品最具指向性的一種外部特征。從心理學角度出發,這種做法生動有效地增加了聽者對主題的理解與回憶。因此,下文將對坎切利交響音樂作品中的主題進行詳細分析,以揭示作曲家交響樂創作中主題的呈示與發展。
一、單聲式歌謠式主題
單聲式歌謠式主題主要包含以下兩個特點:第一,音樂作品的主題聲部形態或以單聲部形式呈現,或以主調音樂中典型的旋律加伴奏的形式呈現,或以早期復調音樂中簡潔的奧爾加農形式呈現。第二,主題的音高與節奏運動如歌謠般簡潔、綿長、幽靜,多見調式調性內的自然音高并以級進運動為主。
在20世紀之前的歐洲“共性寫作”時代,作曲家普遍采用主題進行創作音樂。20世紀以后,很多作曲家在創作時常常以力度、音色、節奏等各種要素作為整部作品的創作核心。但格魯吉亞作曲家坎切利仍選擇以強調、展開、引申主題的創作手法呈示和發展音樂,由此可見,主題在坎切利七部交響樂作品中具有重要意義。
坎切利的七部交響樂作品都是在音樂開篇的顯著位置便呈現主題,每一部作品的主題都經過細致雕琢,承載了作曲家的思想,體現了作曲家的美學追求。除此之外,坎切利七部交響樂作品雖然都展現了作曲家的風格,但就每一部音樂作品自身而言,其均是一個獨立個體,并具有唯一性。由于坎切利每一部交響樂作品獨有的藝術形象首先是從主題中體現出來的,因此代表音樂作品個性化的主題也同樣是獨一無二的。如在《第三交響曲》中,主題由人聲演唱;在《第四交響曲》中,主題由兩把小提琴演奏;在《第五交響曲》中,主題由撥弦古鋼琴演奏;在《第六交響曲》中,主題由兩把中提琴演奏;等等。
由上述細節能夠看出,坎切利強調主題音色,強調主題性格,強調作品以主題建構為中心。他每部交響樂作品中主題的結構都是明確的,這樣的結構不僅是整部音樂作品的核心結構與基本骨架,而且支撐了整部音樂作品的發展。正是由于七部交響樂作品清晰的主題呈示,我們才能進一步領會坎切利意欲描述的情感世界,也正是由于主題所包含的深層意義使作曲家追求的思想世界能夠清晰的顯露。
同時,坎切利的音樂由于對主題的精致刻畫,使聽者能夠依靠主題來識別其作品的創作風格,如緩慢,帶著冥想、思索、回憶等。正如杜夫海納所言:“作曲家選擇某個主題是因為這個主題是與他共存的,是因為這個主題在他身上喚起某種激情,帶有某種問號。”[2]355由此可見,主題與音樂作品的內容、創作背景、思想意義之間存在著極大關聯。作曲家需要通過各種技法將上述抽象的要素在具有主導作用和核心性的主題中表達出來。坎切利交響樂作品中的主題在音樂創作與呈現的過程中均承載著作曲家所欲表達的象征意義。以下將進一步對其交響樂作品中主題的具體特征做進一步闡述。①文中所使用的樂譜均為德國斯考斯基(Sikorski)出版社出版。
二、歌謠式主題的特征
(一)主題的音區設置
坎切利交響曲的主題常常體現出一種回憶性,這種回憶是久遠的、徘徊的、帶著思索的。因此,作曲家對其主題音區的設計首先控制在中音區,排斥明亮的高音區。
如在《第四交響曲》第一個主題“奧爾加農”的陳述過程中,樂隊處于靜止狀態,僅由兩把小提琴進行陳述,作曲家對主題音區的安排位于整個樂隊的中音區d1—f2。(譜例1)
譜例1 《第四交響曲》第1-13小節

《第四交響曲》第二個主題“夢幻”在陳述過程中,展現出室內樂化的形式,主要使用色彩性樂器豎琴與鋼片琴進行陳述,作曲家對主題音區的安排位于整個樂隊的中音區g—g2。(譜例2)
譜例2 《第四交響曲》第66-79小節

另外,《第三交響曲》的第一個主題“圣詠”在陳述過程中,運用人聲單一音色呈現,作曲家對主題音區的安排位于整個樂隊的中音區f1—c2。(譜例3)
譜例3 《第三交響曲》第1-3小節

《第五交響曲》的第一個主題“回憶”在陳述過程中,運用撥弦古鋼琴音色呈現,作曲家對主題音區的安排位于整個樂隊的中音區d—g2。(譜例4)
譜例4 《第五交響曲》第1-2小節

《第六交響曲》的第一個主題“低訴”運用兩把中提琴進行陳述,以第二中提琴的持續音襯托,中音區級進線條為主,主題音區的選擇位于整個樂隊的中音區bb—a1。(譜例5)
譜例5 《第六交響曲》第1-4小節

(二)主題的節奏設計
由上述譜例均可見,坎切利交響樂作品中的主題除多以弱力度與中低音區形式強調來呈現音樂外,其對于主題節奏的設計也是簡潔單一的,一個完整主題在陳述過程中基本保持了節奏的統一性,以下舉例說明。
《第三交響曲》的主題節奏非常單一,以四分音符與全音符的交替為基本形態。作品開始處3個四分音符均是站立在C音上的重復,哽咽、欲言又止的情緒瞬間涌現。這種同音重復使音樂產生遞進、微變,渲染出濃濃的鄉愁,作曲家努力營造著格魯吉亞安寧的生活氛圍。[3]90(譜例3)
《第五交響曲》的主題滲透在具有線條性運動的四個聲部中,每一聲部節奏清晰明了。其中,高音聲部為十六音符的勻速運動,偶有六十四分音符級進跑動的裝飾。這種演奏形式是巴洛克時期音樂中撥弦古鋼琴的常見特征,音樂整體形成八分音符富有律動性的節奏運動。(譜例4)
《第六交響曲》的主題由第一中提琴聲部圍繞八分音符、四分音符兩種節奏進行主題陳述,十六分音符多作裝飾性的經過潤色。(譜例5)
(三)以二度音程為核心的橫向音高關系
在坎切利的七部交響樂作品中,主題橫向運動過程中的二度核心音程形成的連續上行或下行音階式的運動已成為坎切利音樂作品主題的基本特征。下面將進一步舉例說明。
譜例1中,《第四交響曲》“奧爾加農”主題的橫向音高完全以二度音程的連續級進形態呈示。在第一樂句中,高音聲部線條自c音開始,經過連續的二度下行,到達g音;低音聲部線條自d音開始,經過連續的二度下行,同樣到達g音。在第二樂句中,高音聲部線條自d音開始,依舊使用連續的二度下行到達g音;低音聲部線條做e音的持續音形態。在第三樂句中,高音聲部線條自e音開始,為避免線條的呆板,上行二度進入f音后再連續二度下行,到達g音;低音聲部線條做f—e—f—g的二度音高行進,與上聲部對位。由三樂句高低音聲部的運動均能看到二度音程的貫穿性使用。
譜例3中,《第三交響曲》“圣詠” 主題的橫向音高以二度音程的連續級進形態做主要呈示,并輔以三度、四度音程跳進。此主題雖為三小節的一個完整陳述,但由于音樂速度、節拍、節奏的設定,此主題呈現出一小節一樂句的陳述模式。第一樂句人聲音高自c音開始,經過連續的二度下行,到達f音。第二樂句人聲音高自a音開始,先經歷上行連續二度再迂回連續下行二度,到達f音,形成拱形線條;前兩樂句形態主要由下行二度的級進運動構成。與前兩樂句對比,第三樂句人聲音高加入了三度、四度音程跳進,但二度音程的下行依舊是此旋律線條的主要運動方向。
通過以上對主題音區、節奏、橫向音高的分析,我們能夠看出坎切利每一部交響樂作品中主題特征的統一性與個性化。首先,坎切利交響樂作品中的主題常常設置為弱奏,其不僅設計廣板或柔板的音樂表情要求,而且追求長線條的、寬廣的音樂氣質,使音樂主題呈現出對中世紀宗教圣詠的模仿。其次,坎切利對主題的設計使我們能夠體會到其欲用主題勾勒出一幅幅具有回憶性的畫面的意圖,他用主題所具有的回憶性音調表現出一種特殊的音樂色彩。如《第四交響曲》中由兩把小提琴奏出的具有中世紀復音音樂形態的“奧爾加農”主題,結合教堂銅鐘的響聲,讓人仿佛置身于中世紀的教堂。《第五交響曲》中由撥弦古鋼琴獨奏奏出的干凈、清澈的“回憶”主題,把聽眾帶入精致、復古的巴洛克時期。由此可見,坎切利音樂中的主題不僅表現了廣袤的時空,而且闡釋了作曲家心中的歷史。
(四)主題調式的選擇
格魯吉亞民族有著深厚的宗教文化傳統,教會音樂對格魯吉亞人民有著深刻影響,多種教會調式與民間音樂融合,構成格魯吉亞音樂文化的主體。東歐民族音樂中的自然調式尤其是自然小調尤為多見,格魯吉亞音樂也不例外。因此,受到格魯吉亞音樂文化強烈影響的坎切利,在其七部交響樂作品中不同程度地體現出對多種教會調式與自然調式的偏愛。
1.對教會調式的偏愛
坎切利在創作中對教會調式的運用在其七部交響樂作品中有多樣體現。尤其是在其較為成熟的作品《第三交響曲》問世之后,他對教會調式的運用更加明顯。
(1)《第三交響曲》的“圣詠”主題調式
在《第三交響曲》開篇,作曲家設計了全曲最為重要的“圣詠”主題,用人聲進行勾勒(譜例3)。“圣詠”主題能夠清晰劃分三個樂句,一小節為一個完整的音樂陳述。其中,前兩小節的結束音分別是f,第三小節的結束音是g,這種結束音的寫法與教會調式圣詠常見的四種結束音d、e、f、g異曲同工。同時,譜例上的5個單聲橫向音高由低至高依次為 f1—g1—a1—b1—c2,這一五音列恰恰說明了其調式為利底亞調式。
由此可見,坎切利采用教會調式但并不使用完整八個音來指明調式,而是運用調式構建基礎的五音列進行交響樂作品的音樂闡述。這種構思不僅使作品充滿歐洲早期單聲部音樂的古樸之風,也使作品整體簡潔、清晰。
(2)《第四交響曲》的“奧爾加農” 主題調式
在《第四交響曲》的3小節引子后,全曲最為重要的主題“奧爾加農”出現,由兩把小提琴勾勒(譜例1)。由譜例1上二聲部線條的橫向音高關系中可以看出,作曲家將高音聲部設計為7個音高,由 低至高依次排列為 g1—a1—bb1—c2—d2—e2—f2,其調式屬性為多利亞調式。其中,第一樂句高音聲部呈現c2—bb1—a1—g1進行的四音列,后每一樂句逐漸增加高一級音級。從坎切利對主題三個樂句低音聲部的設計可知,作曲家設計了4個音高,由低至高依次排列為d1—e1—f1—g1,這個四音列同樣是源于古希臘時期的教會調式,是作曲家強調多利亞調式的一種鮮明表現。由此可見,五音列與四音列的相互關系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多利亞調式音階。(譜例6)
譜例6

同時,“奧爾加農”主題三個樂句的結束音均為多利亞調式的主音g,這進一步說明了坎切利對于教會調式的偏愛。
2.自然小調的應用
(1)《第六交響曲》的“低訴”主題調式
在《第六交響曲》的作品起始處,作曲家設計了全曲最為重要的“低訴”主題,并且運用兩把中提琴勾勒(譜例5)。從譜例中二聲部線條的橫向音高關系中可以看出,在第二中提琴持續強調的g音上,第一中提琴演奏的7個音高由低至高依次排列為bb—c1—d1—be1—f1—g1—a1,在這里 g 自然小調的主持續音地位被充分強調,因而《第六交響曲》建立在鮮明的g自然小調上。
(2)《第二交響曲》的“沉思”主題調式
在《第二交響曲》的作品起始處,作曲家呈現出全曲最為重要的“沉思”主題,在6把第二小提琴弱音器與泛音構成的背景層中,由豎琴、單簧管類、長笛類樂器共同建構的主題緩緩流淌而出。(譜例7)
譜例7中,主題旋律聲部的音高運動依次為f1—g1—e1—d1—c1—b—a,其 a 自然小調的特征鮮明。而在6把第二小提琴構成的泛音背景層中,其音高形成二度疊置的 d4—e4—f4—#f4—g4—#g4縱向音簇構成形態。在主題的第二樂句中,由豎琴、長笛、雙簧管承擔的主題旋律聲部的音高運動依次為g1—a1—bb—c2—d2—be2—d2,其 g自然小調的特征鮮明。
譜例7 《第二交響曲》第1-12小節

三、歌謠式主題的縱向化多聲處理
通過對坎切利幾部交響樂作品的分析,筆者認為,他的音樂具有鮮明的調式元素與調性中心。對坎切利交響樂作品的總譜做縮譜處理后可知,其音高在縱向上呈現出音塊式處理形式。在進一步的研究中,筆者發現,坎切利是將簡潔單一的橫向主題旋律做了復雜化的縱向疊置,由此形成了賦以單線條的歌謠式旋律交響性特點的音塊式音響體。
坎切利交響樂作品的起始部分常常以廣板速度開始做單聲部音樂陳述,當作曲家將音域狹窄的主題旋律首次呈現后,便會將此復雜化,即將橫向運動旋律線條中的多個音做縱向排列。由于坎切利交響樂作品主題旋律的呈現中多為自然音階形態,因而在作曲家將主題旋律做縱向化處理時,首先呈現出的是一種自然音狀態的縱向疊加。
例如,在《第三交響曲》的1-3小節(譜例3)中,作曲家對此主題音高的設計自低向高排列為f—g—a—b—c,在音樂向后延展的過程中,作曲家運用此橫向5個音構成了《第三交響曲》的縱向音高體系。(譜例8)
譜例8 《第三交響曲》的排練號11的第5-6小節

由譜例8可知,第一小提琴分為6組,演奏f—g—a—b—c—d共6個音高,第二小提琴分為6組,演奏g—a—b—c—d—e共6個音高,這種縱向音高的疊置均是源于作品開始處的歌謠式主題的橫向音高設計。
由此可見,坎切利這種縱向音樂的音高構成思維雖然仍與調式、調性、調中心音相關聯,但是已經突破傳統調性音樂中的三度疊置關系的和弦構成,體現出坎切利音樂作品區別于其他調性音樂作曲家的縱向音高思維構成形式。在這種將歌謠式主題旋律復雜化的處理中,頗具特點的音塊式音響體便形成了。并且當交響音樂矛盾逐漸推進與展開時,坎切利不再滿足于自然音構成的音塊縱向疊加,他在此基礎上加入了更多的半音,使音樂呈現出自然音與半音共存的狀態。坎切利時常將這種音高設計放置于音樂結構的高潮部分。(譜例9)
譜例9 《第三交響曲》第4小節(縮譜)

筆者對《第三交響曲》第4小節做了縮譜處理,以便于更加仔細地觀察坎切利交響樂縱向音高的構成特質,以及將歌謠式主題建構而成的基礎性音塊式音響體逐漸復雜化的演變過程。譜例9中,樂隊呈現全奏形態,銅管與鋼琴演奏上面兩聲部,下三聲部為整體弦樂隊。由譜面能夠看出,作曲家在歌謠式主題自然音階基礎上加入半音的處理,使此處形成音塊狀的音響體。弦樂各個聲部縱向具有的復雜性與半音性使整體音響呈現出具有行進感的音效,音型化的進行體現出作曲家不只是追求音樂的縱向不協和性,更多的是為了塑造出一種強而有力的音樂風格,塑造出一種貫穿全曲進行的音塊式音響體。
結語
綜上,坎切利七部交響曲的主題整體音域狹窄,多為二度音高運動線條,伴隨著簡潔單一的節奏型游走在樂隊的中低音區做陳述。同時,其交響曲作品的主題呈示多為獨奏形式,并選用獨特的音色承載主題性格,整體呈現為弱力度狀態下的訴說,體現出歌謠式主題的特征。
同時,由上述分析可知,坎切利對于縱向音高的設計所采用的并不是功能性和聲體系,而是在調中心與調式控制之下的一種音塊式音響體,在音塊式音響體呈現的過程中逐漸疊加,將其復雜化,這種非功能性和聲的處理方式是建立在歌謠式主題之上的。坎切利對縱向音高的設計是與其對歌謠式主題的設計一致的,體現出主題旋律與縱向和聲設計上的一體性。總而言之,坎切利非常重視主題旋律,并且將其特點鮮明的歌謠式主題提升到非常重要的地位,由此形成其多聲音高的構成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