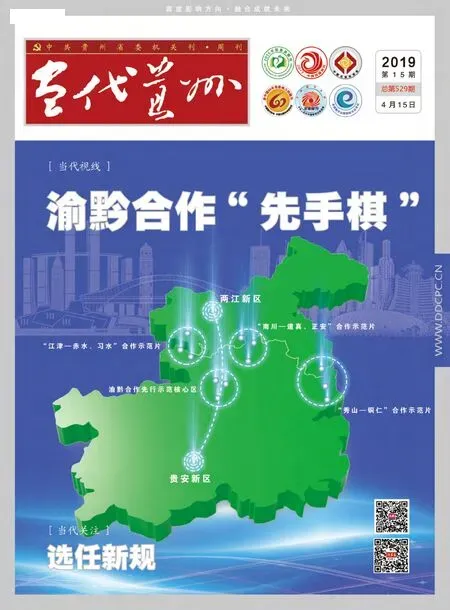大方漆的生態密碼
文_貴州日報當代融媒體記者 / 李思瑾
《大定縣志》記載:“漆樹生山間,其汁可髹物。”星宿、大山等鄉鎮是漆樹的主要生長區。當地百姓與漆樹之間,流淌著人與自然的和諧樂章。
大方縣星宿鄉的村子,名字大都和“樹”“山”有關:松樹村、漆樹村、棕樹村、云峰村、峻嶺村、麻嶺村……這兒的人一開口:“我是松樹的”“我是峻嶺的”或是“我在漆樹長大”。當地百姓不約而同“就地取材”,給村子名字鑲上了“樹”和“山”的印記。
或許他們心里,大山、樹木、村子、人,本就是不可分割的整體。
3月26日,記者走在大方縣星宿鄉的通村公路上,兩邊是起伏的群山,春草蔓發,樹林隨風沙沙作響。不少灰白色的樹干上都有好幾道寬約3厘米的刀口,當地村民告訴記者:“這就是我們的漆樹。”
漆樹是中國最古老的經濟樹種之一,漆液是天然樹脂涂料,素有“涂料之王”的美譽,色澤鮮艷,而且防腐防銹,耐酸耐高溫。
《大定縣志》記載:“漆樹生山間,其汁可髹物。”由于氣候、土壤等自然條件適宜于漆樹生長,星宿、大山、八堡、三元等鄉鎮為其主要生長區,品種有白楊皮、青杠皮、粉皮大木、燈臺大木、黃豆、椒葉、厚葉、柿花葉等。2017年開始,在以往種植了2600萬株的基礎上,大方又連片種植了8000畝,并建立了200畝漆樹育種基地。
大山割漆人
記者見到松樹村村民劉明合的時候,他正在路邊一處剛修建好的房子里做工,“現在不少村民都在農忙,卻是我們割漆人的‘農閑’季節,我就找點活干”。
幾個月以后,夏至到霜降4個多月的時間,因氣溫上升、陽光充足、水分蒸發快,才是割漆的好時候。
劉明合做工的房子周圍,也長滿了漆樹,枝頭冒出點點嫩芽。“過段時間可以采嫩葉,回家炒雞蛋,味道比香椿還要好。”
漆樹和割漆人之間似乎有種天然的默契。《本草綱目》記載生漆可入藥,卻“毒烈,畏漆人乃致死”,一般人對漆樹過敏,沾手即皮膚紅腫,渾身上下會長滿了“漆疙瘩”,而劉明合不會,他笑稱自己對生漆“免疫”。
許多野生的漆樹靠風把豌豆大的種子吹落在地,只有小部分生根長成樹,因此山中的野生漆樹不連片,獲得生漆是極其辛苦的過程,自古有“百里千刀一斤漆”的說法。割漆人的辛勞,也成就了聞名天下的大方漆器。
600年前,奢香夫人選擇用大方漆器作為獻給明太祖朱元璋的貢品;清道光年間,古老的大定府城內幾乎家家都會制作漆器。大方漆器名揚四海,與貴州茅臺、玉屏簫笛并稱“貴州三寶”。
儲存在漆樹體內的液體呈乳白色,割出來經過氧化后就迅速變成了褐色。分辨生漆好差的方法就是在攪拌中觀察,當地有句話叫“壩漆清如油,照見美人頭。搖動虎斑色,提起釣魚鉤”。劉明合解釋:“如果對照時可見人影,攪動時是虎斑色,提起時黏性很大,就是好漆。”
劉明合新建的房子里,最值錢的東西就是漆器:衣柜、床、臉盆架以及一些簡單的生活用品,都是自家漆的,用火熬去生漆水分,刷上兩三次再拋光。木衣柜、臉盆架已經用了幾十年,邊角幾乎無腐化,整體顏色還很好看。
與漆樹和諧相處
割漆的季節,劉明合總是起得很早,夜色還未完全褪去,天空中布滿星星點點,他所帶的割漆工具,有漆刀、刮片和接漆筒。“切刀不大,一寸長。”劉明合比劃著,“接漆筒是我自己用竹子做的,一筒能接3斤半。”
劉明合很有經驗:“首先要給漆樹開漆口‘放水’,隔幾天才正式開刀。第一、二道水分多,賣150元一斤,三道至六道質量最高,可賣到200—300元一斤。”
劉明合割漆的手藝,是跟著父親學的,而父親的手藝,則是跟著爺爺學的。
“割漆的時候不能割斷樹筋,刀口不能太長,如果割斷了,樹皮脫落,樹保不住水分,就會枯萎死掉。”“第一年割了這棵樹,要隔兩三年才能再去割同一棵樹。”爺爺這樣告誡父親,父親又轉達給劉明合。

每年夏至到霜降,正是割漆好時節。圖為大方縣星宿鄉松樹村村民劉明合在割漆。(吳學毅 / 攝)
劉明合還去山中挖得野生小樹苗,移栽到自家70多畝地里,十幾年光陰,小樹苗已長成大樹。“去年我割了自家地里的樹取漆,今年要換地兒了,要讓樹有恢復‘身體’的時間。”劉明合笑著說。
向自然索取,不可毫無節制。人類以善相待,自然才敬之以禮。
劉明合記憶里,割漆讓他家度過了最艱苦的年代。父親把漆液賣給供銷社,換回了家中需要的大米、燈草絨布料。時至今日,割漆也是劉家的重要生活來源,劉明合兒子在遵義讀大學,學費生活費都靠他割漆賺得,平均每年可賣得3萬多元,晴天天數多的夏季,收獲生漆多、質量好,還可以賣4萬多元。
像劉明合這樣的割漆人,星宿鄉還有幾十個。
“一到割漆季節,收漆人就找上門來了。”漆樹村的周孝德割漆,每年也能給他家增收一兩萬元。
當地村民與漆樹之間,流淌著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樂章。
讓非遺“生活化”
每年前往星宿鄉找劉明合、周孝德收購生漆的人里面,有位叫高焱的人,從距離星宿鄉50多公里的大方縣城而來。
高焱的父親,是國家級“非遺”項目“大方彝族漆器髹飾技藝”省級代表性傳承人、大方縣農民畫傳承人高光友。
畢節試驗區成立之初,高光友就進入大方縣國營漆器廠工作。后來,漆器廠因無法適應市場需求,漸漸失去生產和發展的動力。2013年,看到了市場需求的高光友成立了大方縣高光彝風漆器工藝制品廠,吸納了一批民間漆器藝人,專門從事大方彝族漆器工藝品設計、髹飾技藝,“目前工廠主要是訂單化生產”。
高焱與兄長高俊從小就在漆廠長大,受父親影響,大學畢業后,他們回到父親身邊,成為了新一代大方漆器的傳承人。
“大方漆器制品采用牛皮、棉、麻、綢、木等做胎,采用大方天然生漆為主要漆料。從胎坯制作到漆器形成,要歷經50多道工序、80多個生產環節,都需手工完成。”高俊告訴記者,其中最為巧妙的是皮胎隱花工藝,隱花的制作對生漆質量要求最高。“要用提煉成透明色的漆來做面漆,巧妙地把各種花紋隱襯在漆質與胎坯之間。隨著時間的推移,漆器里的花紋會越來越明亮,最長的要一年左右花紋才全部顯現出來。”
學設計的高俊正努力嘗試讓這項民族工藝走進尋常百姓家,近兩年,他開始設計開發小花瓶、茶具、碗、煙盒等生活用品。“你看,這個小巧的牙簽罐,就是用布胎做的,輕巧實用。父親常說,讓手工藝回歸生活,才能真正得到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