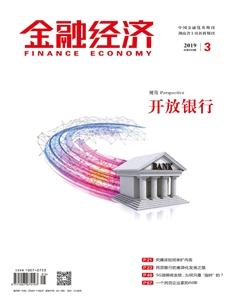雨后的彩虹不是“雷允上”
黃湘源
盡管我們并不排除商譽爆雷之后有可能會出現“雨后的彩虹”,但是,這和促使壞事變好事的“雷允上”是兩回事。離開了轉化機制奢談什么“雷允上”,這和耍無懶沒有什么兩樣。
商譽爆雷,已成當前股市的一大禍害。商譽爆雷之所以比較集中地出現在2018年上市公司年報披露之際,這同3年前高溢價并購的密集發生是分不開的。有關統計顯示,2013年和2014年間,A股上市公司的商譽還在4000萬元以下,從2015年開始,直到2018年三季報,商譽就已經節節攀升到6514.8億元、1萬億元、1.3萬億元和1.45萬億元。建立在估值泡沫基礎上的商譽,原本充其量不過就是一種利益交換或利益輸送。在此基礎上被計入收購方當期財報的商譽無論再怎么光鮮,與其說是未來收益的良好預期,還不如說是早晚要付的租金。不是不付,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都銷。在業績預期大多未達承諾預期的情況下,商譽爆雷現象的出現也就不足為怪了。
2018年11月中旬,證監會發布有關商譽減值的《會計監管風險提示第8號——商譽減值》時,似乎預計到了商譽爆雷的風險,但也只能從信息披露的角度去要求上市公司進行減值測試。盡管一些參加財政部商譽及減值咨詢會議的大部分會計準則咨詢委員都同時認為,隨著企業合并利益的消耗應將外購商譽的賬面價值減記至零,不過,會計準則委員會目前并沒有采納這個意見。這一方面是商譽減值成為一種無法避免之“天雷”的外部制度性原因,另一方面,業績調節機制的存在,也是成為某些上市公司在明知商譽減值無法避免的情況下要么不虧,要虧就干脆來個一次性虧個夠的內在利益動機。商譽爆雷和業績大洗澡就這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交織在一起,成為2018年年報披露期間一道獨特的“風景線”。在目前條件下,如果不能進一步推進更深層次的改革,從根本上消除商譽減值的風險,交易所再怎么用問詢的方法及時跟進監管,也未免是亡羊補牢,豈能不猶為晚矣!
一次性商譽減值雖然給當年年報業績造成了一個巨大的窟窿,但是,如果并沒有讓上市公司傷筋動骨,也不無可能會使來年的業績增長性變得分外的好看。不過,這種所謂的由壞變好,畢竟是相對而言的,未必是真正好的必然表現。如果造成上市公司業績乏善可陳的內在原因,除了商譽之外并沒有其他任何實質性的改變,那么,這種增長性也是缺乏可持續性的。說穿了,上市公司績效提高的根本出路還是需要寄托在自身主業的發展壯大上,商譽調節之類充其量不過是旁門左道,縱然可能討巧得了一時,但不可能討巧得了一世。
從市值管理的角度來看,市值的一次性較大減值,當然也有可能會為后市市值的相對大幅度回升拓寬一定的空間。不過,這同樣也不可能過于機械地一概而論。對于主業具有較好發展前景且公司治理基礎也較好的企業來說,現在的退一步,或有可能會為今后更好地進兩步,甚至更大的步伐。而對于業務凋零、業績大降、人心不振的企業來說,回光返照不過為利益中人提供一個減持套現跑路的機會罷了,投資者要想分享一點成長性紅利,則無異于水中撈月,癡心妄想。
目前,科創板即將開始試點注冊制,主板的發行制度改革在證監會新領導人的推動下,有可能會更順利地向注冊制更靠近一步。直接融資機制的市場化進步,不僅有可能極大地壓縮借殼上市的空間,同時,也必然將使得商譽越來越“英雄無用武之地”。這對于喜歡借殼資源炒作和估值泡沫之助來制造商譽者也許未必是好事,而對于上市公司來說則不失為由以往不務正業重新回歸實體經濟主業的一個轉軌變型的大好機遇。對于廣大投資者來說,這更是在投資理念上撥亂反正,正本清源,不失為一堂生動的風險教育課。
壞事固然可以變好事。但是,這種轉變不僅需要一定的時機,也是需要有一定條件的。用發展的觀點看問題,把希望寄托在商譽減值,就同當初把希望寄托在商譽增值上一樣的靠不住。弄得不好,商譽爆雷非但不可能給上市公司或投資者帶來一個“雷允上”,反而可能會被炸了個粉身碎骨。就此而言,靠商譽還不如不靠為好。不過,如果能夠把關注商譽的心思轉移到關注主業和促進改革上,更好地在發掘和創造公司價值上下功夫,則又何愁發現不了投資價值的雨后彩虹呢?說到底,雨后的彩虹不是商譽爆雷給爆出來的,而是雨后的太陽給映射出來的。而這個給市場帶來彩虹的太陽,無論如何也決不可能是什么商譽或商譽減值,而必然是在改革的促進和推動下,伴隨著上市公司治理改善和業績提高所帶來的價值創造和價值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