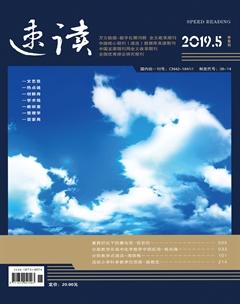童真對(duì)比下的善與惡
伍彩欣
在人們的潛意識(shí)里,兒童常常是單純無(wú)辜,象征著希望的代表,因此在戰(zhàn)爭(zhēng)題材的電影中精心塑造的兒童形象往往有著特別的作用和意義。相比于成人形象,將兒童放置于戰(zhàn)爭(zhēng)提供的絕境下更容易觸動(dòng)人心,使觀者在震撼與憤怒的激情下,自覺(jué)進(jìn)入對(duì)戰(zhàn)爭(zhēng)的反思與對(duì)人性的深入思考。
馮小寧在1999年拍攝的電影《黃河絕戀》是一部紅色主旋律電影,與以往的戰(zhàn)爭(zhēng)愛(ài)情片不同,創(chuàng)造者運(yùn)用兒童的純真形象去貼合大眾心理,努力將愛(ài)國(guó)主義情懷滲透到每一個(gè)中國(guó)人的精神世界。用孩童的純真對(duì)比戰(zhàn)爭(zhēng)中的善與惡,在炮火威脅下寧死不屈的中華精魂更是真實(shí)地觸動(dòng)了每一位觀眾的內(nèi)心。
電影的開頭是暮年歐文帶著孫女故地重游,看著浩浩蕩蕩的黃河水隨著流光的消逝奔涌入海,他想起了年輕時(shí)在異國(guó)度過(guò)的崢嶸歲月。一張張泛黃的黑白照片被翻開,隨著低沉舒緩的音樂(lè)響起,一段塵封的往事被娓娓道來(lái)。那是中日戰(zhàn)爭(zhēng)時(shí)期八路軍一行戰(zhàn)士護(hù)送美國(guó)飛行員歐文去往根據(jù)地的故事,逐漸激昂的管弦樂(lè)奏響,猛烈的記憶如潮水般涌來(lái),序幕在一場(chǎng)回憶中緩緩拉開。
再憶起這段始終伴隨的犧牲和離別的殘酷經(jīng)歷,不知他最先想起的是誰(shuí)?是與他相愛(ài)的安潔,是為他犧牲的黑子,還是那些在逃亡過(guò)程中給予他幫助的中國(guó)人民呢……在觀影結(jié)束后,我的腦海里一直揮之不去的只有在炮火中孩子們童稚的影子。
那在炮火中依然保有的童真仿佛是穿行在空中綿綿不絕的白云,不斷涌出新的感動(dòng)和共鳴,穿透我的心扉,帶我走進(jìn)連自己也無(wú)法說(shuō)清楚的難以釋懷的情景,觸動(dòng)心底那根柔情的弦。
在歐文的回憶里,第一個(gè)出現(xiàn)的是救了他一命,卻不幸被炮彈炸死的放羊娃。歐文在炸毀了日本軍艦后開著搖搖欲墜的飛機(jī)在神州大地上穿行,最終飛機(jī)懸掛在懸崖上。歐文差點(diǎn)墜入深淵,在這千鈞一發(fā)之際,一個(gè)放羊的孩子把他救出。放羊娃黑糊糊的臉和歐文白色的皮膚構(gòu)成了巨大的反差,他們面對(duì)面大笑,東西方文明就此相遇。
歐文想用相機(jī)記錄下放羊娃善良淳樸的樣子,當(dāng)他按下快門的那一刻,男孩的笑容被永遠(yuǎn)定格在被飛機(jī)轟炸前的一瞬間。一枚炮彈將一切化成了泡影,只留下了那條黯淡無(wú)光的長(zhǎng)命鎖。這樣無(wú)辜善良的孩童在生命的最后一瞬間還在微笑,他不知發(fā)生了什么,就這樣失去了生命。
歐文的善引領(lǐng)他來(lái)到中國(guó)參與作戰(zhàn),放羊娃的善則以救命的方式回報(bào)了這份恩情。可善良在戰(zhàn)爭(zhēng)中卻難以避免地受到炮火的殘酷摧殘,放羊娃的犧牲使善惡的對(duì)比更為明顯,從而引發(fā)人們深深的同情和惋惜。
《黃河絕戀》始終以死亡貫穿全片,尤其是無(wú)辜孩童的死亡,以此突顯戰(zhàn)爭(zhēng)的殘忍和邪惡。當(dāng)歐文一行人跋山涉水地來(lái)到村莊,卻發(fā)現(xiàn)那里早已被洗劫一空。鏡頭對(duì)準(zhǔn)村莊里死去的百姓,尸橫遍野、血腥殘忍,最令人心疼的是那些嗷嗷待哺的孩子,他們?cè)谶€沒(méi)有好好看到這世界時(shí)就已經(jīng)在發(fā)不出聲音地哭喊中走向死亡。這里導(dǎo)演特地以孩子的死亡渲染屠殺,暴露出日本鬼子的殘忍罪行。
成人世界的紛爭(zhēng)引來(lái)了戰(zhàn)爭(zhēng)這個(gè)暴力機(jī)器的瘋狂碾壓,對(duì)此毫無(wú)責(zé)任的兒童也不幸卷入其中,成為戰(zhàn)爭(zhēng)最無(wú)辜的受害者。弱小無(wú)辜的兒童死亡與殘酷暴烈的戰(zhàn)爭(zhēng)打響,這兩個(gè)爭(zhēng)鋒相對(duì)的概念放在同一個(gè)文本中發(fā)生交集,觀眾由此被它們相互碰撞產(chǎn)生的沖擊力帶入激烈的情感體驗(yàn)中,沉浸于對(duì)悲劇,人性,人情,人道主義乃至人類命運(yùn)的思考之中。
花花在電影中出場(chǎng)時(shí)間最長(zhǎng)的兒童,給觀眾帶來(lái)了最深的感動(dòng)。她穿著碎花棉襖,兩條垂肩辮,圓圓的臉蛋始終帶著干凈澄澈的笑容,這是黃土地上典型的女童形象,天真淳樸。懂事的她會(huì)滿眼笑意地喂洋大大吃蝎子,調(diào)皮的她會(huì)小心翼翼地拿蝎子捉弄日本鬼子,花花用她孩童的純真給戰(zhàn)爭(zhēng)帶去了一份溫情和安慰。
花花是電影中“小英雄”式的人物,是正義一方既弱小又偉大的代言人。被日本人劫持的花花撕心裂肺地哭喊著叫爸爸,可黑子告訴花花,爸爸是八路,不能聽鬼子的話把洋大大送過(guò)去,于是,幼小的花花咬破嘴唇?jīng)]有再哭出一聲。在面對(duì)生命威脅時(shí),孩子表現(xiàn)出的無(wú)畏和堅(jiān)強(qiáng)最能觸動(dòng)觀眾的內(nèi)心,這是精神的力量感和昂揚(yáng)之美,這是在用兒童展示出中華兒女面對(duì)侵略者寧死不屈的抗?fàn)幘瘛?/p>
在影片中,生存與人格尊嚴(yán)是中西方文明的主要沖突。面對(duì)日軍的侵略,中國(guó)人民奮起抵抗,始終秉承著“士可殺不可辱”的舍身主義,在死亡面前寧死不屈,民族尊嚴(yán)重于一切。西方的歐文有著與中國(guó)人完全不同的生存觀念,在死亡面前,生存始終是第一位的,活著就是一種勝利。但歐文看到花花在面對(duì)死亡威脅時(shí)的那種民族激蕩不屈的精神力量改變了他的利己主義。他逐漸的接受中國(guó)的觀念之后又從心理上給予了認(rèn)可,他選擇把生死置之度外,冒著生命危險(xiǎn)去迎救花花。可見,在戰(zhàn)爭(zhēng)中兒童所表現(xiàn)出的生存大義深深地植入進(jìn)歐文的心理,更扎根于我們每一個(gè)中國(guó)人的心中。
故事的最后,只有花花和歐文活了下來(lái)。在一系列激烈的沖突中,不斷的流血和犧牲更能使觀眾震撼于矛盾解決時(shí)的悲壯。正如江流入海一般,所有沖突矛盾終將匯聚并升華為抗日背后的民族大義。
越是絕望、殘酷、悲壯的故事,越能給人帶來(lái)希望,越能激勵(lì)我們活下去。兒童象征著新的希望,最后花花的存活證明戰(zhàn)爭(zhēng)的漫長(zhǎng)黑夜總會(huì)結(jié)束,中華民族就如奔騰的黃河水滔滔不絕,生生不息。
影片以老年的歐文帶著自己的孫女回到黃河邊,把一張張珍藏已久的舊照片放入波濤洶涌的黃河水中結(jié)束,兩人飽含熱淚地望著奔騰的黃河水,呼嘯著的黃土地,仿佛在參加一場(chǎng)盛大的祭奠儀式。
歐文的孫女可以被看做是未經(jīng)歷戰(zhàn)爭(zhēng)的后代,是新時(shí)期兒童的象征。他們有幸出生在和平年代,沒(méi)有炮火的威脅,不用經(jīng)歷生死的抉擇,但始終不能忘記戰(zhàn)爭(zhēng)曾經(jīng)給人類帶來(lái)的傷害,更不能忘記那些為了守衛(wèi)家園寧死不屈的先烈們。
兒童的形象在這部電影的運(yùn)用是非常成功的,用放羊娃微笑著的死亡表現(xiàn)戰(zhàn)爭(zhēng)對(duì)兒童的摧殘,用村莊孩子們血肉模糊的鮮紅來(lái)展現(xiàn)戰(zhàn)爭(zhēng)的邪惡殘暴,用花花面對(duì)威脅的堅(jiān)強(qiáng)映襯中華兒女寧死不屈的精魂,歐文孫女以新時(shí)期兒童的身份回首往事悼念這段抗?fàn)幍膷槑V歲月……這些被刻畫得有血有肉的孩子們用稚嫩的童真映襯出人性的善與惡,激發(fā)了觀眾對(duì)戰(zhàn)爭(zhēng)的巨大的震驚與悲憤,從而喚醒人們對(duì)于戰(zhàn)爭(zhēng)的深刻反省以及對(duì)和平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