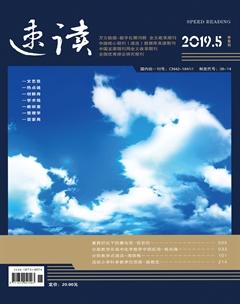懷抱希望去“流浪”
劉紅會 張盼
摘? 要:《流浪地球》這部電影在2019年春節檔一經上映,便迅速成為春節檔中的一匹黑馬,票房和口碑雙贏,更是引起了一股“科幻風”。硬科幻的敘事方式與感人淚下的脈脈親情既具有中國特色,同時也開啟了中國科幻電影的新紀元。
關鍵詞:中國科幻電影元年;“流浪”;希望
2019年春節檔有8部影片競爭,其中寧浩導演的《瘋狂的外星人》上映之前已經被業內人士保守估計取得30億的票房,其它影片如《飛馳人生》《新喜劇之王》等也被業內人士看好。影片《流浪地球》一開始在宣傳、預售等方面,均落后于以上幾部影片,導演及制作團隊也并沒有抱很高的期望,他們的目標是票房能達到12億,可以回收成本即可。但是1月28日在北京首映后,口碑迅速發酵,非常難得地獲得了科幻作家和科幻導演的認可。
劉慈欣的“磁粉”們和中國觀眾評論說:“在觀影過程中,一直掩飾不住內心的震驚與自豪,時刻提醒自己,這真的是中國自己拍出來的科幻片。”當然,作為《流浪地球》監制的劉慈欣看完片子之后,也難掩內心的激動之情,說到:“從《流浪地球》開始,中國科幻電影正式起航了。”《流浪地球》無論在制作層面上還是故事敘事上幾乎能與好萊塢大片并駕齊驅,甚至影片中獨具特色的中國式親情場面更是彌補了科幻電影慣有的“零度敘事”的冰冷感。《阿凡達》導演卡梅隆看完說:“希望《流浪地球》的太空之旅順利,也祝中國的科幻電影之旅好運。
新時代的觀眾口味更加刁鉆,眼光更加毒辣,很少再出現盲目追劇追影的狀況。一部叫好又叫座的影視劇必須拿出它本身的誠意方能打動觀眾。創作者也必須有自己獨到的見解與深入骨髓的創作激情方能引起觀眾的共鳴。就如劉慈欣所言,目前的文化市場處于一種雙盲狀態,“要想實現文藝轉型,需要知道大眾的文化需求是什么。我們對大眾的文化需求存在誤解,處于一種‘雙盲狀態,大眾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文藝工作者也不知道大眾需要什么。”觀眾并不確定自己需要的是科幻片,還是搞笑片,他們唯一確定的是自己需要的是高品質的上乘佳作。題材萬千,搞笑片也好,文藝片也罷,能夠打動他們,能夠引起他們共鳴的方是好的作品。猶如低成本制作的《我不是藥神》,日常題材,教科書級別敘述手法與表演方式,一經上映,便取得了極好的口碑與票房。好的作品,不在乎題材,在乎它的誠意。
放映結束時,觀影的人都有些淚目。電影本身的質量無需質疑,但更多的是影迷們對于國產科幻片的感慨。畢竟,中國的科幻片,始終處于一種“流浪”的狀態。一個成功的大型科幻片,與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經濟發展、劇本創作、國民整體文化素質等都密切相關。《流浪地球》拍攝中間遇到了資金鏈的中斷,畢竟沒有多少投資人愿意蹚國產科幻這潭渾水。資金不足,請不起厲害的特效團隊,永不放棄的劇組就著重影片內容,反復打磨影片的邏輯思維與細節,讓情感與特效雙線并軌,一舉打破傳統的好萊塢以特效取勝的科幻大片。郭帆導演說:“好的電影標準是讓觀眾能從電影里看到自己,找到共同的情感。”吳京飾演的父親以犧牲自己換來了自己兒子與岳父的去往地下城的身份;面對生死時的各色人群的不同選擇,有的選擇開槍自殺,有的選擇勇敢面對;劉啟青春期的沖動與冒險以及經歷磨難后的成長;《流浪地球》的強大之處在于,影片設定雖然在科幻世界,卻都能對應到現實中的人。
《流浪地球》中有句很重要的臺詞,就是“我們選擇希望”。在《流浪地球》中希望是被這樣寫的:“我們必須抱有希望,這并不是因為希望真的存在,而是因為我們要做高貴的人。在前太陽時代,做一個高貴的人必須擁有金錢、權利或才能,而在今天只要擁有希望,希望是這個時代的黃金和寶石,不管活多長,我們都要擁有它!”就如吳京在影片中說過的一句話:“有人的文明才叫做文明。”災難片的內核說到底,還是愛。就如每一部打動我們的小說,每一部感動我們的影片,或者說每一首讓我們單曲循環的歌曲,說到底都是與感情有關,親情、友情、愛情莫不過如此,將科技與人類情感的矛盾放大,這樣,災難來臨時,有希望才不會絕望。
中國科幻電影的拍攝歷程同樣也需要“希望”。中國民眾中一直存在一股消極論調,認為中國依然甚至永遠沒有能力制作出一部屬于自己的科幻大片。但是,《流浪地球》的創作團隊正是抱著這樣的情懷,心生希望,才在重重的困難中堅持下來。2001年,在《球狀閃電》后記中,劉慈欣就曾說過:“中國的科幻作者創造自己世界的欲望并不強,他們滿足于在別人已經創造出來的世界中演繹自己的故事。”他也曾這樣評價郭帆導演:“他對科幻有情懷,而且對科幻的理解,包括對科幻如何與電影結合的理解很深,特別是一個很宏大的科幻設計如何把它和中國的文化、中國的國情結合起來,他有很深的見解。”
盡管《流浪地球》作為中國科幻電影的高起點,依然存在旁白出戲等瑕疵。但是,我們依然希望,它猶如一陣強心劑一樣注入中國的電影市場,能夠激蕩出更多更好的科幻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