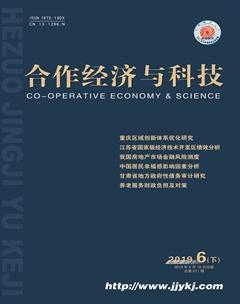中國居民幸福感影響因素分析
董秦男
關鍵詞:Ordered Logit;居民幸福感;邊際效應
中圖分類號:F126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9年3月13日
一、問題的提出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2010年起我國GDP總量已經超過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與此同時人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較大的改善和提升。在經濟取得重大成就之后,黨和政府開始更多地關注人類社會最基本的問題——幸福。2012年11月,習近平指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這代表了中國領導層對國民幸福的關注與重視。
早期的幸福研究主要集中在哲學、心理學、社會學角度,隨著幸福經濟學的興起,幸福的測量及其影響因素被越來越多的經濟學者所關注。盡管在現代經濟學中,經濟增長或收入增長仍是經濟研究的核心命題,但它們可能并不是目標本身,而在更大程度上表現為實現人們“幸福”的手段,“幸福”才是人們最終所追求的目標。而在經濟和國民收入快速增長的同時,中國居民的幸福感表現并不同步。據調查,從1990年開始到2005年,中國人的生活滿意度呈下降趨勢,2005年之后出現回升,整體上形成一條U形曲線。據世界價值觀調查(簡稱WVS)結果顯示:1990~2007年,中國居民的平均幸福感由1990年的7.29下降到2001年的6.63;2007年回升到了6.76,但仍遠遠低于1990年的水準。由此可見,幸福作為一種反映人們生活滿意狀況的指標,要受到諸多復雜因素的影響,不僅受到經濟因素的影響,而且還要受到社會因素以及心理因素的影響,從而表現出非單調的變化趨勢。據聯合國發布的《世界幸福報告》顯示,在156個受調查的國家中,2016年中國幸福感排名83位,2017年排名79位;近年來隨著政府對民生問題的關注以及相關政策的實施,我國國民幸福感在逐漸提升,但這一表現卻與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并不匹配。因此,有必要進一步研究影響國民幸福感的深層次原因。
二、文獻回顧
近年來,隨著幸福經濟學的興起,國內許多學者利用面板和截面等微觀數據對幸福感進行研究。從國內已有的研究文獻來看,大多數文獻使用OLS回歸或有序離散變量回歸方法進行研究。如魯元平和張克中(2010)利用WVS的中國部分,運用有序離散模型研究了經濟增長和親貧式支出對中國居民幸福感的影響,發現經濟增長并不能帶來國民幸福感的提升,而以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構成的親貧式支出對國民幸福感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同樣運用WVS中國部分數據,溫曉亮等(2011)發現在影響主觀幸福感的因素中,相對收入和社會失范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較大,人口學變量中的性別、年齡、健康、婚姻、教育等都對主觀幸福感有影響。劉宏等(2013)利用2009年中國家庭營養健康調查數據(簡稱CHNS2009),使用Ordered Probit計量模型研究了永久性收入和房產財富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發現相比于當期收入,永久性收入和房產財富是主觀幸福感的重要影響因素,但兩者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存在城鄉差異。亓壽偉、周少甫(2010)基于CHNS數據庫研究了一組特殊群體——老年人的幸福感現狀,運用Ordered Logit回歸模型,他們發現收入增加對老年人的主觀幸福感有正向顯著影響,而收入差距的影響并不顯著;健康對老年人的主觀幸福感有明顯的正向影響;醫療保險對老年人的主觀幸福感存在顯著正向影響。但隨著區域分布及城鄉分布的變化,老年人的主觀幸福感存在差異。何立新和潘春陽(2011)運用有序離散變量回歸方法,綜合2005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數據(CGSS2005)和中國經濟數據庫(CEIC2005)數據發現,機會不均和收入差距都對主觀幸福感產生負向影響,但機會不均對居民主觀幸福感的負向影響對低收入者和農村居民的損害更為嚴重,而收入差距顯著損害了低、中低和高收入階層的主觀幸福感,對中上收入階層的影響并不顯著。閏丙金(2012)、王鵬(2011)、陳剛和李樹(2013)、李清彬和李博(2013)等學者使用CGSS2006和不同計量方法研究主觀幸福感影響因素。閏丙金(2012)運用ordered logit研究了收入、社會階層認同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發現收入變化、收入公平、社會階層認同狀況對主觀幸福感都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且這種影響有顯著的城鄉差異,收入對城鄉居民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并不顯著。通過梳理發現,國內外學者對于主觀幸福感的研究多采用Ordered Logit模型進行實證研究。本文參考前人做法繼續使用該模型,并從其他角度對此問題進行進一步探究。
三、研究對象和方法
(一)研究對象。本研究的樣本來自于北京大學中國科學調查中心主持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成人問卷2016年公開數據。CFPS數據包含針對個人基本信息的各種指標如年齡、性別、戶口狀況等,也包含居民幸福感調查的模塊。并且該數據是目前可獲得的CFPS最新數據,能夠更為全面準確地反映目前的時代特征。根據本研究需要對所有數據進行整理和篩選,剔除了模型所使用變量問卷選項中不符合、不清楚等回答的樣本,獲得有效問卷9,694份。

(二)研究變量
1、被解釋變量。研究使用CFPS數據主觀態度模塊中對自己生活的滿意度調查的結果作為被解釋變量。原題目為“您覺得自己有多幸福?”問卷中題目編號為“qn12012”,該變量的取值范圍為1~5,其中“1”表示不幸福,“5”代表非常幸福。
2、解釋變量。本研究關注的自變量包括四個方面:年齡、家庭成員數、健康情況和工作總收入。并將性別、戶口和婚姻狀況作為調節變量。
與年齡有關題目編號為“cfps_age”,問卷問題為2016時受訪者的年齡,是一個近似連續變量。與家庭構成情況有關的題目編號為“fml2016_count”,代表家庭成員人數。健康狀況采用問卷中編號為“pq201”的問題結果,原問題是“評價自己的健康狀況”,回答范圍從1到5,越低代表健康程度越佳。收入情況采用編號為“income”問題結果,原問題為“所有工作總收入”,近似連續變量。與婚姻狀況有關題目編號為“qea0”,問卷回答分為五種,分別是未婚、在婚、同居、離婚和喪偶。為了簡化模型,將未婚、離婚和喪偶定義為單身人群,再婚和同居定義為非單身人群,建立新變量“single”來表示,single為“1”代表單身人群,為“0”代表非單身人群。與戶口有關問題編號為“pa301”,問卷中1代表農業戶口,3代表非農業戶口,因為模型需要進行重新編號,定義二分變量“famer”,“1”表農村戶口,“0”代表非農戶口。與性別有關的題目編號為“cfps_gender”,原問卷中“1”代表男性,“0”代表女性。本研究的主要研究變量具體含義及統計分析見表1。(表1)
(三)模型設計及結果
1、模型設計。本文假定被解釋變量由下式決定:
2、樣本回歸結果及分析。本文利用STATA對樣本進行Ordered Logit回歸分析,并展示了各個變量對居民幸福感的影響。在回歸分析之前,對模型的多重共線性進行檢驗,結果顯示各個變量的VIF都小于2,說明不存在明顯的多重共線性。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表2)
通過對以上回歸結果的分析得出以下結論:在控制變量不變的前提下,解釋變量對居民幸福感的影響基本顯著,說明這4個維度是影響居民生活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其中年齡、健康和收入最為顯著。此外,這幾個維度與居民生活幸福感呈現正相關關系,即年齡的增長、健康的提高、收入的增加和家庭成員的豐富能顯著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如果政府能夠從后三個維度出發,那么人民的生活幸福感就會得到顯著改善。
從年齡、健康、家庭規模和收入對幸福感程度的影響來看,如果年齡增加一歲,那么居民的幸福感將提升2.25%,同時居民認為自己“非常不幸福”、“比較不幸福”和“中性”的概率水平將分別下降0.11%、0.19%和0.23%;如果家庭成員增加一位,那么居民的幸福感將提升2.23%,同時居民認為自己“非常不幸福”、“比較不幸福”和“中性”的概率水平將分別下降0.12%、0.19%和0.24%;如果居民的健康程度增加一個檔次,那么居民的幸福感將提升36.51%,同時居民認為自己“非常不幸福”、“比較不幸福”和“中性”的概率水平將分別下降1.86%、3.02%和3.79%;如果收入增加1萬元,那么居民的幸福感將提升1.38%,同時居民認為自己“非常不幸福”、“比較不幸福”和“中性”的概率水平將分別下降0.07%、0.11%和0.14%。
從不同幸福感的邊際效果來看,年齡、健康、家庭規模和收入對居民的生活幸福感均有顯著影響。從居民感到“非常不幸福”這一程度出發,年齡、健康、家庭規模和收入(每萬元)的提升將降低居民感到“非常不幸福”的程度,其提升比例分別為:0.11%、0.12%、1.86%和0.07%,且均為正相關。在居民感到“比較不幸福”這一程度上,改善比例分別為:0.19%、0.19%、3.02%和0.11%,也均為正相關。在居民幸福感為“中性”這一程度上,上述因素促使幸福感增加的比例分別為:0.23%、0.24%、3.79%和0.14%。由此可見,無論是哪個級別的幸福感水平,健康的改善對于提升居民生活幸福感的影響最大。
從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來看,被訪者個人特征中的性別、戶口和是否單身三個因素中只有性別影響較為顯著。在性別這一控制變量中,回歸系數為-0.3159,表明男性的幸福感低于女性,這與已有文獻的研究結果是一致的。從性別對幸福感的影響來看,同樣條件下,女性相對于男性認為自己“非常不幸福”、“比較不幸福”和“中性”的概率分別要高1.61%、2.61%和3.28%。而是單身和戶口對居民幸福感的影響并不顯著,說明在居民對自我幸福程度的認定中,是否單身和是否為農業戶口并非主要的考慮因素。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本文根據CFPS2016調查數據,使用Ordered Logit模型研究了年齡、健康、家庭規模和收入對幸福感程度的影響,根據分析得出以下結論:年齡、健康、家庭規模和收入對居民幸福感均有正向的影響,且影響都較為顯著。其中健康對于居民幸福感的影響程度最大。同時,性別對幸福感也有顯著影響,同樣條件下女性比男性更容易獲得幸福感。
通過以上研究,本文認為當前正處于轉型期的中國不應只將經濟增長、收入增加作為國家追求的終極目標,而應該在經濟取得一定成就后,逐漸將視角轉移到增強國民實際幸福感這一問題上。而提高國民幸福感除采取措施提高收入外,改善醫療、教育、就業等民生問題顯得十分重要。另外,由于個體之間對于幸福的感受存在異質性,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應該做到有差別且具針對性,應該更多關注弱勢群體和幸福感低的群體,提升他們的幸福度,以維護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可持續性發展。
主要參考文獻:
[1]羅楚亮.城鄉分割、就業狀況與主觀幸福感差異[J].經濟學季刊,2006(3).
[2]Easterlin,R A,R Morgan,M Switek,W Fei.Chinas Life Satisfaction 1990~2010[J].University of California,Working Paper,2012.
[3]魯元平,張克中.經濟增長、親貧式支出與國民幸福——基于中國幸福數據的實證研究[J].經濟學家,2010(11).
[4]溫曉亮,米健,朱立志.1990~2007年中國居民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因素研究[J].財貿研究,2011(3).
[5]劉宏,明瀚翔,趙陽.財富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研究——基于微觀數據的實證分析[J].南開經濟研究,2013(4).
[6]亓壽偉,周少甫.收入、健康與醫療保險對老年人幸福感的影響[J].公共管理學報,2010(1).
[7]何立新,潘春陽.破解中國的“Easterlin論”:收入差距、機會不均與居民幸福感[J].管理世界,2011(8).
[8]閏丙金.收入、社會階層認同與主觀幸福感[J].統計研究,2012(10).
[9]王鵬.收入差距對中國居民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分析——基于中國綜合社會調查數據的實證研究[J].中國人口科學,2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