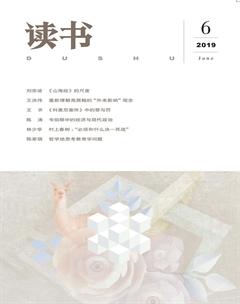村上春樹:“必須和什么決一死戰(zhàn)”
林少華
村上春樹的長(zhǎng)篇新作《刺殺騎士團(tuán)長(zhǎng)》于二0一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在東京出版。兩個(gè)月后的四月二十五日就出版了另一本書《貓頭鷹在黃昏起飛》。聽書名,似乎村上又出了一部長(zhǎng)篇。其實(shí)這是一本訪談錄。問(wèn)話者是日本年輕女作家川上未映子,回答者自然是村上春樹。
那么,這本訪談錄為什么叫這樣一個(gè)容易讓人誤解為小說(shuō)作品的名字呢?這當(dāng)然和當(dāng)時(shí)剛出版的《刺殺騎士團(tuán)長(zhǎng)》有關(guān)。讀過(guò)這部大長(zhǎng)篇的讀者想必記得第五章關(guān)于閣樓里的貓頭鷹的描寫:“一只灰色的小貓頭鷹靜悄悄躲在房梁上面的暗處。看樣子正閉目合眼地睡覺(jué)。我關(guān)掉手電筒,為了不驚動(dòng)對(duì)方,特意在離開些的地方靜靜觀察那只鳥。近距離看貓頭鷹是頭一次。較之鳥,更像生了翅膀的貓。美麗的生物!”關(guān)于這只貓頭鷹,川上未映子在這本訪談錄中認(rèn)為它和《奇鳥行狀錄》中的擰發(fā)條鳥具有同樣意義和功能,都是必不可少的角色。這是因?yàn)椋骸俺綍r(shí)態(tài)和邏輯的故事,其內(nèi)部需要有不同于神的視角,需要什么也不參與的超越性存在,而貓頭鷹恰恰是那樣的存在。”
川上未映子同時(shí)指出:“一如密涅瓦的貓頭鷹,故事中的貓頭鷹起飛也總在黃昏時(shí)分。”這里可能需要多少解釋一下的是,密涅瓦(Minerva)是古羅馬神話中的智慧女神(相當(dāng)于古希臘神話中的雅典娜)。她身旁的貓頭鷹是思想和理性的象征,在黃昏中起飛就可以看見白天發(fā)生的一切,可以追尋其他鳥兒在光天化日下飛行的蹤影。黑格爾曾用密涅瓦的貓頭鷹在黃昏起飛比喻哲學(xué),意在說(shuō)明哲學(xué)是一種沉思、反思的理性。川上未映子則用來(lái)比喻村上久久逼視的動(dòng)筆創(chuàng)作長(zhǎng)篇的最佳時(shí)分——是黃昏時(shí)分還是黎明時(shí)分無(wú)由得知——此其時(shí)也!
不過(guò)村上似乎對(duì)川上未映子關(guān)于貓頭鷹的解讀不以為然。他說(shuō)《刺殺騎士團(tuán)長(zhǎng)》之所以有貓頭鷹出現(xiàn),是因?yàn)樗茉缫郧白〉姆孔拥拈w樓里有一只貓頭鷹,“可愛得不得了。從那時(shí)開始,就心想遲早非讓貓頭鷹出現(xiàn)在小說(shuō)里不可”。從中也不難看出兩人問(wèn)答之間時(shí)而有之的錯(cuò)位。村上在書的“后記”中指出:川上未映子把過(guò)去從未有人問(wèn)過(guò)的那類問(wèn)題迎面砸來(lái),并且毫不膽怯地從各個(gè)角度反復(fù)提問(wèn),一直問(wèn)到心滿意足為止。“而在一個(gè)個(gè)回答那樣的提問(wèn)當(dāng)中,我在自己心中發(fā)現(xiàn)了我本身迄今從未想到的意味和風(fēng)景。”而那樣的意味和風(fēng)景,借用剛才的比喻,未嘗不可以說(shuō)是密涅瓦的貓頭鷹在黃昏起飛后看見的許許多多。于是——我猜測(cè)——川上、村上兩人一拍桌子:OK,書名就叫“貓頭鷹在黃昏起飛”!
一
這本訪談錄收錄了四次訪談,除了第一次(第一章),其他三次都是在村上剛寫完《刺殺騎士團(tuán)長(zhǎng)》后進(jìn)行的,所以難免較多涉及這部最新長(zhǎng)篇,原作腰封廣告詞即是“《刺殺騎士團(tuán)長(zhǎng)》誕生秘話”。
第二次采訪一開始,川上未映子就問(wèn)書名從何而來(lái)。村上回答某一天——不知是走路時(shí)候還是吃飯時(shí)候——“刺殺騎士團(tuán)長(zhǎng)”忽地一下子浮出腦海,就好像從看不見的地方生出云絮,突如其來(lái),卻再也揮之不去。隨即打定主意,那么就因勢(shì)利導(dǎo)地寫一部名叫“刺殺騎士團(tuán)長(zhǎng)”的小說(shuō)好了。村上回憶,《海邊的卡夫卡》和《奇鳥行狀錄》書名的產(chǎn)生也是如此,都是由書名啟動(dòng)的。
除此以外,《刺殺騎士團(tuán)長(zhǎng)》還有兩個(gè)因素:《二世緣》和小說(shuō)第一章第一段。《二世緣》是日本江戶時(shí)期作家上田秋成(一七三四至一八0九)寫的類似《聊齋志異》的志怪小說(shuō)《雨月物語(yǔ)》中的一篇。故事主人公夜半看書,聽得院子一角不時(shí)有類似鉦的聲音傳來(lái)。第二天請(qǐng)人挖開一看,里面有一口石棺,石棺里有一具木乃伊。雖然渾身干得像魚干,但手仍一個(gè)勁兒敲鉦不止。后來(lái)主人公給木乃伊穿衣喝水喂食。一來(lái)二去,木乃伊恢復(fù)得和普通人沒(méi)什么兩樣,娶妻生子,喝酒吃肉,所謂“開悟僧”氣象全然無(wú)從談起。前世記憶也蕩然無(wú)存,只知道經(jīng)營(yíng)今世的世俗生活。村上說(shuō)他很早就喜歡《二世緣》這個(gè)故事,一直想以此為主題寫點(diǎn)什么。問(wèn)題是,“二世緣”和“騎士團(tuán)長(zhǎng)”根本捏不到一起。如此困惑之問(wèn),村上鬼使神差地寫下了第一章的開頭:
那年五月至第二年的年初,我住在一條狹長(zhǎng)山谷入口附近的山頂上。夏天,山谷深處雨一陣陣下個(gè)不停,而山谷外面大體是白云藍(lán)天——那是海上有西南風(fēng)吹來(lái)的緣故。風(fēng)帶來(lái)的濕乎乎的云進(jìn)入山谷,順著山坡往上爬時(shí)就讓雨降了下來(lái)。房子正好建在其分界線那里,所以時(shí)不時(shí)出現(xiàn)這一情形:房子正面一片明朗,而后院卻大雨如注。起初覺(jué)得相當(dāng)不可思議,但不久習(xí)慣之后,反倒以為理所當(dāng)然。
周圍山上低垂著時(shí)斷時(shí)續(xù)的云。每當(dāng)有風(fēng)吹來(lái),那樣的云絮便像從前世誤入此間的魂靈一樣為尋覓失去的記憶而在山間飄忽不定。看上去宛如細(xì)雪的白亮亮的雨,有時(shí)也悄無(wú)聲息地隨風(fēng)起舞。差不多總有風(fēng)吹來(lái),沒(méi)有空調(diào)也能大體快意地度過(guò)夏天。
《貓頭鷹在黃昏起飛》中特別談起這兩段話。村上說(shuō)這開頭兩段是某個(gè)時(shí)候早已寫好的,沒(méi)什么目的,同樣突如其來(lái)。寫完一直以“那年五月”為標(biāo)題粘在電腦界面的一角置之不理。某日忽然心生一念:“啊,這么開頭寫文章好了!”寫完半年時(shí)間里,“時(shí)不時(shí)掏出來(lái)修修改改,慢慢、慢慢打磨,看它能不能在心中存留下來(lái)。就像把一塊黏土甩在墻上,看它是粘上還是掉下”。采訪他的川上未映子聽了有些吃驚,畢竟常見的是保存意念而不是留用某段文章。村上說(shuō)他很少保存小說(shuō)意念那類東西。“我是通過(guò)寫文章來(lái)思考東西的人,所以寫一定長(zhǎng)度的文章這項(xiàng)作業(yè)是很重要的。姑且把一段文章寫下來(lái),再一次又一次修改。如此過(guò)程中,就有某種什么在自己身上自行啟動(dòng)——我要等待那一時(shí)刻。”這么著,加上突然浮出腦海的“刺殺騎士團(tuán)長(zhǎng)”這個(gè)書名,再加上類似聊齋志異的死而復(fù)生《二世緣》故事,這三個(gè)要素成了starting point(起始點(diǎn)),促成了《刺殺騎士團(tuán)長(zhǎng)》這部譯成中文近五十萬(wàn)言大長(zhǎng)篇的誕生。
二
看過(guò)這本由上下兩部構(gòu)成的長(zhǎng)篇的讀者都知道,第一部名為“顯形理念篇”,第二部名為“流變隱喻篇”。何以如此名之,想必不少讀者都感到費(fèi)解。川上未映子也好像不得其解,于是請(qǐng)教村上。村上回答說(shuō),書中的理念和作為柏拉圖哲學(xué)基本概念的理念毫無(wú)關(guān)聯(lián)。“表達(dá)騎士團(tuán)長(zhǎng)到底是什么的時(shí)候,除了‘理念一時(shí)想不出別的詞兒。靈魂啦魂靈啦,這個(gè)那個(gè)倒是很多,但哪個(gè)都不正相合適。不知為什么,單單‘理念(idea)一拍即合。此外‘長(zhǎng)面人那時(shí)候也想了好多。叫什么名字好呢?最終‘隱喻(metaphor)這個(gè)說(shuō)法恰如其分。別的都不合適。意象也好音韻也好,哪一個(gè)都不夠到位。因此,你問(wèn)精確定義是什么,我也極傷腦筋。”隨即又補(bǔ)充一句:“字的意象、音的回響,對(duì)小說(shuō)是非常緊要的。有時(shí)候高于一切,一如人名。”
難能可貴的是,村上再次提起了南京大屠殺。當(dāng)訪談話題進(jìn)入小說(shuō)創(chuàng)作的政治性這一話題的時(shí)候,村上首先認(rèn)為“自己寫的東西是相當(dāng)有政治性的”。同時(shí)覺(jué)得較之直接的具體的政治訴求,莫如以小說(shuō)或故事這一形式“迎面砸過(guò)去”為好。隨即這樣說(shuō)道:
以南京大屠殺為例,否定的一方備有預(yù)設(shè)問(wèn)題集那樣的東西。若這么說(shuō),對(duì)方就這么應(yīng)付;這么駁斥,對(duì)方又這么反擊——模式早已定下,無(wú)懈可擊,一如功夫片。可是,如果換成故事這一版式,就能超出那種預(yù)設(shè)問(wèn)題集,對(duì)方很難有效反擊。因?yàn)閷?duì)于故事或者對(duì)于理念和隱喻,對(duì)方還不知道如何反擊好,只能遠(yuǎn)遠(yuǎn)圍住嚎叫。在這個(gè)意義上,故事在這樣的時(shí)代擁有百折不撓的力量……
自然而然,這要涉及“惡”的問(wèn)題。村上結(jié)合二十多年前寫的《奇鳥行狀錄》強(qiáng)調(diào)說(shuō):“拽出個(gè)體層面的‘惡的,是軍隊(duì)那個(gè)體制(system)。國(guó)家這個(gè)體制制造了軍隊(duì)這個(gè)從屬體制,拽出個(gè)體層面的‘惡。那么,若問(wèn)體制是什么,說(shuō)到底,那不是我們構(gòu)筑的東西嗎?在那一體制的連鎖中,誰(shuí)是施害者誰(shuí)是受害者就變得模糊起來(lái)。我經(jīng)常感到這種類似雙重性三重性的東西。”
必須說(shuō),即使在寫完《刺殺騎士團(tuán)長(zhǎng)》之后,村上春樹仍未能從惡的這種雙重性、三重性的連環(huán)陣中破城突圍,仍為之苦惱。這既是具有“沉思、反思的理性”的當(dāng)代知識(shí)分子共通的苦惱,也未嘗不是魯迅當(dāng)年的苦惱。村上曾在這本訪談錄一再出現(xiàn)的《為了年輕讀者的短篇小說(shuō)導(dǎo)讀者》中從另一角度提及魯迅苦惱的雙重性:“在結(jié)構(gòu)上,魯迅的《阿Q正傳》通過(guò)精確描寫和作者本人截然不同的阿Q這一人物形象,使得魯迅本身的痛苦和悲哀浮現(xiàn)出來(lái)。這種雙重性賦予故事以深刻的底蘊(yùn)。”同時(shí)認(rèn)為魯迅筆下的阿Q具有“活生生的現(xiàn)實(shí)性”。其實(shí),這種雙重性未嘗不是體制之“惡”同國(guó)民性(個(gè)體層面的“惡”)的反映。在某種意義上,魯迅的確終生為之苦惱。也就是說(shuō),魯迅始終在“鐵屋子”和阿Q之間奔走呼號(hào)。
對(duì)了,作為這本訪談錄的活生生的現(xiàn)實(shí)性,村上談“惡”的時(shí)候談到了特朗普:“說(shuō)到底,希拉里·克林頓那個(gè)人,因?yàn)橹徽f(shuō)通用于房子一樓部分的事,結(jié)果敗了;特朗普只抓住人們的地下室說(shuō)個(gè)沒(méi)完,結(jié)果勝了。”村上進(jìn)而解釋說(shuō):“盡管不能說(shuō)是政治煽動(dòng)者,但感覺(jué)上至少像是古代的司祭——特朗普是熟知煽動(dòng)人們無(wú)意識(shí)的訣竅的。于是,仿佛高音喇叭的個(gè)人電子線路就成了有力武器。在這個(gè)意義上,盡管他的邏輯和語(yǔ)匯是相當(dāng)反知性的,但也因之從戰(zhàn)略上十分巧妙地掬取了人們?cè)诘叵聯(lián)碛械牟糠帧!?/p>
應(yīng)該說(shuō),這恐怕也是貓頭鷹在黃昏起飛后看到的情形,亦是貓頭鷹在黃昏起飛的目的或理由。
三
村上春樹雖然也寫隨筆和搞翻譯,但無(wú)須說(shuō),主要以小說(shuō)家聞名。在這本訪談錄中,一貫低調(diào)的村上也對(duì)此直言不諱。他說(shuō)自己喜歡寫小說(shuō),很少外出東游西逛。每天早起早睡,夜生活幾乎是零。
若問(wèn)我為什么能堅(jiān)持過(guò)這樣的生活,因?yàn)槟軐懶≌f(shuō)。并且能在一定程度上寫好小說(shuō)。小說(shuō)比我寫得好的人,客觀看來(lái)為數(shù)不多,世界上。……在第一線專業(yè)寫了差不多四十年,書也能在某種程度上賣出去,我想我還是有兩下子的。所以很開心的,寫東西。想到比我做得好的人不是那么多,做起來(lái)就很開心。例如做愛也不差,可是做愛比我做得好的人,世界上肯定比比皆是(笑)。倒是不曾實(shí)際目睹……
喏,如此看來(lái),村上感到自信滿滿的活計(jì)至少有兩樣,一是做愛,二是寫小說(shuō)。前者對(duì)別人沒(méi)什么參考價(jià)值,不必公開研討。這里只談小說(shuō)。村上為什么小說(shuō)寫得那么好?說(shuō)實(shí)話,因?yàn)槲乙苍蛔粤苛Φ叵雵L試寫一部類似錢鍾書《圍城》那樣的長(zhǎng)篇小說(shuō),所以閱讀和翻譯當(dāng)中格外注意尋找個(gè)中答案。功夫不負(fù)有心人,終于找出兩個(gè)。下面容我粗線條概括一下,如果哪一位看了多少受到啟發(fā),不久的將來(lái)中國(guó)出現(xiàn)一位小說(shuō)寫得有村上那么好甚至比他還好的人也不一定。
答案之一,要有巫女才能。村上認(rèn)為人的意識(shí)出現(xiàn)得很晚,而無(wú)意識(shí)歷史長(zhǎng)得多。那么在無(wú)意識(shí)世界里人們依據(jù)什么活著呢?村上介紹說(shuō)遠(yuǎn)古社會(huì)有巫女或行使巫女職責(zé)的王那樣的存在。這種人的無(wú)意識(shí)比其他人敏銳,能夠像避雷針接收雷電一樣把自己接收的信息傳遞給大家。而作家可能與此有相通之處。換句話說(shuō),如果把無(wú)意識(shí)比作一座房子的地下室的地下室或地下二層,那么作家就應(yīng)該有進(jìn)入地下二層的能力,即具有巫女或靈媒(medium)那一性質(zhì)的能力。“所以,就算問(wèn)我作為作家有沒(méi)有才華,對(duì)那東西我也是不清楚的。再說(shuō)對(duì)于我怎么都無(wú)所謂。相比之下,有沒(méi)有接收那種信息的能力或資格要關(guān)鍵得多。”村上覺(jué)得自己是有那樣的能力的。至于什么時(shí)候開始有的,他回憶可能是早在上個(gè)世紀(jì)八十年代寫《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的時(shí)候。因?yàn)楫?dāng)時(shí)他堅(jiān)信分別以“世界盡頭”和“冷酷仙境”兩條線交替推進(jìn)的故事最后必定合為一體——這種信心即意味著具有“接收什么的魅力”。村上進(jìn)而斷言:“完全沒(méi)有那種能力的人,寫小說(shuō)怕是吃力的吧!哪怕文章寫得再好,小說(shuō)也是寫不成的。即使寫得成,也找不到讀者。”
這讓我想起早在二00三年第一次見村上時(shí)他對(duì)我說(shuō)的話。當(dāng)時(shí)我問(wèn)他創(chuàng)作《海邊的卡夫卡》那樣的想象力從何而來(lái)。他回答:“想象力誰(shuí)都有,難的只是接近那個(gè)場(chǎng)所。……下到那里、找到門、進(jìn)去而又返回是十分困難的。我碰巧可以做到。如果讀者看我的書過(guò)程中產(chǎn)生同感或共鳴,那就是說(shuō)擁有和我同樣的世界。我不是精英不是天才,也沒(méi)什么才華,只不過(guò)能在技術(shù)上打開門,具有打開門身臨其境而又返回的特別的專門技術(shù)。”這里所說(shuō)的“那個(gè)場(chǎng)所”,用這本訪談錄中的比喻來(lái)說(shuō),可能就是地下二層,亦即無(wú)意識(shí)世界、巫女世界、靈媒世界。
答案之二,必須和什么決一死戰(zhàn)。村上說(shuō)他為了寫這部日文長(zhǎng)達(dá)七八十萬(wàn)字的《刺殺騎士團(tuán)長(zhǎng)》,整整花了一兩年時(shí)間。假如不具有同什么戰(zhàn)斗或者格斗那般堅(jiān)定的決心,就很難把故事推向前去。“單單舒舒服服眉開眼笑地坐在桌前,那是寫不來(lái)長(zhǎng)篇小說(shuō)的。必須和什么決一死戰(zhàn)。”那么到底和什么決一死戰(zhàn)呢?總的說(shuō)來(lái),決一死戰(zhàn)的對(duì)象就是“惡”或類似惡的什么。而“惡”大體分為外在的“惡”和內(nèi)在的“惡”。外在的“惡”大多是惡的象征或隱喻——在《奇鳥行狀錄》中,是諾門罕、綿谷升;在《1Q84》中,是“小小人”和邪教頭目;在《刺殺騎士團(tuán)長(zhǎng)》中,是納粹德國(guó)吞并奧地利和日本侵略軍南京大屠殺。所用辦法無(wú)不是以小說(shuō)或故事這一形式“迎面砸過(guò)去”。要“迎面砸過(guò)去”,就要“深化故事”;而要深化故事,“就不能不觸及自身一方的惡”即內(nèi)在的惡。內(nèi)在的惡又往往同外在的惡兩相呼應(yīng)。村上以《鏡》那個(gè)短篇為例:學(xué)校保安夜間巡邏時(shí),發(fā)現(xiàn)照在鏡子里的本人居然一副猙獰嘴臉,嚇得他把鏡子打得粉碎,頭也不回地逃之夭夭。不料第二天再去同一場(chǎng)所一看,那里根本沒(méi)有什么鏡子。這種雙重以至三重幻影暗示了“惡”的雙重性以至三重性。
與此同時(shí),村上盡管把體制視為最大的“惡”,但并不一概而論,不認(rèn)為所有體制都是“惡”。“一如所有東西都有影子,任何國(guó)家任何社會(huì),‘惡都糾纏不去。它既潛伏于教育體系,又藏身于宗教體系之中。……我是鐵桿個(gè)人主義者,對(duì)于那種體制的‘惡懷有敏感的戒心。很想再寫一寫那種東西的形態(tài)。問(wèn)題是寫起來(lái)勢(shì)必成為政治訴求,而這點(diǎn)我是無(wú)論如何都想避免的。”概而言之,村上的糾結(jié)在于,既有同惡決一死戰(zhàn)的決心,又想避免使之成為政治訴求。不過(guò)相比之下,畢竟決心是第一位的。沒(méi)有決心,沒(méi)有和什么決一死戰(zhàn)的決心,長(zhǎng)篇小說(shuō)的創(chuàng)作就無(wú)從談起。
無(wú)須說(shuō),這同樣和貓頭鷹在黃昏起飛的目的或理由相關(guān),表現(xiàn)出了一個(gè)知識(shí)分子、一個(gè)作家的社會(huì)擔(dān)當(dāng)意識(shí)或使命感,及其“沉思、反思的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