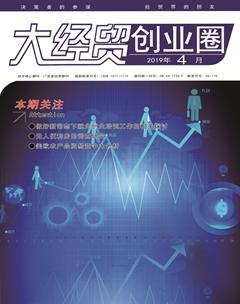文化、個性與企業創新
韓至杰
【摘 要】 本文通過對心理學、經濟學、管理學的文獻進行研究,將文化、個性與企業創新聯系在一起,為企業如何更好的實施創新活動,更好的實現創新成果提供了理論支撐。研究結果表明,企業創新與一個國家或是地區的個人主義水平正相關,與一個國家的不確定性規避水平負相關,與管理者風險承擔能力正相關。
【關鍵詞】 文化 風險偏好 企業創新
引 言
創新是一項重要的企業決策,同時又具有風險性、不可預測性、長期性、多階段性、勞動密集性,以及特殊性,這對于企業內部如何更高效的制定激勵合同提出了嚴重挑戰(Holmstrom,1989)。Manso(2011)認為,傳統的績效工資激勵將可能抑制企業創新。而如果調整激勵方式,促進管理者及員工冒險以達到容忍失敗并促進創新的作用可能會削弱企業內部對于其他業務的激勵。這樣的觀點也得到了很多的實地調研結果的證實,單純按照績效來制定財務激勵會明顯抑制創造力。總的來說,過去的研究強調如何調整傳統激勵機制激勵創新,而顯然傳統的方法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為此,尋找更加有效的激勵辦法或者尋找更有效的風險代理現象成為了研究的重點。
以往的文獻表明,往往是那些傾向于冒險的、過于自信的首席執行官是積極從事與企業創新相關的活動,并且其創新的成功率也更高。不過,雖然風險承擔是創新的必要條件,但可能還不夠。心理學研究發現,對于經歷的追求是五大定義個性的因素之一,是創造力和創新的基礎。并且這種見解得到了Dyer et al.(2011)的證明,他們在當年對5000名高管進行了調查,并證實了這一點。他們發現成功的創新者具有的共性特點是“不斷地嘗試新的經驗和嘗試新的想法“。在此基礎上,首席執行官若能將風險承受能力與對新員工的渴望結合起來,就能取得更大的創新成功。如此,尋找能夠代表首席執行官風險偏好的個性特征可能能夠捕捉他們內在的渴望,獲得需要風險和發現試點首席執行官與更成功和更原創的創新相關。
在針對如何讓企業更具創新性的因素以及創新企業環境的共同特征研究過程中。學者逐漸發現創造力在創造創新中起著關鍵作用,而人力資本則在創新中起到決定性因素。人們開始期望將創新人才與創新環境相結合帶來更強的創新產出。創意人士作為是風險承擔者,當地的創意文化和創新環境可以支持創新等風險投資。這一關鍵組合使得創新文化與個性特征在企業創新中的作用開始得到重視。
同時,以往文獻的結果給了我們研究企業創新相關要素良好的切入點,總的來說,由于企業創新行為過多的依靠管理層決策以及研發人員的開創性,因此個人特征和整體環境文化對創新有著重要的影響。不少文獻也發現一個國家、地區甚至是個人的文化特征與所處地或所處企業商業成果有著密切的關系。不論是我國還是國外,企業的生存脫離不開周圍的環境,并且,企業的整個經營成果也是通過員工、客戶和供應商與當地環境進行互動的結果。因此,圍繞一家公司的文化規范將對一個組織內推廣的價值觀和行為產生深遠的影響,而這反過來又會產生切實的商業后果。事實上,最近的文獻記載,文化影響企業行為的多個方面,包括風險承擔、股息政策和收益質量。鑒于文化在塑造企業政策中的重要作用,我們特別選取個人主義和不確定性規避的文化作為研究對象,探究其是否對企業創新產生影響。企業創新不同于大多數其他企業政策,因為創新成果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不僅依賴前期大量的投資,也依賴于企業的人力資本,因此,一家企業的創新成果也往往離不開員工的風險偏好和價值取向。因此,文化等微妙因素對于人的影響與企業創新成果尤其相關。
文獻回顧與理論推導
創新是產生新產品或新想法的過程,雖然創新可以在個人層面上產生,但如今以企業為集群的生產方式讓創新被認為是一種集體成就。因此,文化或當地因素對于一個地區的個人或社區群體,可能影響該地區的創造力和創新行為。有研究發現擁有大量人口的社區將承載創造性文化,同樣,創意文化也將出現在擁有大量來自創意階層的人的地區,而這些人也更多的受雇于需要創造性思維和創新技能的職業。創造力是創新的主要決定因素,發掘創造力與企業創新之間的聯系是非常重要的。
同時,創造力文化是賦予了企業整體的創造氛圍,而管理層風險承擔同樣對于企業創新有著重要的影響作用,Galasso&Simcoe(2011)研究了管理特征與創新之間的聯系,同時,發現管理層對于失敗的容忍程度與創新之間存在積極關系。除此之外,管理層的風險承擔能力也使得其在與客戶-供應商關系處理方面更加的大膽,也促進了企業創新。作為企業創新的發起者,管理者風險承擔能力會顯著提高企業的創新投入,而整體文化層面賦予企業的創新力會顯著提高企業的創新產出。
2.1 文化層面:
文化通常被描述為“一組人與另一組人的思維的集體規劃”。由于一個國家的人口、內部地理距離和自然環境有很大的差異,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歷史的發展,分隔為小塊的地區漸漸產生一些共同的價值觀和獨特的行為,大至一個國家也往往會產生獨特的觀念,久而久之,個人價值觀便上升為一種固化的社會觀念或約定俗成的規范。因此,我們猜想,個人主義、集體主義和不確定性維度上的文化規范對于將對一個地區、一個國家的企業創新生產力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當然,我們的論點基于一個大前提,大便是企業創新嚴重依賴人力資本,由此產生創新對于文化規范的敏感。
首先,個人主義和企業創新之間的關系。個人主義是指人們傾向于保持獨立而不是相互依賴的自我形象或自尊的程度。高度個人主義的文化強調個人自由,但其并不意味著單打獨斗,高度個人主義的文化強調強烈的群體凝聚力。在個人主義文化中,一個人的身份是在人身上。也就是說,人是有意識的,自我實現是很重要的。因此,人的個體存在更多的是關于他們的能力如何不同于他們的人,因此表現出超越自信和自我歸因的偏見。
因此,有理由認為個人主義有利于企業創新。Gorodnichenko&Roland(2016),他們沿著個人主義-集體主義的維度發展了內生增長模型。該模型預測,個人主義文化中隱含的創新元素將帶來很大的社會回報,繼而個人主義會導致更大、更有效的創新。除了社會獎勵的論點外,個人主義與國家居民表現出的過度自信的整體知識水平有關,這一事實也可能導致更高水平的企業創新。除此之外,個人主義的過度自信層面克服了許多對創新的自然抑制因素,從而導致更大的創新產出和創新效率。
與當前的研究相關,個人主義文化的人更傾向于強調個人的成就,如重大發現或偉大的藝術成就。本著這種精神,Roland(2016)提出了一個理論框架,將文化的個人主義集體主義維度與創新和經濟增長聯系起來。這一模式產生的主要結果是,個人主義通過更強的激勵作用,使其長期增長,從而產生新的文化誘導的社會回報。Roland還采用遺傳數據作為文化工具對他們的模型進行了間接測試,并報告了個人主義與每個工人的收入以及全要素生產率之間的積極關系。
個人主義積極影響創新活動的另一條途徑是通過促進整個勞動力的過度自信來實現的。Galasso&Simcoe(2011)研究發現一位過度自信的首席執行官掌舵公司有助于企業創新。由于個人在風險和目標項目上傾向于過度自信,因此過度自信會導致公司更替的創新項目重新出現。
除了個人主義,與創新相關的地區文化都會不同程度上促進創新的產生。不少學者認為創意階層是城市經濟發展的重要經濟力量。而地區創造力,特別是企業創新水平由創造新知識和高水平創造力的職業人士組成。先前有文獻使用創意課作為一種地方創新氛圍的衡量指標,用以代表當地對于創意和創新活動以及成長的支持,也就是用創意課來衡量地方創意文化。Leuenberger&Kluver(2005)認為,創意課是塑造創意文化的關鍵組成部分,創意文化社區可以產生包括創意在內的解決方案。Pitta et al.(2008)指出,有大量創意個人的城市或地區可以被定義為創意社區。因此,地方創意階層所占比例可以作為地方創意文化的一個很好的代表。不過,整體結果表明,地區文化若有助于員工創新,其所在地創新水平,特別是企業的創新水平會顯著高于其他地區。
其二,文化層面對于不確定性回避的問題。不確定性回避是指一個人對不確定性或歧義感到不舒服的程度。擁有不確定性規避文化的人更傾向于規則、穩定性和一致性。這些感覺在很大程度上與成功的創新戰略是不相容的,因為創新涉及巨大的不確定性,這就意味著,創新者需要在早期有著對失敗較高的容忍度和較強的冒險意愿,這些對創新成功至關重要。研究表明,在不確定性規避范圍較高的國家,即使項目提供了創造突破性發明的可能性,員工也不太可能從事失敗風險較高的項目。因此,企業創新水平與不確定性規避之間存在負相關。
有研究通過對41個國家8萬多個觀察樣本的研究發現,國家文化是企業創新的重要決定因素。具體而言,位于高度個人主義國家的公司產生越來越多的具有影響力的專利,并更有效地將其研發投資轉化為創新產出(按研發比例衡量的專利或引用數量)。而當研究不確定性規避與企業創新關系時,位于高不確定性規避國家的企業生產的專利更少,而且它們生產的專利也更少具有開創性。此外,位于高不確定性規避國家的企業在將研發投資轉化為創新產出方面的效率較低。這些結果在控制了大量的財務和國家一級控制變量以及行業和年度影響后仍然有效。
2.2 個人特性:
文化更強調團隊的創造性,而作為發起者管理層個性特征同樣對創新有著很大的作用,并且,具有風險偏好特征的管理層更加能夠促進企業創新。CEO的經歷便能夠代表其風險的承受能力,其中比較容易獲取的是對各種執照的獲取,例如駕照、賽車駕照、飛行執照等等。心理學方面的文獻指出,人們對于駕駛飛機飛行的欲望來源于對預測的刺激和冒險的尋求,這都是“經歷追求”的一部分。“經歷追求”是個人格層面的定義,它包括對事物多樣性,新奇性,復雜性,并能帶給人強烈的感覺,為了這樣的體驗,他們會愿意去承擔身體、社會、法律和金融方面的風險。最近,有研究人員以飛行員(或是僅僅持有飛行員執照)為首席執行官的代理指標研究其對于風險的承受能力。“追求經歷”的人,他們愿意去尋求風險的原因在于他們對于未知體驗的渴望,同時他們對于不同體驗的接受程度也更高,并且,很多的研究發現“經歷尋求者”更傾向于接受新的想法。可見,文化層面賦予了公司整體員工更強的創新動力,而個性特征給予了CEO更強的創新決策力。
因此,有文獻采用CEO的飛行經歷以及持證情況作為其風險承受能力的代理指標。并且,值得注意的是,首席執行官決定經營小型飛機是個人生活方式的選擇,他們的飛行意愿不太可能受到公司條件的影響。使用CEO飛行員持證作為代理變量的情況下,內生性就不那么令人擔憂了,因此,其研究結論具有很強的效力,我們有理由相信,具有風險偏好、過度自信的管理層更有可能投身于企業創新中去。
結 論
企業創新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創新投入,另一方面是創新產出,而無論是投入還是產出都對最后的結果有著重要的影響。受不斷增長企業創新文獻的推動,我們將個人主義和不確定性的文化維度、“經歷尋求”的個性唯獨與創新投資、創新產出和創新效率聯系起來。我們認為個性維度與創新投入有著較強的關系,而文化維度與企業創新產出之間存在著強有力的關系。具體來說,我們認為,企業創新與一個國家或是地區的個人主義水平正相關,與一個國家的不確定性規避水平負相關,與管理者風險承擔能力正相關。
具體而言,企業在進行管理者選擇時要對影響風險偏好的個性特征做深入的考察,以匹配企業的創新力。同時,充分利用當地的創新氛圍來創造企業創新,要重視當地的環境和當地的人力資本所帶來的創新思維和創新技能,從而加強企業的創新生產。本文重點介紹了影響企業創新的文化和個人因素,以期通過一些外部途徑促進企業創新發展。同時,在研究中我們也發現,地方文化以及其他地方因素可以成為創新的重要組成部分。
當今世界,技術和創新在人們的生活和企業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說到底,創新對企業來說是一項風險投資。我們不應只看到創新帶來的收益,同時也應在意其背后的風險,不過,我們的研究主要貢獻在于為企業創新研究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通過不同的外部渠道,一國、一地區的文化與管理者自身個性特征(可能也來源與當地文化)可能會影響經濟發展。雖然文化在經濟領域的重要性可以追溯到亞當·史密斯的開創性工作,但目前稍有文獻從實證或實地調研的角度來驗證文化與創新間的關系。
同時,本文的研究結果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首先,企業管理者可以在其企業文化中包含并利用當地文化和其他當地因素來產生創新。其次,文化規范對企業創新成功至關重要,無論國家或地區,具體的制度框架如何。因此,宏觀層面,我們應該支持創新的企業文化,即獎勵個人主義和阻止不確定性規避文化。不過,本文并沒有明確地探討創新文化與風險偏好個性是如何或應該如何融入企業創新文化中去,這是本文的一個局限。未來的研究可能會更有效地挖掘文化與管理者個性在企業創新中的整合。
【參考文獻】
[1] Holmstrom, B., 1989. Agency costs and innovation.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12, 305-327.
[2] Manso, G., 2011. Motivating innovation. Journal of Finance 66, 1823-1860.
[3] Dyer, J., H. Gregersen, and C. Christensen , 2011. The Innovator?s DNA: Mastering the five skills of disruptive innovators. Cambridg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
[4] Galasso, A., Simcoe, T., 2011. CEO overcon?dence and innovation. Manag. Sci. 57, 1469–1484.
[5] Gorodnichenko, Y., Roland, G., 2016. Culture, institutions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Rev. Econ. Stat (forthcoming).
[6] Leuenberger, D. Z., & Kluver, J. D. (2005). Changing culture: Generational collision and creativity. Public Manager, 34, 16-21
[7] Pitta, D. A., Wood, V. R., & Franzak, F. J. (2008). Nurturing an e?ective creative culture within a marketing organization. Journal of Consumer Marketing, 25, 137–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