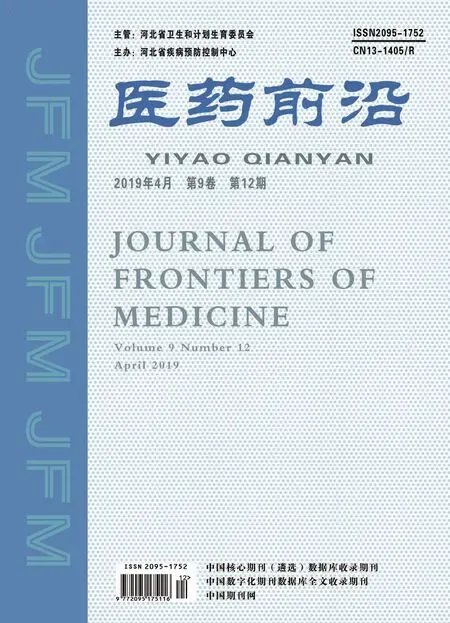神經刺激器指導下腰叢加坐骨神經阻滯用于老年患者下肢手術麻醉的臨床效果分析
張雷
(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五醫院麻醉科 廣東 廣州 510770)
老年患者下肢手術采用的麻醉方式多為腰-硬聯合穿刺麻醉,由于近幾年臨床廣泛應用的神經刺激器可以對腰叢、坐骨神經阻滯精準定位,所以本研究結合我院老年下肢手術患者予以神經刺激器指導下腰叢加坐骨神經阻滯麻醉方式,對其應用價值進行分析,匯報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從我院2017年10月—2018年11月間接診的老年下肢手術患者中選擇64例分作兩組,參照組32例患者采用腰-硬聯合穿刺麻醉,研討組32例患者采用神經刺激器指導下腰叢加坐骨神經阻滯,對比麻醉結局。
參照組患者男女比例17:15,年齡61.8~77.4歲范圍,平均(67.23±3.51)歲;研討組患者男女比例18:14,年齡62.3~76.9歲范圍,平均(65.87±3.69)歲。兩組患者基礎資料進行對比后發現,組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有效可比。
1.2 方法
全部患者在麻醉前半小時肌注0.5mg阿托品,100mg苯巴比妥鈉,隨后進入手術室,然后將10ml/kg乳酸鈉林格氏液行靜脈輸注,此時對ECG、BP、HR、SPO2行常規監測。
參照組32例患者采用腰-硬聯合穿刺麻醉,于珠網膜下采用3ml丁哌卡因,再以0.3%羅哌卡因間斷使用。研討組32例患者采用神經刺激器指導下腰叢加坐骨神經阻滯。首先患者側臥,屈膝收腹,進行消毒鋪巾之后,將神經刺激器的正級貼緊大腿皮膚,負極則與穿刺針相連。以患者的第4腰椎后正中為腰叢,穿刺點為術側開5厘米位置。同時坐骨神經阻滯是標記股骨大轉子,骶裂孔與骶髂關節三點,在股骨大轉子與骶髂關節的連線中點作1線,與兩者連線交點位置行穿刺。此時應當注意神經刺激器初始設置電流為1mA、2Hz,穿刺針進針后誘發足背與腰叢股四頭肌的收縮運動,當患者收縮運動開始后,降低電流到0.3mA.此時若仍有收縮運動,應當使用羅哌卡因0.5%。
1.3 觀察指標
對兩組患者麻醉前與麻醉后各時間段的DBP、HR、SBP指標予以記錄并對比,以此作為麻醉效果的評判依據。
1.4 統計學方法
通過SPSS18.0統計學軟件對觀察數據作處理,計量資料(麻醉前后各時間段的指標)以均數±標準差(±s)表示,以t檢驗,當P<0.05時,組間差異有顯著性。
2.結果
2.1 麻醉指標對比
對兩組患者麻醉前與麻醉后各時間段的DBP、HR、SBP指標予以記錄并對比,數據顯示研討組DBP、SBP在麻醉后各個時間段都低于參照組,特別是麻醉后即刻顯著下降,P<0.05,組間差異有顯著性。
表 麻醉指標對比(±s)

表 麻醉指標對比(±s)
組別 時間 DBP(mmHg) HR(次/min) SBP(mmHg)參照組麻醉前 77.02±9.75 78.43±12.82 127.97±17.89麻醉后即刻 74.43±11.72 79.82±15.87 125.94±14.36麻醉后半小時 74.07±13.37 78.52±13.81 127.04±14.38手術結束時 75.18±13.02 77.29±12.41 127.57±11.42研討組麻醉前 76.97±11.67 79.03±13.04 127.42±16.62麻醉后即刻 64.21±12.25 84.12±12.13 101.82±11.49麻醉后半小時 68.38±13.24 81.16±10.06 114.16±11.49手術結束時 75.03±12.26 81.83±10.94 117.83±13.29
3.討論
腰-硬聯合穿刺麻醉是以往臨床應用非常廣泛的一種麻醉方式,它起效快,且有較良好的時間可控效果,有完善的麻醉阻滯[3]。但是,其存在腰麻上界的阻滯平面難以控制。患者通常在麻醉后血管會產生擴張,從而顯著改變血流動力學,所以常常會出現并發癥,老年患者的麻醉風險進一步加大。多數老年患者的脊柱往往存在變形或是增生,并且下肢骨折手術會讓患者的體位配合較差,椎管穿刺難度加大。下肢神經來源于腰叢與骶叢,坐骨神經作為骶叢的主要表現形式,因位置較深,極易產生并發癥,因此臨床手術多選擇阻滯坐骨神經。神經刺激器指導下腰叢加坐骨神經阻滯更加精細準確,可以顯著改進阻滯效果[4]。
對兩組患者麻醉前與麻醉后各時間段的DBP、HR、SBP指標予以記錄并對比,數據顯示研討組DBP、SBP在麻醉后各個時間段都低于參照組,特別是麻醉后即刻顯著下降,P<0.05,組間差異有顯著性。綜上,神經刺激器指導下腰叢加坐骨神經阻滯用于老年患者下肢手術麻醉,安全有效,值得進一步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