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影視業態五大關鍵點
胡正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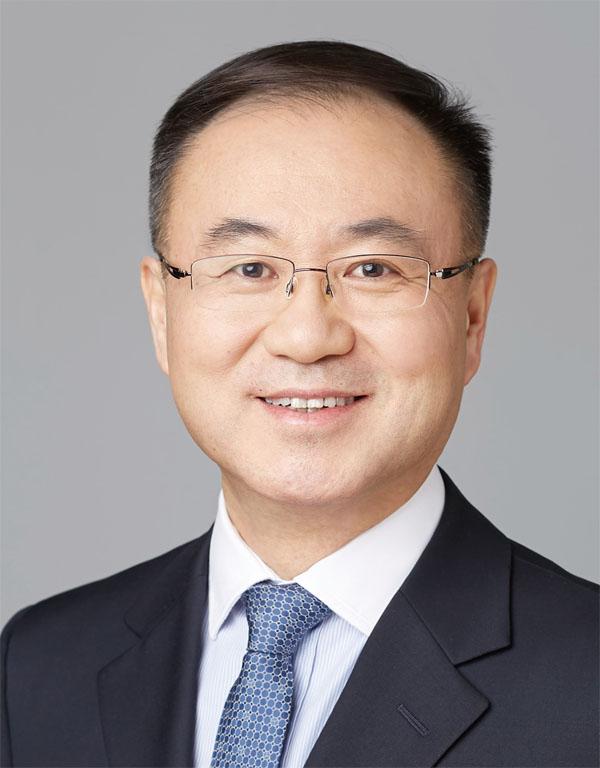
從本質上看,影視業燒錢還是不燒錢只是現象,只是表征。燒錢不燒錢不是問題,有投入就有合理的產出和回報才是關鍵。簡單說,燒錢的行業可以說是不理性、不成熟的行業,因為可能前期投資就不夠成熟,也可能生產流通環節不成熟,如市場混亂導致非良性競爭、成本分配和控制不合理等,又或者用戶消費也不夠理性和成熟,消費的多樣性和類型化不夠等。
從歷史上看,燒錢還是不燒錢只是行業發展的階段性問題。我們的影視行業正處在調整期,或稱平臺期。傳統影視行業還沒有發展到成熟階段,形成自己的模式時,互聯網已經開始沖擊和顛覆了傳統的影視行業模式,因此,影視行業到現在都還在摸索、試錯、磨合和整合,尚未發展出一個有效的運營模式。其實在影視行業成熟的美國,也可以看到這種沖擊、顛覆、磨合和整合,比如盡管有非常成熟的好萊塢影視模式,但是當Netflix顛覆和逆襲傳統電視行業,乃至近兩年開始逆襲傳統電影行業后,美國的影視行業也在洗牌,模式也在重建。最新的例子就是迪士尼重金收購福克斯,希望在日益流媒體化的影視行業中重振生機,重構模式。任何行業的發展都有生命周期。能否盡快修正和調整生命周期,走可持續發展道路,是對行業,特別是對巨頭的挑戰。看歷史,行業巨頭轟然倒下的前車之鑒真是不少。
所以說,影視行業,乃至互聯網時代的視聽行業燒錢不燒錢不是關鍵,要想生長出一個健康、成熟的行業,需要抓住下面這些關鍵。
第一,成熟、理性、長期的心理預期和認知判斷。當全社會都想掙熱錢、掙快錢,缺少長遠預期時,很難苛求影視行業乃至視聽行業不急功近利。從投資商到編劇,從導演到演員,從平臺到院線,從流通到消費等都需要這種“長大了”的心態。
第二,生產方式與生產機制要顛覆式創新。原有的工業化大生產還是可以持續的,畢竟影視行業、視聽行業的投資、生產、流通與消費是大體量的、專業化的和高成本的,這一點從我國和歐美成功的案例中都可以看到。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互聯網時代,特別是人工智能時代,一定程度上市場準入門檻降低,生產模式日益多樣化,眾創內容(crowd-creativity)、機器智能生產內容、人機共創內容等將會大量涌現。這可能就要求生產方式和機制發生很多變化,如更加專業化分工,更加垂直化生產,更加精準化流通,更加場景化消費。
第三,深刻把握和適應互聯網下半場影視消費和視聽消費的模式變異。消費模式既有繼承,又有變異。其中變異值得關注和適應。一方面消費平臺正在多元化,從早先的單屏消費,走過了多屏消費,目前正處在跨屏消費階段,并日益走向無屏的全息消費平臺。另一方面,以用戶為中心的生產消費方式正在形成,Netflix早些年基于用戶數據的生產、流通和消費方式就是這一體現。無數據勿生產幾乎已經成為共識,用戶數據是生產的起點。
第四,運用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化技術手段,以適應網絡智能時代影視、視聽行業生產、消費的變遷。除了傳統的影視制作手段與呈現方式,當前和未來階段,大數據、云計算和邊緣計算、人工智能、全息顯示、虛擬\混合\增強現實技術,還有區塊鏈等眾多新興技術都正在快速運用到影視行業中。現在看還要繼續燒錢,但是這種高投入也容易產出高回報,如歷史上的《阿凡達》和近前的《流浪地球》。
第五,有效的監管體系和高效的治理結構也很關鍵。1997年新修訂《聯邦電信法》推動了美國行業的融合和大發展。我們也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道路上,這個體系中一定要有政府、行業、行業協會、用戶等各個利益攸關方參與,各司其職、各做其事,不僭越、不替代才是真正有效的體系。
說實話,初露端倪的是行業產能不足,產品存量不夠,供給側已經開始出現供給不足,可是消費側的消費需求卻是個增量。因此,幾方互動如何讓供給與需求能夠達成動態的平衡,這才是當下和未來一段時期影視行業重整的最大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