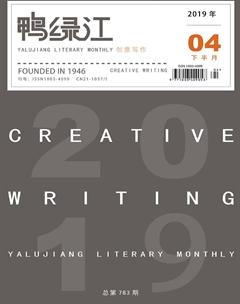在未名湖邊和書房里的對話
曹文軒 徐妍
與一位古典風格的現代主義者對話之一
地點:未名湖邊。
旁白:五月中旬的一個周六的傍晚,我比曹文軒先生早五分鐘來到未名湖邊。將訪談的地點選在這里,這是我與曹文軒先生在電話里商定好的。選擇這個地點,是頗有意味的。第一次訪談,我不想將話題直接切入嚴肅的主題里,更重要的原因是,水可以讓時光向記憶的縱深處流淌。像平時講課準時走進教室一樣,曹文軒先生如約而至。
1. 水與成長
徐妍:對您的第一次專訪,選擇在未名湖,是因為我多次在您的文字里感受到您對水的親和態度。您在《童年》這篇散文里曾說:“我家住在一條大河的河邊上。”1所以,我很想從“水”開始我們的訪談。您的整個成長階段都是在大河邊度過的嗎?
曹文軒:是的。盡管家隨著父親工作的不停調動而不停地遷移,但家總會傍水而立,因為,在那個地區,河流是無法回避的,大河小河,交叉成網,那兒叫水網地區。那里的人家,都是住在水邊上,所有的村子也都是建在水邊上,不是村前有大河,就是村后有大河,要不就是一條大河從村子中間流過,四周都是河的村子也不在少數。開門見水,滿眼是水,到了雨季,常常是白水茫茫。那里的人與水朝夕相處,許多故事發生在水邊、水上,那里的文化是浸泡在水中的。可惜的是,這些年河道淤塞,流水不旺,許多兒時的大河因河坡下滑無人問津而開始變得狹窄,一些過去很有味道的小河被填平成路或者成了房基、田地,水面在極度萎縮。我很懷念河流處處、水色四季的時代。
徐妍:我是在平原長大的。我珍愛并感謝平原給予我的一切。每次車過平原,我都注視窗外。每一次注視,都讓我感受到平原的豐厚與寬闊。除了大海,平原上的高度也是一種無限。平原上的大雁飛得再高,也不會丈量出天空與平原的高度。但是,我所見到的平原河流很少,這就使我常感一種缺憾:在我的理解中,生命原本應該是由水構成的,而我的平原的高度與廣度畢竟線條太硬,不像柔和的流水那樣讓人感到溫馨和有韻味。所以,我又不禁羨慕生長在水鄉的人。尤其是當通過閱讀得知水對于您的性格、人生觀和審美趣味都有很深的內在影響時,我更是對您生活的那個水邊的村莊充滿想象。您說:“這是一個道道地地的水鄉。我是在吱吱呀呀的櫓聲中,在漁人噼噼啪啪的跺板(催促魚鷹入水)聲中,在老式水車的潑剌潑剌的水聲中長大的。我的靈魂永遠不會干燥,因為當我一睜開眼來時,一眼瞧見的就是一片大水。在我的腦海里所記存著的故事,其中大半與水相關。水對我的價值絕非僅僅是生物意義上的。它參與了我之性格,我之脾氣,我之人生觀,我之美學情調的構造。”2您能否進一步談一下水構成了您怎樣的性格、人生觀與審美情趣?
曹文軒:首先,水是流動的。你看著它,會有一種生命感。那時的河流,在你的眼中是大地上枝枝杈杈的血脈,流水之音,就是你在深夜之時所聽到的脈搏之聲。河流給人一種生氣與神氣,你會從河流這里得到啟示。流動在形態上也是讓人感到愉悅的。這種形態應是其他許多事物或行為的形態,比如寫作——寫作時我常要想到水——水流動的樣子,文字是水,小說是河,文字在流動,那時的感覺是一種非常愜意的感覺。水的流動還是神秘的,因為你不清楚它流向何方,白天黑夜,它都在流動,流動就是一切。你望著它,無法不產生遐想。水培養了我日后寫作所需要的想象力。回想起來,小時我的一個基本姿態就是坐在河邊上,望著流水與天空,癡癡呆呆地遐想。其次,水是干凈的。造物主造水,我想就是讓它來凈化這個世界的。水邊人家是干凈的,水邊之人是干凈的,我總在想,一個缺水的地方,是很難干凈的。只要有了水,你沒法不干凈,因為你面對水再骯臟,就會感到不安,甚至會感到羞恥。春水、夏水、秋水、冬水,一年四季,水都是干凈的。我之所以不肯將骯臟之意象、骯臟之辭藻、骯臟之境界帶進我的作品,可能與水在冥冥之中對我的影響有關。我的作品有一種“潔癖”。最后,是水的彈性。我想,這個世界上再也沒有比水更具彈性的事物了。遇圓則圓,遇方則方,它是最容易被塑造的。水是一種很有修養的事物。我的處世方式與美學態度里,肯定都有水的影子。水的滲透力,也是世界上任何一種物質不可比擬的。風與微塵能通過細小的空隙,而水則能通過更為細小的空隙。如果一個物體連水都無法滲透的話,那么它是天衣無縫的了。建一座大樓,最揪心的莫過于防水了。誰家跑水,全樓人都緊張。水之細,對我寫小說很有啟發。小說要的就是這種無孔不入的細勁。水,也是我小說的一個永恒的題材與主題。對水,我一輩子心存感激。
徐妍:通過您的話語,我大概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水對一個人生命的影響是一種浸潤式的。水,常態的水,總是神態安詳、步履輕盈,與時間的本質有相似性。而就在水的舒緩流動里,一個人成長階段的性格塑造完成了。當水參與了一個人成長階段的性格構成時,我想它實際上也參與了一個人的人生觀、審美趣味的形成。您說的這一切都是讓我們這些遠離水鄉的人永遠向往的。但是,現在我換一個角度與您談論這個問題:水對您性格與審美趣味的影響,是否也有讓您認為不盡人意的地方?
曹文軒: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從來沒有人這樣問過我。是的,我與我的小說的長處與短處,大概都在水。因為水——河流之水而不是大海之水,我與我的作品,似乎缺少足夠的冷峻與悲壯的氣質,缺乏嚴峻的山一樣的沉重,容易傷感,容易軟弱,不能長久仇恨。水的功能之一,就是將具有濃度的東西進行稀釋,將許多東西沖走,或是洗刷掉。大約在四十歲之前,我還一直沒有覺得世界上有壞人,很壞很壞的壞人。我對人只是生氣,而很難達到仇恨的程度。即使生氣,也絕不會生氣很久,更談不上生氣一輩子了。時間一久,那個讓我生氣的人或事,就會慢慢地模糊起來,一切都會慢慢地變得光溜溜起來。一個人沒有仇恨,不能記仇,這對于創作是十分有害的,它影響到了他對人性的認識深度與作品的深度。仇恨是文學的力量,不能仇恨與不能愛一樣是一件糟糕的事情。由仇恨而上升至人道主義的愛,才是有分量的。我一直不滿意我的悲憫情懷的重量。但是,一個人做人、做事都必須要限定自己,不能為了取消自己的短處而犧牲了自己的長處。換一種角度來看,“短處”之說也未必準確。
2. 記憶與成長
徐妍:剛才我們談論水的時候,實際上也在一直談論著另一個話題——記憶。如水一樣的時光實際上也是如水一樣的記憶。說到記憶,我們盡管不知道它在一個人的一生里究竟有多長,但總是大約知道它的起點。我的經驗是我隱約從四歲開始記事兒,以前是一片混沌,仿佛一眨眼就長到了四歲。您最早的記憶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
曹文軒:說到我的記憶,有點不可思議。我居然將我在一歲時的個別情景敘述給我的父母聽,他們感到十分吃驚,因為那都是真正發生過的事情。至今我還依稀記得我的二爺去世時的情景。那是一個十分炎熱的夏天,臨河的草棚下,有一些不停地走動著的大人。吹鼓手來了,我大聲叫著,讓奶奶躲起來,因為在我看來,這些吹鼓手的到來,是要將老人帶走的,母親立即用手捂住了我的嘴巴。多少年后,當我向大人們敘述這一情景時,他們絕不肯相信,因為那時我才一歲。使他們感到疑惑甚至微感恐怖的是,這些事情后來沒有人對我講過,完全是我的當時的記憶。
徐妍:在我的體驗里,每個人的記憶長廊里都有第一張黑白色的老照片。雖然后來又陳列了許多張讓自己更為得意的生活照、風景照、明星照、結婚照等,但那第一張以童年的又黑又亮的目光拍攝的曠野或水鄉照片,在時間的沖洗下總是讓我難以忘記。而且,越回想越清晰、越有味道。可能在回想時,增添了一些再造的成分,但底色依然是黑白的。它的構成要素竟然是生根的。您現在能夠敘述您童年記憶中的第一個完整的事件嗎?它為什么讓您至今難忘?
曹文軒:我要講的這件事很難說是第一個完整的事件,但它最深刻地存在于我的童年記憶中。不知道是幾歲時發生的事情,因為我從未向家里人講過這件事——它一直在我的記憶的一角默不作聲地藏著。我的童年是在貧窮中度過的,童年留給我的許多記憶中,最刻骨銘心的是饑餓。饑餓的感覺是一種讓人心慌、發昏的感覺,一種想啃石頭的感覺。我的家設在父親任校長的學校,母親的工作就是給老師們燒飯。當時的老師們是有糧食供應的,因此他們總還能吃上飯。大約是在春季,一個暖烘烘的日子,我肚子餓極了,想找點東西吃。就是在這一天,我做了一件不光彩的事情。我在將近中午的光景,趁母親去河邊洗菜的空隙,悄悄溜進了廚房,揭開鍋蓋,一股熱氣頓時升起,等我看清楚了鍋中白花花的米飯之后,竟然不害怕燙,抓起一把米飯就往嘴里塞去,而就在這時,廚房門口出現了一個人影,我一掉頭就看見了他——那個長著威嚴長眉、面容永遠冷峻的語文老師。他就那樣看著我,很漠然的樣子。我一手拿著鍋蓋,一手還捂在嘴上,那只手上沾滿了米粒。我低下頭去。不知過了多久,門口的腳步聲漸漸遠去了。我將鍋蓋重新蓋在鍋上,趕緊逃出了廚房。就在那一天,我知道了什么叫自尊,什么叫羞恥。
徐妍:有人說,一個人其實在童年時就已經注定了是否能夠成為一名作家。這句話的意思我理解為:成為一個作家的前提就是首先要具有童年的記憶。我認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擁有過童年的時光,但不是每一個人都擁有童年的記憶。您的小說大多采用追憶的視角追溯從前的時光,這除了出于小說敘述學方面的考慮,我猜想,也一定與您記憶里儲存了許多珍貴而有趣的童年記憶有關。甚至可以說,正是這些珍貴的記憶構成了您小說豐厚的生活經驗、鮮活的生活氣息。這樣,在閱讀您的作品時,我就時常感到好奇,您對于記憶中的事件敘述得那樣鮮活、細微,是由于您天生就有一種驚人的記憶力,還是您具有超出尋常的對記憶的虛構能力?或者兩者兼有?或者有其他原因,比如天生有一顆敏感、豐富的心靈?
曹文軒:很難解釋清楚。童年確實留給了我太多太多的東西,幾乎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我對那些靠胡編亂造的作家,一直感到不可理解,他們的記憶呢?他們的經驗呢?他們在說到童年時——在我的感覺上,他們的童年幾乎是一片空白,他們在開始創作時,仿佛是赤手空拳的。這樣的創作,我一天也進行不下去。我在寫小說時,總要找到一個依托——經驗的依托。這個依托,十有八九是與童年的印象有關的。它是土壤,然后我再想著如何讓我的小說在這塊土壤之上生長。只有這樣,我心里才能感到踏實。說白了,先得有個影子。信口開河,無風起浪,總叫人心里有點不安。當然,我的虛構也是很厲害的。這個能力,又要感謝我的童年,因為,是那清湯寡水的日子培養了我的想象力。人在什么也沒有的狀態下,才會想象——用想象來充饑,用想象來給自己造一張大床,用想象來為自己穿上一套漂亮的衣服,用想象來彌補一切缺失與空白。說到心靈的敏感,我想大凡是作家,都會有這份敏感的。沒有,還寫什么小說?至于說是否是天生的,這就無從考證了。
徐妍:以我的觀點,記憶太豐富了會很容易讓人產生沉重的懷舊情緒。所以,有一種人,恍惚地生活在記憶里。但是,您雖然擁有那么豐厚的記憶,又似乎沒有被記憶所累。無論是在文字上,還是在日常生活中,您都是一個從容而富于行動的人。您是怎樣處理記憶世界與現實世界的關系的?
曹文軒:這是一個很有見地的問題。你已看到,我并未一味沉湎于我的童年記憶。一個作家,其實是很難原封不動地動用童年的生活的。他的文字也不應當到童年止。我是現在時間中的人,我只能帶著現在時間所給予的色彩去回溯已經過去的時間。那個“過去”的礦藏,如無“現在”的點化,是無意義的、無價值的,甚至是不能夠被發現的。后來的經驗,后來的知識,將浸潤“過去”、照亮“過去”,這番浸潤與照亮,才使“過去”得以轉化為有用之才。事實上,我在動用“過去”時,用的是現在的價值觀與審美觀。我是在為現在寫小說,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小說不是回憶錄。一味懷舊,是一種沒有是非、沒有立場的表現。我曾做過一個表述:“經驗”與“經歷”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一個人是靠經驗寫作,而不是靠經歷寫作的。童年只是作為經驗而活在我的小說之中的。
徐妍:我一向認為,童年的記憶只有在成人的視角里才能復活,因為無拘無束的童年生活只有在追憶里才能算是在理性中度過。所以,您一再重構您童年的記憶。我似乎能夠理解您對童年礦藏的開采:每一次開采,這些童年的礦藏都轉化成您成年世界的財富。我很想知道:每一次開采過程中,哪些礦藏您格外看重呢?
曹文軒:淳樸的價值觀、沒有被破壞與污染的風景、富有人性的地方風俗、沒有多少附加條件的人情、炊煙與號子,等等。
3. 苦難與成長
徐妍:我清晰地記得在一次關于“低齡化寫作”的討論會上,您曾經認為現在的孩子已不知什么是真正的苦難了,他們甚至就沒有什么苦難。當時,我不完全贊同您的觀點,因為我認為現在的孩子在孤獨地承受著另一種難以言說的苦難,比如心靈的重負,社會、家長將自己所有沒有實現的希望強加給他們的達到甚至超越他們承受能力之極限的重負。我知道,您的判斷是以您的童年作為參照的,我由此想到您的童年一定是與苦難聯系在一起的。所以,我很想請您談談,您是如何理解大河邊上的童年時的苦難的含義的?苦難在大河邊上,是否等同于物質的貧窮,而在精神方面,卻具有了讓今天孩子艷羨的富足的自由?
曹文軒:我堅持我的看法,現在對孩子的痛苦是夸張的。而且,這主要是自以為有責任感的成人干的,是他們在扮演小孩的代言人與救世主的時候將孩子的痛苦放大了。現代人,由于受享樂主義的影響,往往都要夸大痛苦,以為只有他們這個時代的人才痛苦,才在水深火熱之中。他們對痛苦過于敏感,稍微有點痛苦就委屈,就叫苦連天。現代人在痛苦面前缺乏先人們那樣的風度。我們將這種感覺傳到了孩子那里,使他們變得十分脆弱,并且極容易在痛苦面前畏縮不前。他們很容易沉浸在對痛苦的感覺里,并且不能自拔。如果我們不是那樣添油加醋地去敘述他們的痛苦,而是向他們無聲地傳達一下自己在痛苦面前的堅韌與冷靜,情況將會是怎樣?請注意一下日本,在現代化的今天,他們并沒有對現在的小孩的處境無節制地渲染痛苦,相反,他們在教育中還盡可能地創造條件讓孩子去經受痛苦的洗禮。那年夏天,我們驅車行駛在新疆的火焰山下,柏油路的路面已經被炎炎熱日曬得幾乎熔化,一隊日本中學生卻在路上默默地行走著。他們的背后是紅色的鐵質的山。為了防止水分的蒸發,他們戴著口罩。不用憐憫他們,他們也不會接受憐憫。一個民族沒有這么一點精神,而是老在那兒自說自話地大談特談痛苦是沒有意義的,也是沒有意思的。我感謝大河邊上的苦難,由衷地感謝。我不同意物質的苦難是一種低于精神苦難的見解。物質的苦難,是一種深刻的苦難,這種苦難是實在的,而且它既是肉體的也是靈魂的。我的小孩在考大學時,每天夜里要復習到很晚,但我們是陪伴著他的,并且會不停地去伺候他。所以,我對他說:“你吃的這一點苦算什么?你到了夜里,會有人給你端上牛奶,而你爸在你這樣的年紀時可能會餓著肚子在月光下割麥子。你苦什么,難道你還比你老子餓著肚子割麥子苦嗎?”現在的孩子失去自由了嗎?我們那時候的孩子就有無邊無際的自由嗎?
徐妍:人們常說,苦難對于一個作家來說,是一筆豐富的財富。您的文字,也經常書寫苦難對您少年時期成長的意義。比如,您曾經寫道,一次您到八里地外的地方看電影,深夜回來,餓得不成樣子,但又懶得生火燒飯,父親對您說:“如果想吃,就生火去做,哪怕柴草在三里外堆著,也應去抱回來”3,在那天晚上,您的父親奠定了您一生積極的生活態度。如果時間能夠倒流,您愿意選擇今天都市里的生活,還是從前的大河邊上的生活?
曹文軒:無法選擇,正如舊戲文里說的一句話:“一切是天命,半點不由人。”
與一位古典風格的現代主義者對話之二
地點:曹文軒先生的書房。
旁白:這天上午九點,我如約來到了曹文軒先生的書房,專訪曹文軒先生的文學觀。書房選擇了紅木色與黑胡桃色營造自己的主色調。紅木色的書架高接房頂,飽滿地佇立在兩壁。梵高的《向日葵》盛開在用加拿大松板制作的墻壁上。
1. 路與夢想
徐妍:以我對您的文學作品的閱讀經驗,到目前為止,您的作品可以分為兩個階段。長篇小說《草房子》誕生之前的小說為第一階段,代表作品與作品集有《憂郁的田園》《暮色籠罩下的祠堂》《紅葫蘆》《薔薇谷》《少年王》《山羊不吃天堂草》等。這一階段的作品體制多為短篇,相對而言,故事純凈,情節呈現單線發展,人物大多符合并服從作品的審美原則。第二階段從《草房子》開始,經《紅瓦》《根鳥》,到在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細米》。這一階段的作品,體制多以長篇為主,故事較為復雜,情節出現復線或者循環地向前發展,人物大多趨于多維空間。兩個階段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您的小說都是一個夢想的空間。這對于當下中國小說對夢想的放逐而言是一個反向。可以說,您的小說是一個孤獨的存在。因此,我很驚異:在這個越來越物質化的時代,您的小說為什么反復書寫夢想?
曹文軒:這個世界太灰色、太實際、太平庸、太物質、太缺少浪漫,也太缺少詩意。這是一個稍微有人文情懷的人都不能容忍的世界,但我們無能為力。因為,物欲橫流,排山倒海,勢不可當。人文學者在這樣的格局中,顯得有點滑稽。他們甚至被這個世界所利用,做了許多有背一個人文主義者身份的事情。一個軟弱的人文主義者,被這個世界收買,是件很容易的事情。我能怎樣?真的是奈何不得。還好,我會寫小說。小說的功能這時就顯出來了。它是哲學、政治學都不能取代的。小說可以寫美,寫夢想——即使人已物化,在他的內心深處也仍然會有一種對美的向往和對夢的呼喚。這也是基本人性,大概也正是在這一點上,人才為之人,人也才有了被救贖的可能。我的骨子里始終有一種浪漫主義的情愫,是拂之不去的。我的小說大概不是嚴格意義上寫實主義的東西,更不是那種不嫌屎尿、不避蒜臭、不拒蒼蠅的新寫實主義。我有強烈的現實精神,但我不愿落入現實的滾滾風塵。我的靈魂中,有飛揚的一面。夢是一種精神,夢是一種做人時不能忘記的高度,是人在做人時的必需品質,夢也屬于美學范疇。當然這個夢是廣義上的,不是狹義上所說的夢。文學這個東西的誕生,依我看,本就是因為人的夢想。它誕生以來,其主要功德,大概就是幫助人保持住了一份夢想。
徐妍:在您的小說里,夢想的空間各有色彩。在短篇小說里,大多是單顏色:有時,是純白色的,如《十一月的雨滴》;有時,是淡紫色的,如《水下有座城》;有時,是鉛灰色的,如《田螺》;有時,是橘黃色的,如《甜橙樹》……在長篇小說中,夢想的色彩常常不斷疊加、變換。如《根鳥》里,有玫瑰色的少年夢,有血紅色的欲望之夢,有黑色的絕望之夢,也有回歸故地的潔白之夢,但是,就是沒有現代主義小說中的讓人恐懼與戰栗的夢魘。您能夠大致談一下您小說中夢想的美學原則嗎?
曹文軒:向上、飛翔、遠離垃圾、守住詩性、適度憂傷、不虛情假意、不瞪眼珠子、不揮老拳、憐憫天下,等等。
徐妍:我在欣賞這些夢幻的美妙之時,也有一種疑惑:這些古典的夢想在審美空間里的魅力是否會在現實世界里不可避免地顯得有點虛弱,或者說這是一種逃避?
曹文軒:我一直懷疑對小說的社會功利主義定位。對小說的社會性希望常常是過分的。小說有這么大的能耐嗎?我們從來也沒有看見過一篇小說使一輛坦克停止了前進,我們也從來沒有看到過一篇小說讓一個貪污犯將拿回家的公家的沙發又扛了回去。我一向對小說的戰斗性不以為然。如果小說真的有立竿見影的效能,真的有子彈的效能,魯迅當年為什么放棄小說而專注于雜文?好端端的一個小說家,就這樣半途而廢了,可惜!但魯迅是偉大的,他是憂國憂民,他是從民族的利益出發,他知道小說這玩意兒沒有雜文那樣能刀起頭落,小說這玩意兒對付現實不怎么中用。這樣來看,我們就會對小說的功能有一個恰當的認識。說小說是一種逃避,我以為,也未嘗不可。小說能承當逃避者的庇護所,也是件功德無量的事情。逃避也是需要勇氣的。身處監獄,能動逃跑的念頭,就是一份勇敢,如果敢于實施這個計劃,那么他就太勇敢了。小說的勁是慢慢地顯露的,是那種喝起來不上頭,但酒勁上來是要將人徹底打倒的酒。這么說,它的力量卻又是意識形態的其他門類所不可相比的。
徐妍:您在學術的世界里是一個理性思維很強大的學者,而您在文學的世界里,又是一個夢想家,您的兩個思維似乎能夠和睦相處。但我還是有所憂慮:想象力與邏輯力是否有沖突的時候?比如,是不是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有一天,您本來在調動想象力,上場的卻是邏輯力?
曹文軒:見過那個蓬蓬松松地豎立著一頭灰白毛發的美國人唐金嗎?他策劃著讓哪一個拳擊手上場,還會搞錯嗎?心里是早計算好了的。想象力與邏輯力,是兩個鬼,我很清楚它們的性質,我會掌握住它們的,它們不可能亂來。但我要說的是,有時讓它們對打一場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其實它們是常常結伴而行的。
2. 路與美感
徐妍:您在《紅瓦》代后記中說的“美感與思想具有同等的力量”,讓我印象格外深刻。可以不夸張地說,您是當下唯一一位敢于公然地談論美感并書寫美感的作家。或者說,在作家們紛紛為現世寫作的時候,您卻在為未來寫作。所以,您的小說在夢想的空間里一直將美感作為一種精神向度,甚至一種準宗教,以此救贖這個日漸麻木、下沉了的社會。我記得您很偏愛地一再指出早期的短篇小說《薔薇谷》中的“美讓絕望者重新升起希望”的可能性,也一再將您的情感投入具有美感的人物與風景中。但是,在這個強大的、實用的物質社會,您如何看待美感對這個社會及人心的救贖力量的有限性?
曹文軒:如果連美都顯蒼白,那么還有什么東西才有力量?是金錢?是海洛因?如果一個人墮落了,連美也不能挽救他,那么也只有讓他勞動改造,讓他替牛耕地去,讓他做苦役去了。還剩下一個叫“思想”的東西。思想確實很強大,但思想也不是任何時候都強大。思想有時間性,過了這個時間,它的力量就開始衰減。偉大的思想總要變成常識。只有美是永恒的,這一點大概是無法否認的。當然,美不是萬能的。希特勒不是不知欣賞美,但這并沒有使他放下屠刀,一種卑賤的欲望使他那一點可憐的美感不堪一擊。
徐妍:您在舉世皆丑的寫作風尚中,依然堅持美感的寫作,是否感到孤單和困惑?有沒有改弦易轍的打算?
曹文軒:負隅頑抗,活路一條。但是,我會在以后的寫作中加強思想的滲透,讓它與美感成為和諧的搭檔。
徐妍:我猜想,您可能只是在日常世界里對自己的美感寫作感到猶疑,但只要一進入您的文學世界,美感對您的召喚就會讓您忘記所有的猶疑與困惑。于是,您的小說,越來越堅定自己的美感追求,甚至將美感作為一種信念。這個判斷,來自于對您的小說的跟蹤閱讀。僅以對您第二階段小說的閱讀為例。我認為《草房子》是由意象連綴起來的故事,《紅瓦》屬于散文體的意境寫作,二者都表現出對廢名、沈從文、汪曾祺古典風格的承繼。但至《根鳥》,發生了一些變化:在古典風格的基點上,注入了現代主義的隱喻,但“峽谷”“白鷹”“百合”“云煙”等古典原型意象依然是閃亮之處。尤其是,“夢想”就是“美感”的同義詞。近著《細米》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在成長小說的外形里,您竟然將美感作為一種與《根鳥》中的“夢想”同樣圣潔之物。還有您去年發表的短篇小說《甜橙樹》,構思就是以美感為中心的。但是,我有一種感受:您對美感的傾心似乎已經達到了一種極致。當美感成為一種理念時,您是否有所警惕?正是美感的極致破壞了小說的美感?或者說,我認為,美感是一種泉水山間流的自然形態,而不是理念。
曹文軒:我不會去刻意地制造美感,順其自然。我會在以后的創作中時刻提醒自己,矯情本是丑陋的。而且,對美應當有更加廣闊與深入的理解。
3. 路與存在
徐妍:您的小說雖然將古典家園作為小說的終點,但您更著力的則是人物在路上遇到的各種考驗。特別是,您選擇了成長一族作為小說的中心人物,更有利于表現在各種命運的考驗下人性的復雜性。因為人在成長中,一切都是變數。這使得您小說中的古典主義與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廢名、沈從文,甚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汪曾祺的古典主義有所不同。如果說您的具有古典主義精神的前輩也是在古典主義的美學范疇內思考著現代社會的某些現象性問題的話,那么您則直接以古典主義精神關注現代社會的哲學性本質——存在。您的人物一方面是古典主義精神的寄寓,另一方面也是現代主義的存在。所以,我很關心這樣一個問題:您認為古典主義的寫作能不能關懷現代主義寫作中關懷的形而上的問題?
曹文軒:毫無疑問,能。事實上,古典主義的小說一直也在關注著形而上的問題,只是與現代主義小說相比,形而上的程度有所區別罷了。古典小說沒有只是關注那些沒有時間延長的眼前的事,它關心的仍然是千古不變的問題,只是與現代主義小說相比,這些問題不那么玄學罷了。另外,我們需要搞清楚,這里的古典主義與現代主義到底是指一種內容還是指一種形式,是指說的方式還是指被說的對象。卡夫卡的小說是現代主義的,這一點毫無疑問,但卡夫卡的形式其實與我們傳統的小說形式并無區別,也就是說,他用的是一種很正常的寫法,里面沒有什么現代花活與噱頭。我用一種很古典的風格,一樣可以寫出一個很現代的小說主題。
徐妍:在我看來,所謂的古典主義只是現代社會里的誕生物。而您的古典風格恰恰是一位現代主義者的另一種表現方式。這一點,在您的作品中體現得最明顯。在您古典的美感表達里,同樣思考著與“惡”“荒謬”“欲望”等關鍵詞相關的現代主義作家們思考的問題。但是,我就有一個問題:如果上述現代主義的這些關鍵詞影響了美感,您將如何取舍?
曹文軒:不是取舍,而是讓那些東西在美的面前轉變——要么轉變,要么滅亡。你在花叢面前吐痰害臊不害臊?你在一個純潔無瑕的少女面前袒露胸膛害臊不害臊?我記不清是哪一篇小說了,一個壞蛋要對一位女士動以粗魯,而一旁一個天使般的嬰兒正在酣睡之中,那個女士對那個壞蛋說道:“你當著孩子的面就這樣,你害臊不害臊?”那個壞蛋一下子就泄氣了。當然這只是小說,生活中,一個壞蛋才不在乎這些呢。但連美都不在乎的人,你還能有其他什么辦法嗎?只有訴諸法律了。
徐妍:我發現您的小說在人物的塑造上有一個普遍性的規律——將善與惡都不寫到極致。如《紅瓦》中的王儒安與喬桉。您常常將人物置于“之間”的地帶。這符合人性本身,但同時,是否使得您的小說缺少現代作家筆下人物的深刻性?
曹文軒:我不光是寫小說的,還是研究小說的,因此我比誰都更加清楚現代小說的那個深刻性是怎么回事,又是怎么被搞出來的。無非是將人往壞里寫,往死里寫,往臟里寫,寫兇殘,寫猥瑣,寫暴力,寫蒼蠅,寫濃痰,寫一個人在實際生活中不愿意遇到的那些東西。現代小說的深刻性是以犧牲美感而換得的。現代小說必須走極端,不走極端,何有深刻?我不想要這份虛偽的深刻,我要的是真實,而且,我從內心希望好人比實際生活中的好人還好,而壞人也是比實際生活中的壞人要好。但說不準哪天我受了刺激忽然換了一種心態,我也會來寫這種深刻性的,我對達到這種深刻的路數了如指掌。
注釋:
[1-3] 曹文軒,《追隨永恒》,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8年。
徐 ?妍:中國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
曹文軒:作家,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