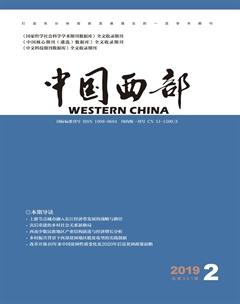基于宏觀視角的四川省農民收入質量評價
李鳳至
〔摘要〕?本文從宏觀視角構建了基于收入的充足性、結構性、成長性、成本性和知識性五個維度的農民收入質量指標體系,利用四川省1997~2016年的數據,得到農民收入質量指數,并分析了農民收入質量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結果顯示:與全國相比,四川省農民收入質量還相對較低,且主要依賴收入的充足性,其他維度的貢獻依舊較小;經濟增長對農民收入質量的帶動作用也相對較小。因此,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過程中,對農民收入的關注應從收入數量轉到收入質量上,尤其應注重增強經濟發展對農民收入質量的提升作用。
〔關鍵詞〕?農民收入質量;熵值法;協整回歸;四川省
〔中圖分類號〕F323.8?〔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0694(2019)02-0061-10
一、引言
黨的十九大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并強調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要求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順應了億萬農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對“三農”工作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是新時代做好“三農”工作的總抓手,對促進“三農”發展具有重大現實意義。《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更把堅持農民主體地位作為基本原則之一,即把促進農民共同富裕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促進農民持續增收,不斷提升農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農民收入問題是“三農”問題的核心,而隨著我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為向高質量發展,對農民收入的“振興”也不應停滯于數量的增長,更該關心農民收入來源、收入的穩定性等真正體現農民收入優劣的指標。國內外學術界一直高度關注農民收入問題。國外相關研究盡管與收入質量的內涵相關,如:Du,Park 和 Wang(2005)指出較高的受教育水平能夠在未來獲得更高的收入;〔1〕Leonardo Corral and Thomas Reardon(2001)認為在農民家庭收入中非農收入占 41%,鄉村非農收入遠比農村工資收入更重要,這和收入的結構性相關;〔2〕Lerman(2004)發現規模化生產能夠提升農業的生產效率,擴大農村的規模化,能夠增加農產品的銷售量,進而提升農民的收入,〔3〕但卻未明確提出收入質量的概念。
國內研究主要集中于農民收入現狀及其影響因素、城鄉收入差距、農民增收促進對策研究等幾個方面,也有部分學者從財產性收入等收入結構方面進行研究。最早提出收入質量概念的是孔榮和王欣,他們在2013年對農民工的研究中指出,收入不僅有量的規定,更應有質的規定,定義了收入質量的五個維度:充足性、穩定性、結構性、成本性和知識性,同時還指出高質量的收入應表現為“數量充足、結構合理、成長性強、知識含量高、獲取成本低”的特點,并分析了影響農民工收入質量的主要因素。〔4〕〔5〕但這一定義主要是針對農民工的收入質量,而農民的收入質量確與農民工的收入質量并不相同。王欣(2014)又進一步指出我國農民工收入質量不高。〔6〕鄧鍇(2014、2016)對農戶收入質量進行定義,同時對收入質量和中西部農戶貸款行為關系進行考察,分析了收入質量對農民工信貸需求的影響。〔7〕〔8〕譚梅云(2017)指出收入質量是對收入做出整體判斷的綜合指標,它以收入的數量多少作為主要評判依據,并利用收入的充足性、穩定性、結構性、成長性和知識性的概念及特征,對農戶獲取的收入進行綜合評價。〔9〕任吉?力(2016)進一步從宏觀角度分析,認為收入質量是農民收入的充足性、結構性、成長性、成本性和知識性的總體衡量,并研究其與消費和投資的關系。〔10〕
綜上所述,現有文獻對農民收入的研究大多單純著眼于農民收入的數量視角,但收入的數量并不能精準地表現農民實際收入的優劣程度。國外研究雖對收入質量略有涉及,但尚未明確給出收入質量的定義,只是初步揭示了收入數量與收入質量其他維度間存在密切的相關關系,忽視了收入質量各要素間的聯系。國內當前對農民收入質量的研究還較少,且現有研究大多又基于調研數據,存在農民對自身評價的不客觀性,影響研究結論的精準性,從宏觀視角著手來研究農民收入質量的更少。
四川省作為農業大省,從農民收入數量視角轉為收入質量并從宏觀視角出發評價農民收入質量的現狀,不僅符合鄉村振興的總要求,還對《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的具體實施具有積極意義。本文借鑒任吉?力(2016)對農民收入質量定義:以收入的數量為評判基礎,利用收入的充足性、結構性、成長性、成本性和知識性5個維度,判定農民收入的水平和獲取能力,〔10〕試圖對農民的收入進行綜合評價,以真實體現農民實際收入的優劣程度。并以宏觀視角出發,采用四川省1997~2016年的相關數據,運用熵值法測算出四川省農民收入質量指數及五個維度的指數,對四川省農民收入質量現狀進行分析,通過協整方法分析四川省農民收入質量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
二、四川省農民收入質量的測度
1.農民收入質量的指標構建
根據數據的可獲得性,以及為了避免指標之間存在因果關系或者相關關系而出現多重共線性的原則,同時結合任吉?力(2016)構建的指標體系,本文構建了農民收入質量的指標體系(詳見表1),以測度農民收入質量指數,進而評價四川省農民收入質量的現狀。
(1)收入的充足性。收入的充足性(A)是指收入總量是否滿足家庭生活和生產等的資金需求。目前宏觀統計數據中能夠反映農民收入充足性的指標主要有農民總收入、現金收入和純收入,而現金收入主要衡量農民家庭現金流入,不能反映農民全部收入,也不能完全反映農民收入是否充足,指標不具備典型性。所以,本文采用農民總收入A1、農民純收入A2和農民收入結余A3來衡量充足性指標。〔10〕
(2)收入的結構性。收入的結構性(B)主要是指收入來源渠道數量,以及各來源的占比情況。收入來源不同,收入比例不同,農民收入增長路徑就會不同。目前宏觀統計中我國農民收入主要來源為經營性收入與工資性收入中的一種,本文采用主要收入來源比例B1即:Max(經營收入,工資性收入)/總收入,轉移性收入比例B2。而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對比B3可以衡量外部結構性,因此也作為度量收入的結構性指標。
(3)收入的成長性。收入的成長性(C)與微觀視角下收入質量概念中的收入穩定性相對應,由于受到物價、通貨膨脹等客觀因素影響,如果收入與往年持平,則實際收入是減少的,所以采用成長性代替穩定性更準確。本文采用農民的經營性收入增長率C1、工資性收入增長率C2和轉移性收入增長率C3三個指標衡量農民收入成長性。其中,增長率的計算為:某來源收入增長率=1-前一年某來源收入/當年某來源收入-當年CPI增長率,減去CPI是為了消除物價及通貨膨脹的影響。
(4)收入的成本性。收入的成本性(D)是指獲取收入發生的各種實際費用、機會成本和心理成本,由于機會成本和心理成本難以度量,這里暫不考慮。本文主要采用以下三個指標衡量收入的成本性:“家庭經營費用現金支出”D1衡量農民的實際經營成本,“購買生產性固定資產支出”D2衡量農民用于未來生產的費用支出,“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指數”D3來衡量農民整體環境下的生產成本。
(5)收入的知識性。收入的知識性(E)指在收入中所包含的知識含量與技能經驗要求。采用“農村居民家庭勞動力受教育年限”農村居民家庭勞動力受教育程度根據學制加權計算。E1衡量勞動力受教育程度,使用“農村成人技術培訓比例”通過農村成人文化技術培訓學校結業生數除以農民總人口數計算而得。衡量農戶的技能水平E2。
2.收入質量的測算方法
由于收入質量的三級度量指標較多,需要對每個三級指標確定相應的權重系數,從而測算收入質量指數。確定指標權重的方法通常分為兩類:一類是主觀方法,如專家打分法、層次分析法、經驗判斷法等;另一類是客觀方法,如熵權計算法、主成分分析法等。由于指標的權重對被評價對象的評價結果可能產生較大影響,為盡可能客觀,本文采用客觀方法來計算指標的權重。具體選用熵值法來確定每個指標的權重,具體計算主要參考Xu D(2018)的步驟。〔11〕
3.四川省農民收入質量測度結果
(1)收入質量指標體系的權重計算結果。通過四川省統計年鑒、中國農村統計年鑒等對四川省1997~2016年的相關宏觀數據進行整理,利用熵值法對各三級指標賦權(詳見表2)。
(2)農民收入質量指數的計算結果及分析。依據上述三級指標權重,對四川省農民收入質量的指數以及五個維度的指數進行計算,同時,為了對四川省農民收入指數的高低水平進行判斷,本文還采用全國的1997~2016年的相關數據,計算全國農民收入質量作為參考標準(詳見表3)。
為了進一步分析四川省農民收入質量現狀,以及其五個維度的波動趨勢,還繪制了農民收入質量指數和其五個維度的趨勢圖。其中,雙實線表示中國農民收入質量,單實線表示四川省農民收入質量,兩條虛線是各自的趨勢線,5條帶標記的實線分別表示四川省農民收入質量的五個維度。??根據收入質量的測度結果(表3)可知:
第一,與全國農民收入質量水平相比,1997~2016年,四川省農民收入質量還處于相對較低的水平,且增長趨勢相對緩慢。這與四川省作為全國扶貧開發工作的重點省份之一,貧困面廣、貧困人口數量多、程度深,制約發展因素較多的特質密不可分。
第二,隨著“三農”政策力度的持續加大,農村經濟不斷發展,就業機會逐步增多,農民收入也從單一向多元化發展。自2009年起,農民收入數量得到明顯增加,收入質量出現加速提升態勢,且農民收入結構性略有優化,成本性略有降低,總體收入質量有明顯的提高。
第三,農民受教育程度整體較低,知識的欠缺導致對新事物、新技術的接受和適應更慢,農民收入始終大多依靠務農或外出打工,財富積累始終依靠“人掙錢”而不是“錢生錢”。盡管當前收入質量指數有所增長,但主要還是依靠收入充足性的增長,而其他維度對收入質量貢獻依舊較小,尤其是收入的知識性和成長性始終沒有得到明顯的提高。
三、四川省農民收入質量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分析
1.變量說明和數據來源
選取四川省地區生產總值(GDP)作為經濟增長的衡量指標,在實際計算時,采用人均GDP來度量;前文測度出來的收入質量指數作為四川省農民收入質量的衡量指標,用IQI表示。同時做農民人均純收入與人均GDP的關系檢驗,以此與收入質量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形成對比,農民人均純收入用I表示。數據選取1997~2016年,均依據歷年《四川統計年鑒》整理所得。
2.實證分析
(1)單位根檢驗。在對經濟變量的時間序列進行分析時,需要對變量做平穩性檢驗,判斷各變量是否為平穩的時間序列。運用ADF單位根檢驗對所選取的變量GDP、IQI和I進行單位根檢驗,檢驗這三個變量是否是平穩序列。若不平穩,則對其進行差分處理再進行單位根檢驗。檢驗結果表明,GDP、IQI和I二階差分后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是平穩的,即:GDP、IQI和I為二階同階單整,平穩檢驗的結果詳見表4。
(2)協整檢驗。根據平穩性檢驗,三個變量均為二階單整,可能存在某種平穩的線性組合,這個線性組合能反映變量之間長期穩定的比例關系,即可能存在協整關系。本文選用E-G兩步法進行檢驗,首先對收入質量與經濟增長關系進行檢驗,步驟及結果如下:
第一步:用OLS估計協整回歸方程,經過調整得到長期回歸整方程為:
IQI=0.218451+0.000006GDP
(0.026253) (0.0000013)
注:括號中的數字為相應系數對應的標準差,其系數在1%的水平上均顯著。調整后的R2=0.54,DW=1.951,不存在自相關。
第二步:殘差平穩性檢驗,仍采用ADF檢驗(詳見表5):
由表5可得,殘差的ADF值小于1%的臨界值,殘差序列為平穩序列。所以,GDP和IQI之間存在長期均衡的關系,即從長期看,經濟增長對農民收入質量有具有拉動作用,但從變量的系數來看,目前這個拉動作于還較小,當GDP增加1個單位,農民收入質量才提高0.000006,這個提高的程度基本可以忽略不計。
而采用同樣的方法,檢驗出農民人均純收入與GDP之間的長期關系,結果表明農民人均純收入與GDP之間存在協整關系,但是經濟增長對農民收入數量的拉動作用比對收入質量的拉動作用更大。
(3)Granger因果檢驗。上述檢驗表明:農民收入質量與經濟增長、收入數量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但這種均衡關系是否構成因果關系,需進一步驗證。本文借助Granger因果檢驗來判斷四川省農民收入質量與經濟增長之間、農民收入數量與經濟增長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根據AIC準則反復假設,最后確定其滯后階數為2,Granger因果檢驗的結果詳見表6:??Granger因果檢驗的結果表明:GDP是IQI和I的Granger原因;I是GDP的Granger原因,而IQI不是GDP的Granger原因,即:經濟增長是農民收入數量和收入質量提高的原因,農民收入數量能拉動經濟的增長,而農民收入質量提高不是經濟增長的原因。
四、結論與啟示
本文利用四川省1997~2016年的數據,采用熵值法對四川省農民收入質量指數進行測度,分析四川省農民收入質量的現狀,并進一步考察了農民收入質量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1.結論
(1)與全國農民收入質量水平相比,四川省農民收入質量還處于相對較低的水平,且增長趨勢相對緩慢;收入質量指數的增長主要依靠收入充足性的增長,其他維度的貢獻較小,尤其是收入的知識性和成長性始終沒有得到明顯的提高,對收入質量的提升貢獻較小。
(2)當前四川省經濟增長對農民收入質量的帶動作用仍然較小,也導致農民收入質量相對較低,未能通過收入質量的提高帶動消費從而促進經濟增長,但收入數量的增長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逐漸凸顯。
2.啟示
(1)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應從關注農民收入的數量轉化到關注農民收入的質量,并注意結合四川省農業農村的自身特質,制定適合四川省的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細則,推進精準扶貧的具體工作,以提高農民收入質量整體水平,加快農民收入質量的增長速度,不斷縮小與全國整體水平的差距,真正實現農民生活富裕。
(2)在關注農民收入時,不僅應關心農民收入的數量,更應關注其收入的成長性、結構性、知識性和成本性,才能真正地了解農民的真實收入的優劣程度,才能更好地制定三農扶持政策。如:在提高農民收入時,不僅應注重農民收入穩步增長,還應穩定物價,提升農民收入的成長性。可以大力支持和鼓勵農民就業創業,拓寬農民就業渠道以及促進農村傳統產業的提升,優化收入結構;重視農村教育和技術培訓,提供定點定時的農民知識和技能培訓,不斷培養新型職業農民,增強農民收入的知識性和穩定性;制定各種支農惠農政策,健全農村農業基礎設施體系,降低農民收入的成本性。
(3)在大力發展經濟發展的同時,還應堅持“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服務鄉村”的理念,加大農村地區的經濟發展,結合農村地方特色,發展鄉村產業,增強經濟發展對農民收入質量的帶動作用,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不斷提高農民收入質量,進而拉動農民消費,促進地區經濟增長,形成良性循環。
參考文獻:
〔1〕Du Y,Park A,Wang S.Migration and Rural Poverty in China[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5,(04).
〔2〕Leonardo Corral,Thomas Reardon.Rural Nonfarm Incomes in Nicaragua[J].World Development,2001,(29).
〔3〕Lerman Z.Policies and Institutions for Commercialization of Subsistence Farms in Transition Countries[J].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2004,(03).
〔4〕孔?榮,王?欣.關于農民工收入質量內涵的思考[J].農業經濟問題,2013,(06).
〔5〕王?欣,孔?榮.影響農民工收入質量的因素研究——基于10省份調查數據的實證分析[D].統計與信息論壇,2013,(04).
〔6〕王?欣.農民工收入質量評估研究[D].西北農林科技大學,2014.
〔7〕鄧?鍇,孔?榮.收入質量對農民工信貸需求的影響研究——來自河南、山東、陜西的數據[J].經濟經緯,2016,(01).
〔8〕鄧?鍇.收入質量對中西部農戶貸款行為影響研究[D].西北農林科技大學,2014.
〔9〕譚梅云.基于農戶收入質量的信貸員授信偏好影響因素研究[D].西北農林科技大學,2017.
〔10〕任?吉?力,孔?榮.基于驗證性因子分析的農戶收入質量研究[J].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04).
〔11〕Xu D,Deng X,Guo S,et al.Sensitivity of Livelihood Strategy to Livelihood Capital: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Using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Survey Data from Rural China[J].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2018.
(責任編輯?肖華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