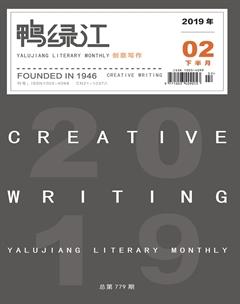理解《北上》的通關(guān)密碼
透過對運(yùn)河的重訪,透過運(yùn)河兒女的眼睛,重新審視既有的歷史結(jié)論,重新找尋模糊的價(jià)值與意義,才是擺脫今日困境與實(shí)現(xiàn)精神救贖的有效途徑。
徐則臣沉潛四年之作《北上》是極為豐富的,這種豐富當(dāng)然表現(xiàn)在已經(jīng)飽受好評的對運(yùn)河沿岸風(fēng)土人情、草木蔬食的詳細(xì)考證和細(xì)致描摹,但我認(rèn)為更重要的豐富性在于其對諸多重要文本與歷史問題的回應(yīng)和討論。繼《耶路撒冷》之后,徐則臣再次觸及了家國時(shí)代的疑問與個(gè)體靈魂的困境,以極為虛構(gòu)也極為歷史的方式。“耶路撒冷”作為徐則臣以同代人之名建構(gòu)起的心靈烏托邦,其實(shí)始終承載著他念茲在茲的“到世界去”的理想召喚。這種召喚足以讓千萬人生死相與,四年之后,徐則臣卻后撤一大步,離開現(xiàn)世代的目光,回望運(yùn)河的古老面孔,審視祖輩的旦夕禍福。但毫無疑問,他關(guān)切的依然是普遍的當(dāng)下,那些關(guān)于起源與去處的疑問,那些關(guān)于興盛與衰亡的探尋,那些關(guān)于戰(zhàn)爭與和平的思考,那些關(guān)于情感與心靈的救贖。在去往烏托邦的旅程中,徐則臣仍然是敏銳而執(zhí)著的。那么書寫《北上》的徐則臣,為“大和堂”內(nèi)外的自我與他者找尋到了比耶路撒冷更在地更有效的答案了嗎?或者說,徐則臣找尋到了不一樣的找尋道路了嗎?
古今中外以河流為主題的作品不勝枚舉,旨趣也多天差地別,但如此明確地以運(yùn)河為書寫對象,以意大利人為主要人物,自1901年寫起的《北上》還是喚起了諸多并不新鮮卻始終重要的中國現(xiàn)當(dāng)代的話題記憶,那是自1988年的《河殤》到2006年的《大國崛起》兩部產(chǎn)生重要影響的紀(jì)錄片未曾回避卻也未曾解決的問題,徐則臣在開卷之初便在讀者心中扎下一根“大河文明”與“海洋文明”邂逅糾纏的刺。隨著小說展開與情節(jié)推動,維新變法、義和團(tuán)運(yùn)動、八國聯(lián)軍侵華、抗日戰(zhàn)爭等重大歷史事件紛至沓來,看似紛雜厚重的中國近現(xiàn)代史卻又四兩撥千斤地收束于湯湯大水中的一葉扁舟。相比于兩種文明形態(tài)的宏觀比較,徐則臣顯然更關(guān)注“大河”自身的歷史理性。但這條“大河”不是壯闊傳奇的“遙遠(yuǎn)的東方有一條江”的長江,也不是在《河殤》中被賦予復(fù)雜內(nèi)涵與情感的母親河黃河,而是人工開鑿于兩千多年前,在2014年被列入世界遺產(chǎn)名錄的“大運(yùn)河”。長江和黃河依地形規(guī)律自西向東橫穿中國,大運(yùn)河則由南向北由人工挖掘貫通,附帶了不同水系、不同河段的多種水利與治理設(shè)施,“大河文明”背后便不只是自然與地理的生態(tài),更攜帶了人文與社會的多重勾連。出版社以“一條河流與一個(gè)民族的秘史”作為宣傳語,似乎有野心將其關(guān)聯(lián)至更為宏大的民族與國家問題,“史詩”二字呼之欲出。徐則臣的文字功力與書寫意識自然也擔(dān)得起如此厚重的訴求,但他以何種方式處理這種厚重以及如何將自己獨(dú)特的歷史與文學(xué)觀念融入其中便成為閱讀和理解《北上》的通關(guān)密碼。
活潑瀟灑的意大利人保羅·迪馬克以小波羅的外號躍入讀者視野,與之相伴的是深沉不得志的沒落帝國的文人謝平遙。這種動-靜、內(nèi)-外對照的敘事模式本身就暗示了矛盾的轉(zhuǎn)換與戲劇性的可期。北上的運(yùn)河獵奇最終證實(shí)為充滿愛與溫情的尋親之旅,也成為此行所有人的人生轉(zhuǎn)折。善良無邪的核心人物,智慧機(jī)敏卻有隱痛的文人,輔之以“改邪歸正”的保鏢護(hù)衛(wèi),質(zhì)樸純真的挑夫兼廚師,奔著一個(gè)誰也說不清誰也不知道是什么結(jié)果的目標(biāo)。這趟旅程恍然間有了《西游記》中決絕的朝圣味道。不同于師徒四人最終的邪不壓正、修成正果,保羅·迪馬克意外死亡,孫過程舍生就義,秦老夫婦葬身火海,還有變法失敗、志士逃亡,民間恃強(qiáng)凌弱,廟堂腐朽昏庸,戰(zhàn)場堆尸如山,前線血流成河……歷史的荒誕與理性在運(yùn)河兩岸以殘酷而罪惡的方式完成了對這一渺小團(tuán)體的洗禮。但也正是這種渺小穿越歷史隧道,組建了包括攝影師兼畫家、精通意大利語的民宿創(chuàng)始人、考古學(xué)家、節(jié)目制作人在內(nèi)的“超級文藝工作者聯(lián)盟”,他們尋尋覓覓,終將以完全現(xiàn)代化的方式替他們的祖輩表達(dá)未竟的對運(yùn)河的眷戀與愛。這是一個(gè)悠長的敘事弧(Narrative Arc),是一場跨越時(shí)空的心靈與情感救贖(Redemption)。一百年前落入運(yùn)河中的手杖終于有了當(dāng)下的回響,那些罪惡和血腥,那些悲傷和絕望,有了此時(shí)此刻的報(bào)償。
他會產(chǎn)生一個(gè)錯(cuò)覺,覺得孫過程他們抬著小波羅,正朝低矮的天上走。
“救贖”與“天上”,是小波羅的故鄉(xiāng)有的宗教概念,是來自遙遠(yuǎn)的海洋文明的微風(fēng)。小波羅以一己之力窺伺了大河文明的點(diǎn)滴,而他的弟弟馬福德則將一生獻(xiàn)給了這片古老的土地。他們共同見證乃至參與了東西文明的沖突,也親自承受了帝國末期的傷痛。小波羅無辜慘死,馬福德演繹了前現(xiàn)代版本的更為殘酷的《永別了,武器》。對河流的執(zhí)迷與歷經(jīng)戰(zhàn)爭的創(chuàng)傷都在一個(gè)運(yùn)河邊的姑娘那里得到了釋放和療愈,于是才有了顯得彌足珍貴的安然舒適的三十年人生。他和他的哥哥一樣,以微薄之力抵抗著運(yùn)河兩岸的罪惡與苦難,以真心真意感受著運(yùn)河形塑之下的中國人民的愛與怕,以肉身的消亡成全了謝平遙、孫過程、邵常來、周義彥的家族傳承。那些不可名狀的巧合與相逢,都因這種拯救與試圖拯救具有了中西文明相遇相知的溫度。
只有我們這樣每天睜開眼就看見河流的人,才會心心念念地要找它的源頭和終點(diǎn)。對你伯伯來說,運(yùn)河不只是條路,可以上下千百公里地跑;它還是個(gè)指南針,指示出世界的方向。
但我們終究是不同的。當(dāng)顯得有些油膩不正經(jīng)的節(jié)目制作人謝望和回到運(yùn)河邊的家鄉(xiāng),遭遇的是與他的現(xiàn)代價(jià)值理念截然不同的伯伯,“世界的方向”再次指涉了徐則臣“到世界去”的召喚,也明示了運(yùn)河對運(yùn)河邊的人們生活觀念的決定性影響。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的哲學(xué)天問以更具體的形式困擾著他們。運(yùn)河是世界的能指,它的源頭與終點(diǎn)的不可抵達(dá)成為運(yùn)河人永恒的焦慮,成為和兄弟矛盾一樣的時(shí)間都無法作為的飛地。而對這一焦慮的一種緩解路徑或許就是邵家的生活方式,承繼了小波羅意大利羅盤的邵氏后人是“北上”之旅中唯一真正沒有脫離運(yùn)河的一脈。最年輕的邵星池做出了上岸的努力,最終卻還是要贖回羅盤回歸運(yùn)河。而和謝望和的伯伯一樣堅(jiān)守著運(yùn)河信念的邵秉義儼然成為與運(yùn)河同生的水上鸕鶿。
吃睡、睡吃,抓兩條魚,喝二兩酒。生在這條河上,活在這條河上,死也得在這條河上。
去而復(fù)返的邵星池其實(shí)是水上版的高加林,即使是貼著大地呼喚“我的親人啊”,我們也知道他終有一天會毫不猶豫地離開,而邵星池再次離開之日便是邵家堅(jiān)守運(yùn)河終結(jié)之時(shí),這也意味著意大利羅盤將真正成為文物,歸屬于“小博物館”。謝望和的伯伯和邵家,是運(yùn)河神秘性的最后一批崇拜者與守護(hù)者。但正如當(dāng)年初平陽對大和堂的“背叛”,如果聽到了世界的召喚,那么即使遺落在身后的是悠長的歷史和祖輩的榮光,今天的選擇也絕非大逆不道。運(yùn)河是慈母也是嚴(yán)父,更是聲聲催促的內(nèi)心欲望的野獸。
運(yùn)河運(yùn)河,有“運(yùn)”才有河。不“運(yùn)”它就是條死水。
和所有書寫歷史和文化的作家一樣,徐則臣也有著深刻的文人知識分子的焦慮和責(zé)任意識,但在《北上》中很欣喜地感受到他觀念意識的鮮明變化。不“運(yùn)”的大運(yùn)河會是死水,但“運(yùn)”的方式卻可多變。“大運(yùn)河”入選了世界遺產(chǎn)名錄,《大河譚》項(xiàng)目正需要更多市場邏輯下的投入與關(guān)注。或許在此時(shí)此刻,“運(yùn)”本身便代表了一種靈動和變化,對文明與進(jìn)步的接納,對現(xiàn)實(shí)狀況的認(rèn)知,對欲望野獸的誠實(shí),對即刻選擇的隨心所欲。老子云“上善若水”,在欣賞水的不爭與包容的同時(shí),何嘗不是提醒我們對自身活力與擺脫桎梏的珍視。在百年滄桑之后,運(yùn)河與她所養(yǎng)育的人們之間的關(guān)系以辯證的姿態(tài)邁入了新的階段。
面對“民族秘史”一般的河流,自稱“運(yùn)河之子”的作家該如何坦然面對她的昨天與今日,更為重要的是如何無愧地走向未來?20世紀(jì)80年代,劉小楓以“拯救”與“逍遙”區(qū)分中西方精神的原始沖突、兩種詩的精神之問的沖突,他認(rèn)為在中國精神中,怡然之樂的逍遙是最高的精神境界,而在西方精神中,受難的人類通過耶穌基督的上帝之愛得到拯救,人與親臨困難深淵的上帝重新和好是最高的境界。這一組比較詩學(xué)領(lǐng)域的概念卻在某種程度上與《北上》有了微妙的呼應(yīng)。這并非因?yàn)橐獯罄说募尤胴S富了小說中的精神來源,而是在時(shí)代、歷史、文化、民族、國家的多重維度中,徐則臣找尋到了全新的處理方式。雖然跨時(shí)空的戲劇化搭建方式與某些行文風(fēng)格仍有待商榷,但于運(yùn)河所及之處展現(xiàn)出的不同文明中人面對愛與恨、善與惡、生與死、戰(zhàn)爭與和平,自由與束縛等永恒矛盾時(shí)的掙扎與抗?fàn)帲瑢κ聦?shí)、真理、價(jià)值與意義的不斷探求其實(shí)都觸及了當(dāng)代文學(xué)中未得到足夠討論的精神自覺與靈魂建設(shè)的問題,這一問題被徐則臣巧妙地借運(yùn)河的歷史和文明以祖輩和今人的群像表現(xiàn)出來。作為人工開鑿的運(yùn)輸通道,大運(yùn)河時(shí)刻在創(chuàng)造也時(shí)刻在摧毀她的兒女們的肉身與精神,那些被湮沒的和被銘記的,共同構(gòu)成了運(yùn)河人民的物質(zhì)與精神狀況,那些光榮和夢想,那些痛苦和災(zāi)難,都如被意外發(fā)現(xiàn)的沉船,難以準(zhǔn)確地把握卻又散發(fā)著驚人的魅力。唯有透過對運(yùn)河的重訪,透過運(yùn)河兒女的眼睛,重新審視既有的歷史結(jié)論,重新找尋模糊的價(jià)值與意義,才是擺脫今日困境與實(shí)現(xiàn)精神救贖的有效途徑。也只有實(shí)現(xiàn)了這種形而上的超越性的拯救,今天所有有關(guān)運(yùn)河與自身生活的選擇才有進(jìn)入怡然自樂的逍遙的可能性;也只有有了逍遙的可能性,那些在夢中向我們走來的祖輩和在俗世中向我們侵襲的重壓與枝節(jié)才有可依附的與被紓解的時(shí)間與空間。在這樣的意義上,徐則臣從劉小楓的中西比較走向了個(gè)人特色的自我辯難。
四年前的耶路撒冷終于以運(yùn)河的具象再次呈現(xiàn),那遙遠(yuǎn)的漂浮的精神烏托邦悄然落地,代之以百年的風(fēng)雨飄搖,大水湯湯之中是對歷史相對真實(shí)與普遍價(jià)值的體認(rèn),是對東西文明都孜孜以求的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該怎么做的的溫柔追問,是對全體人類永恒困惑的路在何方的嘗試性回答。是謂徐則臣的舉重若輕,是謂運(yùn)河之子的拯救與逍遙。
樊迎春,北京大學(xué)中文系博士生,哈佛大學(xué)訪問學(xu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