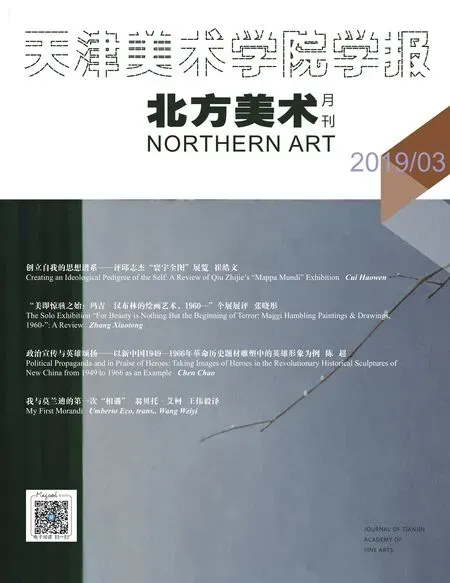政治宣傳與英雄頌揚
——以新中國1949—1966 年革命歷史題材雕塑中的英雄形象為例
陳 超/Chen Chao
一、新中國英雄人物雕塑形象塑造的現實語境
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后,新生政權需要以一種全新的公眾化視覺藝術形式,審視過往戰爭,緬懷和頌揚英雄人物,以教化、啟迪民眾。其中,作為革命歷史題材雕塑核心內涵之一,英雄人物具有的高尚品質和崇高精神,承載著榜樣的作用、鼓舞的力量和教育的意義,體現著鮮明的時代特征與時代精神。對英雄人物的塑造則直接表達了當時國家意識形態訴求和政治指向。
早在1942年,毛澤東發表著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講話》重點強調文藝為什么人的問題,指出藝術首先要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其中,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武裝隊伍,作為革命戰爭的主力,被確立為文藝作品服務的主要群體之一。1949年7月,周揚在第一次文代會上作《新的人民的文藝》報告,重點論及“新的英雄人物”的問題。[1]在1953年第二次文代會上,周揚指出“表現完全新型的人物”是“文藝創作的最崇高的任務”。[2]伴隨著關于“新英雄人物”塑造問題廣泛而深入的討論,作為民族國家意識形態凝聚的符號,英雄被視為新中國成立初期雕塑創作的核心話語,成為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雕塑創作的首要主題。
1954年,江豐在論述“美術工作的重大發展”時首先提到雕塑,他指出:“在舊中國時代極不發達的雕刻藝術,……由于無數的英雄人物需要雕刻家去塑造,這給雕刻藝術創造了良好的發展條件,不再是像過去那樣‘英雄無用武之地’了。”[3]雕塑作為極具公共性、標識性、場域性的藝術表現形式,這一時期在官方組織的美術館、博物館收藏活動的推動下,同時受國家對于紀念碑雕塑項目的影響,通過題材、造型、空間、材料等層面的具體塑造,在博物館、美術館、紀念公園、廣場、城市街道等公共場所永恒持久地發揮影響,彰顯出紀念戰爭、緬懷英雄的特定主題,完成了教化、啟迪、頌揚的社會職能。
在新中國英雄人物雕塑作品中,雕塑家通過嚴謹的寫實手法,真誠地歌頌了革命英雄的崇高精神,突出了教化和頌揚的社會職能,具有強烈的政治指向和精神特質,如王朝聞的《劉胡蘭像》《民兵》,蕭傳玖的《地雷戰》,王臨乙的《紅軍》,潘鶴的《艱苦歲月》等作品。英雄的形象成為彰顯國家形象和時代崇高利益的代言體系,同時,這一角色也被賦予了更多的社會價值和歷史價值。
二、新中國英雄人物雕塑的創作特征
在以英雄人物為主題的雕塑作品中,英雄人物的舞臺化塑造與崇高性表現,革命歷史的宏大敘事與集體“亮相”,苦難敘事的遮蔽與悲劇意識的“缺席”,成為新中國英雄人物雕塑創作的主要特征。
(一)舞臺化塑造與崇高性表現
20世紀50年代,新中國全面學習蘇聯,藝術上受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深刻影響。雕塑家遵循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法則,積極學習和繼承蘇聯學院派雕塑的創作經驗,英雄人物創作在權威話語規約下形成一套概念化、程式化的英雄主義塑造模式。
王朝聞的《劉胡蘭像》本質上塑造的是一位14歲的少女形象(圖1)。作者選取劉胡蘭就義前最具表現力的瞬間,著重突出其橫眉冷對、昂首挺胸的“架勢”,表現劉胡蘭在面對死亡時的無畏精神,具有強烈的舞臺化效果。在具體塑造中,作者弱化女性的性別特質和年齡差異,對少女形象做“雄化”塑造,高顴骨、大眼睛、厚嘴唇,身體粗壯,臂膀寬大,呈現出男性的陽剛和健壯,凸顯威嚴、冷峻的人物性格,從而吻合主流意識形態所規約的英雄行為與壯舉。王朝聞曾說《劉胡蘭像》在創作時力爭對人物真實面貌做客觀還原,但人物形象與人物原型之間仍有較大距離,可以看出這一時期雕塑家的歷史意識被嚴重限制,英雄的形象和性格特征被“崇高性”“理想化”所遮蔽,忽略了人物性格和情感表現,是這一類型創作的缺憾。

圖1 王朝聞 劉胡蘭像 鑄銅 1951年
1958年,在中央美術學院舉辦的蘇聯專家“克林杜霍夫雕塑訓練班”畢業展上,于津源的《八女投江》引起關注。其獨特之處在于將八位人物分布于每個面,突破了紀念性雕塑正面觀看的局限,形成四面觀看的視角,拉近了觀眾與作品之間的距離(圖2)。《八女投江》同樣表現的是女性英雄就義時寧死不屈的形象。作品選取人物最具表現力的面部、手勢、動作和姿態等典型特征,表現出抗聯戰士深沉、豪壯的革命氣概。作品一方面捕捉英雄就義前最具典型性的瞬間,在群像組合、人物塑造和環境烘托方面,呈現出強烈的舞臺化效果。另一方面對于人物形象的刻畫趨于模式化、男性化,忽略女性性別特質與年齡差異,人物之間有著清一色的面部表情和昂首挺胸的“架勢”,身體健壯,臂膀粗實,這種針對女性的“雄化”塑造和英雄主義的渲染,目的在于展現女性英雄凜然無畏、至剛至強的形象,凸顯高亢激昂的情緒,真誠歌頌革命英雄的崇高精神。

圖2 于津源 八女投江石膏 1958年
女性英雄人物因其特殊的歷史貢獻在這一時期被廣泛表現,成為新中國英雄人物雕塑創作的重要題材。誠然,女性人物塑造的“男性化”特征,違背了人物真實形象及性格的本真,但在英雄年代卻有著特殊意義。雕塑家通過借用男性的生理、形象特征,強調出女性的陽剛之美,適應了革命英雄主義理想化和崇高性的規約,體現了社會心理對女性形象特征的要求,是新中國英雄人物雕塑創作的一大特色。
值得注意的是,新中國英雄人物雕塑聚焦于“英雄主義”“理想主義”的主題,但不乏有側面表現戰爭中感人的情節、細節的作品。例如,潘鶴的《艱苦歲月》以普通革命戰士為表現對象,描繪了戰爭年代革命戰士閑暇的生活,體現出艱苦年代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作品在題材、主題上轉向對于普通革命戰士、無名英雄等“小人物”“小題材”“小細節”的觀照,豐富了新中國英雄題材雕塑創作的思想內涵,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這一時期藝術家的英雄觀發生了根本轉變。這件作品創作之初因“沒有表現革命高潮和勝利”而被否決,但雕塑家堅持己見,不斷爭取,作品的最終完成是雕塑家個體與上級意志之間博弈的結果,由此成就了這件在美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品。
(二)宏大敘事與集體“亮相”
湯姆斯基認為:“紀念碑雕刻具有直接的社會教育意義的思想,具有與社會斗爭、人民群眾的勞動、人民與國家的歷史密切聯系的思想,它直接面向廣大群眾,直接面向全體人民,是一種與人民的集體生活聯系得最為密切的藝術形式。”[4]紀念碑雕塑自身獨特的形式語言、空間屬性以及社會性、歷史性的特點,成為這一時期強化國家政治意識形態的重要載體。
盧鴻基的《大連蘇軍烈士紀念碑》表現了蘇軍戰士保衛和平的英雄形象。紀念碑碑體高32米,蘇軍戰士銅像高5米,頭戴鋼盔,雙手持槍,氣度凝重。臺座正面東西兩側鑲嵌兩塊浮雕,集中表現了蘇軍戰士戰斗的情景,有力地宣傳了蘇軍戰士英勇抗戰的無畏精神(圖3)。這種以圓雕主體人物與浮雕場景敘事相結合的塑造方式,強調紀念碑圓雕主體人物的“正面”形象給人的視覺沖擊,突出浮雕中人物集體“亮相”的宏大場景,是新中國紀念碑雕塑的典型樣式,高聳硬朗的碑體與敦厚規整的臺座以及高大威武的人物,形成一種典型的金字塔似的“英雄崇拜”的構圖和“神化”的人物塑造,強調出紀念碑雕塑的精神作用和心理效果,潛在突出了紀念碑雕塑的政治功能和現實意義,深刻影響著新中國英雄人物形象塑造的基本范式。
與之不同的是,在表現方式上,尹積昌1958年創作的《廣州解放紀念碑》①并沒有選擇具體的英雄人物來組成宏大的敘事場景,而是以普通革命戰士為表現對象,塑造出一名右手持步槍、左手捧鮮花、面帶笑容的年輕戰士(圖4)。不僅如此,在主題思想上,作品突破了以戰斗場面凸顯英雄的英勇善戰,以戰爭高潮的狀態體現革命的激情、彰顯革命勝利的單一視角,而是通過塑造一名革命戰士接受民眾獻花的情景,表現出人民群眾與革命戰士的血肉關系。無獨有偶,潘鶴、梁明誠1980年的《廣州解放紀念碑》(圖5)在表現題材上同樣以一名普通革命戰士為對象,但作者在寫實的基礎上融入強烈的個人色彩,通過概括夸張的手法,突出了人物面貌和心理特征的描繪。
縱向比較同一題材雕塑在不同時期的創作,一方面反映出不同時代背景下藝術家在創作觀念和審美視點上的變化,另一方面可以看出在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的規約下,這一時期英雄人物雕塑創作重點強調英雄行為與壯舉,忽略了人物內心情感的挖掘,個體性被政治性所淹沒,喪失對人性豐富性的揭示,這不得不說是這一類型創作的一個問題。
事實上,英雄人物紀念碑雕塑自身明確的社會指向性和政治意義,直接受到國家政治變革和社會主流意識形態調整的影響。無論是在題材、內容、性質上,還是在形式、語言、手法上都必須按照國家的意志來完成。作為一項嚴格的政治任務,雕塑家的創作個性和藝術風格受到限制,作品存在著題材選擇單一、創作手法程式化、藝術創作面貌雷同等弊端,作品思想性突出,而藝術性明顯不足。客觀來講,這一時期紀念碑雕塑最大程度地突出了其社會功能和教育意義,很好地完成了它在特殊政治環境下的任務,但從深層意義上看,作品藝術性明顯缺失,其審美意蘊并未充分發揮。

圖3 盧鴻基 大連蘇軍烈士紀念碑鑄銅人像,花崗石碑身 1955年
(三)苦難敘事的遮蔽與悲劇意識的“缺席”
美國哲學家蘇珊·朗格認為:“只有在人們認識到個體生命是自身目的,是衡量其他事物的尺度的地方,悲劇才能興起,才能繁榮。”[5]國內學者邱紫華認為:“悲劇并非僅指生命的苦難與毀滅,更重要的是面對不可避免的苦難與死亡的來臨時,人所持的敢于抗爭的態度和勇于超越的精神。”[6]在頌歌話語制約下,這一時期作品大多充滿著樂觀向上的革命激情和信仰。作為革命話語核心任務之一的苦難敘事完全被歡歌和頌揚的主題所主導。即便是表現犧牲,作品中也很少出現人的苦難、悲劇和戰爭的慘烈,而是著重強調英雄人物在面對死亡時那種威武不屈、無所畏懼的英雄形象,他們不怕死,他們的死沒有凄慘之感。
拿于津源的《八女投江》來講,作者并未直接表現死亡,而是重點突出女戰士堅定勇敢地面對死亡時的崇高精神。如果把于津源《八女投江》與20世紀80年代張德華、曹春生等人的《八女投江》②(圖6)相比較,可以看出人物塑造上的明顯變化。前者中的女戰士毫無畏懼地走向死亡,人物形象的塑造籠罩著英雄主義的理想化光環,作品的悲劇性被英雄性所遮蔽,氣氛壯而不悲。后者則是堅定樂觀地面對死亡,壯烈與崇高之美有所削弱,悲傷凄涼氣氛增強。值得注意的是,對于最前面的負傷戰士面部表情的刻畫,前者強調的是一種無情感、無痛感、不真實的塑造,而后者則顯得平和、柔美,富有人性化色彩。

圖4 尹積昌 廣州解放紀念碑鑄銅 1958年

圖5 潘鶴,梁明誠 廣州解放紀念碑 花崗石 1980年

圖6 張德華,司徒兆光,曹春生八女投江 花崗石 1982—1986年
1949至1966年間,個人立場的懸置使得雕塑家主體意識被嚴重限制,苦難敘事很難得到正面描繪和全面表現。這一時期意識形態決定了英雄題材雕塑創作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悲劇產生。然而,也正是對苦難的遮蔽,折射出英雄犧牲的事實,從而將崇高美推向極致,人們化悲痛為力量,積極面對革命事業,英雄人物雕塑的社會功能充分發揮。
三、結語
1949至1966年間,英雄人物雕塑創作最本質的特征是意識形態性。創作主題上以頌揚革命英雄、宣傳政治形態為主,凸顯政治訴求,彰顯時代主題。雕塑家在選題、表現對象、構圖、人物組合、造型等層面,必須嚴格依照規定執行,其個體想象力和主體意識融匯于整個社會對“理想”“信仰”“激情”的熱潮中去,作品重點強調政治性、思想性,弱化審美的表現。人物塑造上,存在概念化、程式化痼疾,清一色的面部表情,動作劃一的姿態,昂首挺胸的“架勢”,重點強調英雄人物在面對死亡時威武不屈、無所畏懼的人物形象,人物性格和情感被“英雄性”“崇高性”“理想化”所遮蔽;表現手法上,寫實手法“一統天下”,因其自身塑造人物和事件的形象性、整體性的特點,能夠表現直觀、翔實的內容來記錄、圖解歷史,完成教化、頌揚的任務,而寫意手法正因為不具備這種“優勢”而在這一時期受到擱淺。題材內容上,作品重點強調主流意識形態所倡導的歷史“真實”,遮蔽與當時意識形態不相吻合的細枝末節,題材單一,內容局限。今天看來,1949至1966年英雄人物雕塑創作盡管存在諸多“弊端”,但從整個我國英雄人物雕塑發展的上下文關系看,仍具有不可否認的現實意義。它一方面集中體現了特定政治環境下的時代主題和主流意識形態的需求,很好地完成了其在特定時期的社會任務,另一方面則建構生成了新中國英雄人物雕塑創作的革命理想與價值觀念,為新中國雕塑創作提供實踐經驗,深刻影響著改革開放以來英雄人物形象塑造的基本范式,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
注釋:
①該雕塑1958年建于廣州海珠廣場,因“文革”期間擬在此處建毛澤東塑像,于1969年被拆除。文中圖2是作品小稿,存于廣州尹積昌雕塑園。
②于津源1958年創作的《八女投江》參加1984年“首屆全國城市雕塑設計方案展”獲得優秀作品獎。1982年,張德華、司徒兆光、曹春生等雕塑家在創作《八女投江》時,他們在前期小稿基礎上加以深化,前后歷時四年創作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