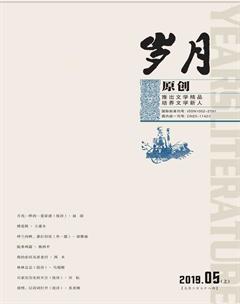呼蘭河畔,蕭紅舊居(外一篇)
談雅麗
我是因為女作家蕭紅而要去呼蘭河的,要到呼蘭小城親眼見到她的故居。
我想看看這位命運多舛的女作家生活過的地方,那座小城是否如她筆下《呼蘭河傳》中細細描述的樣子。我想近距離體會她的心靈歷程,去走走呼蘭城唯一的兩條大街,一條從南到北,一條從東到西,想看看十字街,是否集中全城的精華。也想去看看冬天的呼蘭河,在封凍的河上做一次愉快的漫游。
在蕭紅筆下,呼蘭這座小城單調而呆板。一年之中,人們很有規律地過生活:一年之中,必有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燈,野臺子戲,四月十八娘娘廟大會……這些熱鬧、隆重的節日,而這些節日也和他們的日常生活一樣單調而呆板。這座小城彌漫著舊時生活的音響和色彩。大街小巷,每一茅舍內,每一個籬笆后面,充滿了嘮叨、爭吵、哭笑,乃至夢囈,一年四季,依著那些走馬燈似的挨次到來的隆重熱鬧的節日,在灰暗日常生活的背景前,呈現了粗線條大紅大綠的帶有原始性的色彩。
在蕭紅筆下,呼蘭這座小城的人民良善而淳樸。他們依著幾千年傳下來的習慣而思索和生活,他們有時也許顯得麻木,但他們也頗敏感而瑣細,芝麻大的事情他們會討論或者爭吵三天三夜而不休。他們使女作家又愛又恨,一方面急急離家出走永不回頭,一方面又在筆下不斷地深情回望。
我們從天寒地凍的哈爾濱出發,沿著濱水大道一直前行,三十多公里的自駕之旅,越野車在明凈的國道線上勻速而行,不時可見道邊有枯木站立,殘雪堆積。公路不遠處能隱隱瞧見一條大江,一直跟隨我們行走,這就是松花江。她時而合流成一條主江道,時而分流成幾條細干枝,然而一直不離不棄,等流到了呼蘭區時,忽然有另一條大河橫著沖了過來,在城南五公里處匯入了她的江口。城以河命名,這條河就是呼蘭河。我們進入呼蘭城必先經過呼蘭河大橋,橋也以河命名。年輕女作家蕭紅的書也以河命名,因為書中有了這條河,就保留了生命的記憶。蕭紅生命中歷經的滄桑和磨難,仍被人永久記得和回味,仍被時光之河緩緩道來。
從呼蘭河大橋上經過,看到呼蘭河已被完全封凍,只有一條蜿蜒向前的冰雪線,這條冰雪線通向了不遠處的松花江。河水的流動可以想象成冰雪的延伸,無盡的冰雪正鋪開在大地。我們從橋上駛過就進入了城內,和許多中國式的小城無不相同,街道的主干道并不寬闊,一些商鋪、餐館、酒店、糧米加工、五金、木器、紡織、印染、皮革、鞋帽,林林總總,立于街道兩旁。呼蘭是一個不新不舊的普通小城,很多年來它一直安于安靜的現狀,與世無爭地保留著固執和倔強,唯一不同的,小城里曾經生活過固執和倔強的蕭紅。
穿警服的劉所長在派出所門口等著我們,這個中年男人憨厚善良,他要帶我們去蕭紅故居參觀。他說,整個呼蘭區,除了蕭紅故居,幾乎沒有更多旅游景點可去,而故居一個多小時就可看完,所以不著急,先要去填飽肚子。下午兩點多,我們也饑腸轆轆了,在蕭紅故居旁不到二百米的地方有一家餃子店,兩盤鮮肉水餃,每盤三十多個,炒菜都用大盤裝著,數量驚人,因為怕浪費,我們吃得很飽,但也剩下了很多。我忽然想到蕭紅是把饑餓寫得最好的女人,那種悲慘,不是真真切切經歷過的人沒法體會。她有一篇文章《雪天》的開頭這么寫道:“屋子雖然小,在我覺得和一個荒涼的廣場一樣,屋子墻壁離我比天還遠,那是說一切不和我發生關系,那是說我的肚子太空了。”她在冰冷的小屋里等蕭軍歸來,想的是:“我拿什么來喂肚子呢?桌子可以吃嗎?草褥子可以吃嗎?”蕭軍賺了錢兩人下館子,半毛錢的豬頭肉配二兩燒酒,再喝上一碗熱氣騰騰的肉丸子湯,兩人高興得像孩子一樣。她把對食物的滿足感寫得那樣透徹,是最真切的感受和經歷,她把自己的人生依附在一個又一個的男人身上,或許就是為了填滿發自內心的巨大的空洞和饑餓。這也導致了她一生悲慘的命運。她是民國四大才女中命運最為悲苦的女性,一生都在與苦難掙扎、抗爭,這使我對她的命運產生了巨大的同情。
蕭紅紀念館和蕭紅故居緊挨著,故居前是一溜兒一米多高的深青圍墻,院墻上的浮雕再現了《呼蘭河傳》的場景。院墻盡頭有雙開木門,木門上橫有深青門楣,一棵落光葉子的柿子樹站立在門右側,不知道誰在柿子樹上系了幾盞通紅的燈籠,這使蕭條的冬天多了幾盞暖色。一群男男女女隨意站在樹下,有幾個女人在陽光底下閑聊,幾個中年男人只是單純地無所事事地站著,看著熱鬧,也許這些閑著的人,正是蕭紅筆下卑微平凡的實際生活場景的再現。
故居門外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喧嘩,閑逛的人,打堆說話的人,車聲人聲不時響起。門內卻無比安靜和荒涼,我和阿華是唯一兩個闖入者。清末傳統八旗式住宅清寒地立在雪地上,青磚青瓦的兩個院落單調而無人煙氣;北方鄉村的典型建筑,地面鋪滿了深青的地磚,但上面落滿了冰雪,顯得荒涼而寒冷。園子、道旁種滿了樹,但樹落光了枝葉,只有凌厲的枝條伸向了深藍的天空。漢白玉雕刻的蕭紅正在園子中央托腮沉思,她顯得那樣潔白,不解人世,她凝望著園子里的冰雪,我順著她的視線看過去,只見鋪滿冰雪的園子里竟然長出了一樹紅花,不知道那是什么花,然而奇跡般地開得滿樹鮮艷、燦爛。從這開滿紅花的樹向遠處望去,也許就是封凍的呼蘭河了。
從故居出來,我們直接進入蕭紅紀念館,紀念館分為:呼蘭河畔、漂泊歲月、書香恒久、夢回呼蘭河四個展區。主題色調以灰色為主,每一部分都是蕭紅生活的再現,我們從這里進入了蕭紅短暫而悲涼的一生:蕭紅小時候無憂無慮地成長;蕭紅與蕭軍的雕像再現了他們美好的愛情生活;蕭紅的創作手稿規整、細膩、干凈,她的字雋秀漂亮;蕭紅用過的帽子、圍脖、鞋子可見她是個熱愛生活的人;魯迅先生生病時,蕭紅為他熬藥的雕塑,蕭紅寫過的《魯迅先生》是公認的寫魯迅最形象的懷念文章,也許蕭紅對魯迅的景仰和熱愛是旁人無法體會的,所以她才能將細膩的細節和真實的情感流露在這篇懷念的文章中。一張張照片、一組組圖片、一部部書集都在細述蕭紅的人生經歷,記錄她坎坷而微光的一生。
從紀念館出來,我看見一尊高大的漢白玉雕像,上面寫著女作家蕭紅(1911—1942)。蕭紅只活了31歲,年輕的蕭紅身后是一輪紅日,一泓蕩漾的河水,她身著旗袍,披著圍巾,站立船頭,凝視遠方,那身后的大河就是呼蘭河。
傍晚我們到達呼蘭河畔,這條雪白的冰河上到處都是游玩嬉戲的孩童,他們在冰上玩車輪滑雪的游戲,幾臺越野車在大河上奔跑。一輪落日正徐徐緩緩降下帷幕,落日把金色的光芒投進冰雪之中,把天空和冰河都染得通紅,我在冰雪之上看到了燃燒的彩云,從西邊一直燒到東邊,紅彤彤的,好像是天上著了火。一時間,我變得恍恍惚惚,滿天空又像這個,又像那個,其實什么也不像,什么也沒有,我只看見年輕的蕭紅,靜靜地憂傷地望著這條冰凍的大河。
呼蘭河是蕭紅生命的起點,是她靈感的源泉,她從這里起身,決絕地離開呼蘭小城,跋山涉水,但其實在她的內心深處從來沒有忘記過這條寒冷的大河。無論走得多遠,故鄉的一切已牢牢根植于她的心靈深處。
三岔河,冰雪江上的華爾茲
我到過許多河流匯聚口,那些流動的河口如深愛的戀人,歷久相思而得以相逢擁抱,瞬間匯合一體,流向遠方,這些交融的生命線給我的人生帶來最美好的遐想。
我在黑龍江看到凝固的冰雪河流,知道冰雪下的奔騰,暗流涌動于平靜雪白的冰面。我生出了這樣的幻想,我想找到冰河上的河流交匯口。冰河與冰河之間怎樣交流?是否冷酷中傳達相聚的熱烈和不舍?于我而言,不動聲色的波光和凝固,那是柔情與冷酷的一種對峙,是一種我從未曾經歷的生命體驗。
到達肇源的那天傍晚,我和詩人梁久明談到想去第二松花江、嫩江和松花江交匯的河口——三岔河去看看。梁久明是縣一中的副校長,學養豐富,也是一個騎行愛好者,他曾經用一輛自行車騎遍了肇源的山山水水,甚至遠及幾百公里的哈爾濱市。夏天他騎行到了肇源茂興鎮,南行十里,看到了三江匯聚之地——三江口,當地人稱之三岔河的地方。當時微風吹拂,這片大地到處種滿了剛剛結苞的玉米和翠綠的花生,偏僻的河口周圍被莽莽蒼蒼的荒涼覆蓋,大片苫房草、小葉樟漫山遍野,圍裹江堤,大片柳條通、柳蒿塘、水蓮花鋪天蓋地,遮護江灘。他在三岔河自然保護站的樓房前停了下來,看見了一黑一白兩條江水在不遠處合聚。嫩江淺黑,第二松花江潔白,兩江涇渭分明并江而成松花江。雖在一江之中,但兩江綿延兩公里之遠仍然界限分明,黑白不混,令他嘆為觀止。自古有記載:“南有涇渭,北有粟黑。”這粟黑之說指的就是肇源三岔河的兩江交匯,江水一黑一白截然分流的壯美景觀。
梁久明說,雖然三岔河離縣城較遠,但在冰雪中不妨走到江面看看,找到凝固的黑白兩江。其實在當地人眼里,三岔河又叫“陰陽河”。這使我想起太極圖譜中轉動融合的陰陽兩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在宇宙混沌期,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渾而為一。陽的解釋就為向陽面,如受到光照的白晝。而陰則代表背光面——黑夜。陽從左邊團團轉,陰從右路轉相通,這是太極運轉的軌跡。而兩江匯合,正符合陰陽兩合,萬物協調的規律。
三岔河位于松嫩平原的腹地,殘冬過后,只剩下一些枯黃的玉米殘梗遍布大地,我們路過那些鄉村老房子有石頭圍起的院墻,墻外都壘有圓形的、金黃的玉米圍垛子。下午三點,我們到達三岔河自然保護站,看到一座紅色小樓立于落光葉子的樹林之中,旁邊有一個水泥石頭小碑刻著“三岔河”幾個紅字。靠近江堤停靠著一艘生銹的舊船。保護站的樓房前還有一個綠色牌子,上面寫著:“三岔河保護管理站,位于茂興鎮當權村南三岔河口岸邊,建筑面積150.96平方米,主體兩層,局部三層,磚混結構,三層為瞭望塔。三岔河保護管理站負責對超等鄉和茂興鎮保護區沿線4750公頃濕地面積的管理。”
我們到達江邊時,保護站的小樓空無一人,寒冷的冰雪使濕地所有的動植物沉入了睡眠,濕地的守護者也搬離到遠離寒江的溫暖之地。厚厚的冰層覆蓋著江面,因為江岸石頭之間巨大的裂縫,所以形成了陡峭的冰斜坡,人不可能直接走到江面。當我沿著江邊一直走著,一條帆皮帶做成的水管適時地幫了我的大忙,水管大概是在冰河抽水遺棄下來的。為了防滑,我踏著帆布水管慢慢挪步到江面上。也許不久前抽過水,所以在抽水處形成了一條晶瑩剔透的冰龍,略高于冰面半米,橫臥于江中的冰龍長若數米,鱗片栩栩如生,龍角翹起如飛,非常壯觀,仿佛因著某種機緣歡迎我們的大駕光臨。
在清澈的玻璃冰面之上行走,我能看見冰江底下凝固的氣泡,看見冰江中的裂縫,看見死去的水草。我把腳踏在冰江叢叢簌簌堆積的新雪上,沙粒子一樣的雪冰使江面晶瑩而生動起來。我沿著江面小心翼翼地走著,不遠處就是三江匯合之處,我沒有看到那條明顯的分界線。橘紅的太陽正一點點往下落,我面對著夕陽站立,河的彼岸是吉林,此岸是黑龍江,左手前方是嫩江,右手前方是第二松花江,我站立的冰下就是松花江。我想起了松花江的命名,想起這個黑龍江最大的支流,在不同的朝代被人稱呼著不同的名字,唐時稱涑沫江或粟末水,遼、金時稱宋瓦江、混同江,明始稱松花江。清朝時用滿語稱為“松阿里烏喇”,亦即“天河”。清朝楊賓《柳邊紀略》中寫著:“謂松阿里者漢言天,烏喇者漢言河,言其大若天河也”。我感覺到腳下站立的正是一條浩瀚的天河,它似乎連接著天地萬物中的一切,在陰陽中、混濁中化歸一切生命于其中。
透澈的冰河被傍晚的夕陽染了色彩,一層淡紅,一層金光。如果順著陽光看,能看到一個太陽在晴朗的天空之上,無數太陽卻被折射地冰下。陽光不斷地被冰雪反射,它將我的身影拖長,將冰層變成了懷抱無數陽光和晚霞的黛青色土地。如果逆著陽光看,看到的卻是一條潔白透明的冰河,陽光在其上撒下無數帶金光的碎點。
暮色一點點消失在江面,在零下二十度的三江匯聚口,我凍得手腳麻木,臉色通紅,卻舍不得離開,似乎在這江水之上實際存在著一個未知的永恒,我在與三條江水同時對話,只是我們的交流是無聲的,因為我自己也成了江的一部分,混同于江中的游魚、水草、江石和冰雪,我在與流動的時空對談,而冰雪可以將這樣的對話永恒記載下來。
我踮起了腳尖,輕輕地在冰江上轉動身體,我要與江水共舞,我聽到空中傳來悅耳的音樂,我跳得那樣輕柔,那樣迷醉,那樣深情,那樣忘我,就如同抱著心愛之人的身體旋轉,飛舞——我跳的那支舞就叫冰河上華爾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