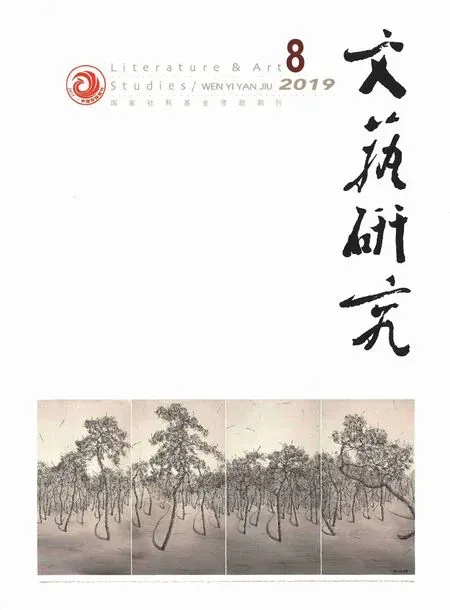屈原及其作品研究的文化視野
——評聶石樵《屈原論稿》
劉全志
(作者單位 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

聶石樵的《屈原論稿》①,是一部屈原評傳式論著②,該書由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2月初版,其后又于1992年4月修訂再版。評論者指出,修訂版篇幅增加了近一倍,主要是修正了相關提法、加強了對論證資料的征引、增設了相關章節,修訂部分很能反映出作者于“此書出版后的十年間,在屈學研究方面不斷探索和開拓的新進展”③。正是由于這種不斷探索和開拓,2010年5月《屈原論稿》又在中華書局出版,并于2015年10月收錄于《聶石樵文集》第五卷。一部《屈原論稿》,先后出版四次,從20世紀80年代初一直迤邐至今,時間跨度三十多年。按照古人的說法,三十年為一世④,《屈原論稿》從初版至修訂版再到最終收入文集,前后經過了“一世”,其內容與研究方法也已影響了幾代學者。從1983年至2010年,報紙、書籍、雜志對《屈原論稿》的評介不少⑤。這一現象無疑昭示著這樣一個事實:學術話語、學術環境也許已經悄然發生了變化,但《屈原論稿》的影響依然強勁,其中所論頗值得當今學界反思和借鑒。
與《司馬遷論稿》“長于深化”相比,聶石樵明言“《屈原論稿》勇于創新”⑥,這一自我評價一方面來自學界對此書的品評,另一方面則源于作者的自勵。誠如湯炳正所說,自劉安、司馬遷以來,有關屈原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是“熱門”當中的“熱門”⑦。如果沒有宏闊的文化視野、熱情探索的信心和勇氣,又如何走向創新和突破?三十多年前,這一課題擺在了聶石樵面前,而學界的評價和贊譽早已證明他實現了自己的目標。當今,我們新一代學者也同樣面臨這一問題。也許對此做出的回答存在仁智之別,但毫無疑問的是,前輩學者的創新之路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財富,值得進一步繼承發揚。
一、歷史意識與屈原的生平
在談及《屈原論稿》的內容時,聶石樵自言:這部書是“對屈原的時代、生平、思想、作品進行比較全面、系統的探索;闡明屈原及其作品和他那個時代的深刻聯系,闡明屈原及其作品出現在那個歷史轉變時期的意義;內容涉及屈原的哲學思想、美政理想、美學觀點和文學成就。總之,想通過以上的論述全面地認識屈原、評價屈原,說明屈原的思想和作品怎樣深刻地反映他那個時代、表現他那個時代”⑧。顯然,與以文本為中心的研究相比,聶石樵關注的是作家研究,但他的作家研究無疑又是以閱讀和理解文本為中心的,即“作家研究是古代文學研究的一項重要內容,通過作家的素養以及他對時代政治和文化的反映,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理解文學作品產生的機制,理解文學作品的意義和價值”⑨。也就是說,認識、評價屈原,是為了更好地理解他的作品,而要達到這一目的,需要理解他生活的時代以及他表現時代的心理動力和話語方式。因此,聶石樵特別注重古代文學研究中的“歷史意識”,他說:對于歷史熟悉到什么程度直接決定著對文學作品了解到什么程度,并明確指出,“古代文學屬于過去的時代,學術研究應該追求久遠的價值”,特別是“對文學現象和作品的理解,不能脫離社會歷史的背景和具體的歷史事實,否則就容易成為想當然,陷入空談”⑩。顯然,這種“社會歷史的背景和具體的歷史事實”,就是歷史學者一貫強調的“必要的證據和大量可靠的證據”?,沒有歷史意識,對作家、文本的閱讀和理解必然會陷入臆想,由此而生發的議論往往只能是囈語。
如果缺乏必要的歷史意識,研究屈原及其作品常常會得出比較“怪異”的判斷。如《劍橋中國文學史》在談到“早期中國文學”時說:“與《詩經》不同,《楚辭》從未得到過帝國的官方承認。”?這一論斷貌似“新穎”“準確”,而其中的判斷標準和依據又頗讓人困惑:什么狀態才算是得到“帝國的官方承認”?“官方承認”的根據又是什么?得出這樣結論的原因和推演過程頗值得推敲。若其中的“帝國”是以西漢而論,將設立博士、立為官學才算是得到帝國的官方認可,那么涉及的文本會很多,如毛詩、《左傳》《國語》甚至承載黃老道家思想的《老子》等都沒有立為“官學”,更不要說那些諸子百家著作了。這樣以“帝國的官方承認”為標準,又如何突出《楚辭》的獨特性?再以與《楚辭》相類的漢大賦而言,在西漢時期蔚為大觀,深受皇帝及上層貴族的喜愛,但是又有哪一代皇帝將之立為“官學”了?如果其中“帝國”的范圍可擴展至東漢以后的帝國時代,后人將楚辭作品編入《文選》、詩賦取士以及諸如洪興祖、朱熹等官員、大儒對《楚辭》作注,甚至宋神宗將屈原封為“忠潔侯”?等,應該算得到“帝國的官方承認”了吧?
當然,準確地說,聶石樵對歷史意識的強調,也并非僅僅宏觀勾勒一下文學作品或古代作家所處的歷史環境,如果這樣做,歷史事實與文學作品還是“兩張皮”,只是將文學作品貼上了歷史的標簽,而在實質上兩者并沒有融會貫通。毋庸置疑,這樣使用歷史意識來理解作家、作品,是十分機械、生硬的,同時也是無效的。而聶石樵所說的“歷史意識”,是與《孟子·萬章上》所謂“知人論世”和“以意逆志”的方法融合為一的?,即“將作品當做一個歷史事實,回到作品的歷史背景上去”,這樣不但能“揭示作品的具體內涵”,還能準確地把握作品、作家的“文學史的意義”?。具體到《屈原論稿》,最能體現聶石樵這一研究意識和研究方法的,無疑是對屈原人生歷程與創作關系的考察。
在《屈原論稿》中,作者將屈原的生平描述成一個動態的生命軌跡,即由少年至青年、壯年再至暮年的完整歷程。如有關屈原的身份和任職經歷,自20世紀40年代以來,一直存在著“文學弄臣”的爭議?,再加上自古以來有關左徒、三閭大夫職守的討論,學界對屈原身份及其與楚王室關系的認識越發模糊。在諸多爭論之后,聞一多認為屈原同時具有“弄臣”“使臣”“政治家”“文學家”的身份,即“弄臣”與文學家的合體,“沒有弄臣的屈原,哪有文學家的屈原”?。屈原的這一多元化身份雖然能夠解釋文獻記載的一些矛盾,但是仍然是以靜止的眼光來看待屈原人生乃至作品創作的。
與聞一多不同,聶石樵認為屈原為“文學侍臣”只是其成長歷程中的一環,并不能以此作為屈原身份的標志。這就如同孔子在未擔任眾弟子之師以前做過“乘田”“委吏”一樣?,我們顯然不能以此來指稱孔子。戰國時期士人學派不同,價值理念有別,但他們無疑都存在著一段近似而又相異的成長歷程,孔子、孟子、荀子不例外,屈原也同樣如此,幾乎每一位士人成長的背后都有曲折而又豐富的人生經歷,所以,孟子才會說:“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在《屈原論稿》中,屈原的人生經歷是分階段的,由“賤貧”到“文學侍臣”只是他早期成長的一段履歷?,后來他又擔任左徒、三閭大夫,由于職務的變化,活動場所也由蘭臺走向朝堂,由朝堂“自疏”于漢北(第39—44頁)。
值得強調的是,《屈原論稿》在討論屈原人生經歷的各個階段時,密切關注屈原的創作情況,力求將人生歷程與文學創作緊密關聯,進而做到“知人論世”與作品闡釋的無縫對接。作者指出,在屈原的人生經歷中,存在兩次比較集中的文學創作,正是這兩次創作成就了作為“文學家的屈原”:第一次是“自疏”于漢北之時,第二次是遠赴楚國西南之時,它們分別處于屈原的壯年和晚年。《屈原論稿》之所以這樣判斷,均存在屈原作品內在的證據。如第一次創作高潮的代表作《離騷》之所以被認定為壯年作品,實為屈原所自言“及余飾之方壯兮”“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等,甚至其中的主人公兩次飛升、不斷“求女”的過程本身就暗示著“《離騷》是他壯年的作品”(第43頁)。正是依據諸如此類的文本信息,聶石樵不認同林云銘、游國恩、孫作云等諸家觀點,而認為屈原此時離開郢都到達漢北,是“自疏”而非被“放逐”?。屈原“來集漢北”的選擇性與主動性?,促使了創作高潮的到來,除《離騷》《抽思》之外,《天問》和《九章》之《惜誦》《思美人》均作于此時。
屈原第二次創作高潮的到來是在旅居陵陽九年之后?,此時屈原決定離開陵陽遠赴西南,而在生命終結之前“寫了《懷沙》和《惜往日》”(第45頁),這兩篇是屈原的“絕命辭”。在聶石樵看來,屈原的這次旅行發生在暮年時期,他離開陵陽時正值楚襄王十二年,其時屈原五十二歲,旅行三年后自沉于汨羅江(第45—46頁)。正是這暮年時期的旅行,成就了《懷沙》《惜往日》《涉江》《悲回風》以及除《國殤》之外的《九歌》篇章(第45—46、188頁)。有研究者已經指出,與“白起破郢、屈原殉國”之說相比,聶石樵將屈原的人生定格于楚襄王十四年(前285),更符合“屈子作品反映的晚年經歷”,因而也“更接近研究對象的實際情況”?。由《屈原論稿》的屈原生平研究可知,屈原的人生歷程更像一場文學作品的集結過程。從壯年時期的《離騷》《天問》,到晚年時期的《懷沙》《惜往日》,其中有屈原的自由、暢快、質疑、困惑、糾結和痛苦,更有逐漸加深的憂郁和絕望。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屈原的生命走向了終結,而他的作品也得以集結、傳承乃至不朽。
二、屈原與荀子的關聯
在現存文獻中,最早將屈原與荀子并稱的應是《漢書·藝文志》,班固在著錄五種詩賦之后云:“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實,在此之前,“荀卿賦”和“屈原賦”的著錄,不但分屬于兩種不同的賦的開端?,而且中間還有“陸賈賦”:屈原賦20種,陸賈賦21種,由此可見“屈原賦”與“荀卿賦”之間的距離。也許正是因為這一排列,雖然班固將荀子與屈原并提,并直言兩人均有相同的人生經歷即“離讒憂國”,又有相似的創作文體即“皆作賦以風”,但后人往往將兩人的經歷、賦作分而論之,即使將兩人同在一文論述也互不關聯?。這一研究方式可能源自一直存在的潛在觀念,即一般認為荀子之賦與屈原的作品存在著顯著的差異,如章太炎在《國故論衡·辨詩》中說:“《七略》次賦為四家:一曰屈原賦,二曰陸賈賦,三曰孫卿賦,四曰雜賦。屈原言情,孫卿效物……屈原的賦是道情的,孫卿的賦是詠物的。”?對此,李炳海指出:“太炎先生所持的是廣義的賦類作品的概念,把屈原的楚辭作品也歸入賦類,沿襲的是《漢書·藝文志》的做法。把荀子賦認定為詠物,實為不刊之論。”?章太炎論學以文字訓詁為主,又出入經史,他延續《漢書·藝文志》的分類方法符合他的治學理念。但李炳海認為其依據的是“廣義的賦類作品的概念,把屈原的楚辭作品也歸入賦類”,顯然是當代學者從辭、賦兩分的角度加以評判的,即屈原的作品是辭,而不是賦;荀子的賦不是辭,而是賦。費振剛在討論這一問題時,重點即在限定辭的地域、形式、時代,以之與賦相剝離?,然而漢賦類別之中的騷體賦一直代有傳承、延續不衰,顯然是“楚辭在戰國之后走向沒落衰歇”的反例?。以漢人的記載來看,辭、賦兩分的觀念至少沒有考慮《荀子·賦篇》之賦的真正所指?、班固將司馬相如之賦歸入“屈原賦”一類的事實。所以,將屈原的作品排除在賦類之外,不但會將漢賦理解得過于狹隘,而且也很難梳理賦文學的發展歷史,更不要說打通屈原之賦與荀子之賦了。
其實,早在南宋時期王應麟就依據《荀子·不茍》與《楚辭·漁父》言辭的相同,發出這樣的疑問:“荀卿適楚,在屈原后,豈用‘楚辭’語歟?抑二子皆述古語也?”?可嘆的是,王應麟這樣的疑問,也發生在當代學者身上,李炳海認為《九章·思美人》的抒情主人公感慨“愿寄言于浮云兮,遇豐隆而不將”的表達方式,與《荀子·賦篇》之“云賦”中的“行遠疾速而不可托訊者與”“大體一致”,即均暗示“浮云無法為人向遠方傳遞信息”?。對于兩篇文辭的“大體一致”,李炳海認為:“《云》賦與《思美人》的云意象彼此相通,是出于偶然的巧合,還是荀子讀過《思美人》而受到啟發,對它予以借鑒,已經無法得到確證。”?當代學者的“是……還是”與王應麟的“豈……抑”,所用的言語文辭是多么的相似,心態又是多么的神似!
在李炳海之前的1988年,趙逵夫討論《荀子·賦篇》的構成時指出,《賦篇》的佹詩是《荀子》真正的“賦”,它不僅在句式、內容上同于諸如《橘頌》《涉江》《抽思》《懷沙》《天問》等篇章,而且結構分為“小歌”也與屈原作品相似,進而,他認為這些信息可以看出荀賦與屈原作品之間的“前后繼承關系”,《賦篇》之佹詩“正顯示了從屈原以來歌詩向誦詩的轉變”?。趙逵夫的觀點直接承自魯迅而又有新的闡釋,魯迅在討論《荀子·賦篇》時說:“又有佹詩,實亦賦,言天下不治之意,即以遺春申君者,則詞甚切激,殆不下于屈原,豈身臨楚邦,居移其氣,終亦生牢愁之思乎?”?1991年,廖化津在討論屈原為歷史人物時,又說《荀子》之《成相》“陳辭”、《賦篇》“莫之媒也”等用語也是屈原的常用語?。
無疑,王應麟、魯迅、趙逵夫、李炳海等古今學者的感覺、體悟都在指向荀賦與屈原之賦的關系,而這一課題在當代學者中,涉及最早的應該是1982年初版的《屈原論稿》,而且,與上述學者的梳理不同,聶石樵討論及觀察的范圍早已超出了兩人在賦體文本之間的關聯。換言之,除了兩人賦作上的關聯,聶石樵已經考慮到兩人整體文章風格的相似,如他指出,《荀子·議兵》“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是以香草象征美德”;又《荀子·勸學》“蘭槐之根是為芷,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是以香草變成臭草比喻人的品德由善轉為惡”(第237頁),而這兩者都與屈原《離騷》“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等句(第237—238頁),存在高度的相似;而且《離騷》“從立意和語調看,都很像荀子的《成相》篇”(第60頁)。顯然,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聶石樵的眼光已經觀察到《荀子》文章整體風格之于屈原作品的關聯,而不僅僅局限于《賦篇》文本。
更為重要的是,聶石樵不僅注意到了荀子與屈原作品文辭風格的相似,還把更多的精力與筆墨放到了兩人思想觀念、人格風范之間關聯的研究。而且,他在這一方面的分析細致入微,三十多年之后讀之仍令人拍案叫絕,比如他說:
荀子主張治國安民必須實行“美政”“美俗”(《儒效》),只有實行美政、美俗,國家才能富強。屈原則執著地勸諫懷王推行“美政”,以期望“國富強而法立”。荀況講修身,著《修身》篇;屈原也重視道德修養,自謂“獨好修以為常”。荀況寫《天論》,論天人之分,屈原寫《天問》,對天命提出了質疑。荀況寫《賦篇》,屈原則是我們文學史上最偉大的辭賦家。(第60頁)
可見,聶石樵對屈原與荀子關聯的研究,顯然是在更為廣闊的歷史空間和文化視野中進行審視的。在2010年《屈原論稿》第3次出版之際,聶石樵在訪談中直言:研究屈原的思想“是一個吃力不討好的論題”,但“這確實是一個歷史問題,我們也不應該回避它”;屈原的思想“與荀子非常相似,處在儒法漸變的過程中”;搞清楚這個問題,再借助荀子講的“美政”和“修身”,我們“可以評價屈原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和貢獻”?。
在聶石樵視野的啟發與引導下,他的學生曹晉撰文更加深入、細致地比較了屈原與荀子在思想及人格上的異同?,其論文發表于1998年,這已是《屈原論稿》初版后的第十六個年頭。我們常說,時間是檢驗一切的最好標準。顯然,《屈原論稿》的創新性,已經經受住了時間的檢驗。
以當今研究楚辭、漢賦的趨勢來看,聶石樵關于屈原與荀子關聯的分析仍然具有很大的啟發意義。如我們對于辭、賦兩分的認識以及對于漢賦起源的探討,是否真的符合賦體文學發展的歷史?屈原作品在戰國時期的傳播和影響,難道僅止于宋玉、唐勒以及荀卿之賦?漢賦的內涵、歸類及發展線索,是否真的需要將騷體賦剔除?這些問題,顯然需要我們逐步清理,否則域外學者還會得出諸如“《楚辭》從未得到過帝國的官方承認”之類的怪異論斷。
三、華夏文化之于屈原創作的意義
楚文化與中原文化的關系及定位,也是《屈原論稿》關注的重要問題。在作者看來,屈原作品雖然具有楚地的特殊性,但毋庸置疑的是,只有楚地的祭祀、民俗顯然也是產生不了楚辭的。因為關鍵的“問題是先秦時期楚文化不是封閉的,它與中原文化總是處在互相交流、互相融合之中,楚國在春秋時期是周天子統治下的屬國,多處史籍記載了中原史官、賢人、典籍在楚國的活動、傳播和影響,而屈原作為一個有著高度政治和文化修養的士人,他對中原文化的接受”,“也是他創作文學作品的主要精神動力和支柱,所以,如果我們斤斤于屈原作品中的楚文化因素,而完全忘記或否定屈原作品中的中原文化精神,這就有些舍本逐末了”?。
聶石樵十分強調屈原對華夏文化的吸納和創新,比如討論屈原的美政理想、批判精神、天命觀、美學思想以及藝術手法的繼承和創新,都注重勾勒華夏文化與屈原作品之間的密切關系。這說明在聶石樵看來,屈原的創作雖然具有很明顯的楚國特色,但仍是華夏文化的集中表現。因此,聶石樵在討論屈原思想的方方面面時,總是將屈原與戰國諸子百家的思想、行為加以比較、衡量。除了荀子,他還將屈原及其創作與孟子、莊子、惠子、韓非子以及稷下學人甚至縱橫家的行為相比較(第61—88、105—117頁)。
聶石樵指出,要真正理解屈原的作品,必須將古人的生活習尚與原始宗教結合起來考察(第129—142頁)。從《屈原論稿》所列的事例來看,作者所說的“生活習尚與原始宗教”除了楚地的風尚,還涉及中原各國的習俗和宗教信仰,如歷史上的夏、商、周社會以及魯國、齊國、鄭國等地的習俗、信仰,舉證的文本除了《楚辭》,還有《詩經》《周禮》《禮記》《左傳》《國語》《論語》《莊子》《山海經》《呂氏春秋》等。由此可以看出,聶石樵在注意突出“楚朝廷郊祀之典和民間祭祀之禮”“保留著濃厚的原始社會的風習”的同時(第135頁),仍在強調楚地的“原始宗教”是華夏文化的一部分,屈原的創作延續著華夏文明的意識和觀念。如龍、鳳在《楚辭》中習見,而“楚國并不以龍、鳳為圖騰”(第135頁),那么這又來源于何處呢?結合《禮記》《論語》《周易》《左傳》《莊子》《山海經》等書的記載,聶石樵指出,屈原作品“對龍、鳳的景仰和贊揚”都是“華夏族以龍、鳳為宗神的遺俗”,“屈原對夏、商歷史”極為熟悉,“因此,他在作品中表現崇拜華夏族宗神龍、鳳的遺風便是自然的了”(第138頁)。顯然,在聶石樵的觀念中,楚地文化至少在屈原時代已成為華夏文化的一部分,因此楚辭作品一方面具有楚國地域特色,另一方面無疑又具有華夏文明的知識觀念和精神意識。簡而言之,屈原的創作實為華夏文化與楚地特色共同作用的結果。聶石樵指出:“楚文化有其鮮明的特點,體現了楚民族的風俗、習尚、信仰等,但其精神實質并其筋骨則是華夏文化。屈原及其作品便是這種巫文化融匯入華夏文化的集中產物。他既具有楚民族的特點,又具有華夏文化的精神實質,其核心是華夏文化。”?毋庸置疑,在作者看來,華夏文化與楚文化的關系是大范圍與小地方的聯屬,我們不能將這兩種文化加以對立、割裂,也就是“不能把屈原及其作品所體現的特點,從華夏文化中分割出去”(第297頁)?。
今天看來,聶石樵20世紀80年代的不少論述,不但沒有過時,反而更值得我們珍視和反思。比如,當今出現了許多有關屈原題材的影視劇,它們往往從地域文化、地域觀念的立場出發對屈原加以重塑和表現,正如趙彤所說:“如果《大秦帝國》只尊秦而貶楚,《思美人》只護楚而短秦,各自只說己之所美,不述己之所惡,將古之一諸侯的立場與今之一地域之喜好結合,來演繹戰國史,讓華夏體系內的戰國史故事講述,以地方功利化為先導和旨歸,這可能是目下正逐漸熱起來的‘戰國題材’創作最大的缺陷。”?當代文學及影視劇的這種創作趨向,是當前社會對戰國歷史文化認知、理解和研究的一種體現,與地方政府突出本土旅游文化?、期望以“文化搭臺,經濟唱戲”來提升地方經濟實力的訴求密不可分。各個地域著力挖掘自己的歷史文化本是一件大好事,由此借機發展經濟也無可厚非,然而,對于學術研究來說,應該本著純粹的、求真求實的態度,至少不應以功利目的為宗旨,只有這樣,我們對屈原及其作品的理解、評價才能把握住本真與關鍵。
當今學界這種過于強調楚地地域文化的研究趨勢,集中表現在對《離騷》“三后”的解釋上。“昔三后之純粹兮”之“三后”,王逸以為“謂禹、湯、文王”,名單與其所注《大招》之“三王”相同?。對此,朱熹表示懷疑:“疑謂三皇,或少昊、顓頊、高辛也。”?但這一懷疑,并非將“三后”指向楚地,而是提升了“三后”的時代及地位。以目前的文獻來看,最早認為“三后”指楚先王的是明代的汪瑗,他認為:“三后謂楚之先君,特不知其何所的指也……以理揆之,當指祝融、鬻熊、熊繹也。”?汪瑗所撰《楚辭集解》往往喜歡標新立異,四庫館臣曾批評他“以臆測之見,務為新說以排詆諸家”?。后代學者對其觀點雖然沒有直接承繼,但也往往將“三后”限定于楚國先王,如王夫之認為:“三后,舊說以為三王。或鬻熊、熊繹、莊王也。”?這一問題延續至當代,特別隨著楚文化在楚辭研究中的影響力日趨強盛,“三后”為楚之先王幾乎成為學界共識,如劉永濟認為:“下文始舉堯、舜、桀、紂比言之。此處自以稱楚之賢后為當。”姜亮夫也說:“三后猶言三君,指楚之先君言。”在這一“共識”之下,趙逵夫認為“三后”實指楚三王:句亶王、鄂王、越章王。黃靈庚依據新蔡葛陵楚簡、望山楚簡之“三楚先”,認為“三后”指老僮、祝融、鬻熊。如此,從汪瑗首發延續至當代學者,《離騷》之“三后”成為楚地之先王已成“定論”,剩下的問題只是討論楚之先王具體指哪三位。對此,聶石樵并不認同,他認為其中“三后”首先應指“三皇”,“指黃帝、顓頊、帝嚳”,并指出《離騷》對“堯、舜、禹、湯、文王”“贊不絕口”,“而這些人物并不是楚國的,而是被作為華夏民族天下一統的政治領袖來看待的”(第62頁)。如果結合《離騷》文本所透露的信息來看,會發現聶石樵的觀點更為妥帖。
如果“三后”是指楚之先王,那么堯、舜“既遵道而得路”,“遵”的又是誰的“道”,又怎樣“得路”的?如果說其中的“道”具有抽象的意義,而這一抽象意義的“道”仍然要有所屬。而之前的“純粹”之“三后”顯然就是“堯舜遵道”的依據。既然被堯舜所遵,必然生活在他們之前,而不可能是楚之先王。在汪瑗、戴震等人討論的基礎上,楊義認為:“針砭楚國現實政治,先從楚國古代卓有勛業的賢明君主說起,較為得體,而避免開口就禹、湯、文王那么大而無當。”這一議論,與古代學者一樣,沒有注意到堯舜“既遵道而得路”的明確表述以及《離騷》前后文的承繼關系。
楚文化至遲到屈原時代已納入華夏文化圈的范圍,這從眾多的出土文獻亦可加以證明。郭店簡、清華簡、上博簡、長臺關楚簡等出土文本均使用楚文字書寫,但書寫的內容多是《詩經》《尚書》《周易》以及儒家、道家、墨家、兵家等諸子百家的文本。這至少說明楚文化早已不是華夏文化的對立面,而是其組成部分之一。更為典型的是,上博簡有眾多楚辭類作品,而且是與《周易》、詩類、道家、儒家等文本一起現世的,這有力地說明屈原及其作品乃是“楚文化融入華夏文化的集中產物”。
統觀《屈原論稿》全書,還有諸多的創新處和啟發點,它們浸透并彰顯著作者的學術理念和研究精神,已成為我們研究屈原、理解楚辭的基礎和鑰匙。
聶石樵在談到自己研究古代作家及其作品的動機時,多次強調自己的憂傷“幸可寄情古人,而屈原、司馬遷、杜甫、李商隱,此皆心懷憤懣而以情動人者”;同時,他在《司馬遷論稿》的“自序”中認為,屈原、司馬遷、杜甫、曹雪芹四人雖生于不同時代,但“各自處在一個由鼎盛轉向衰敗的時代,他們作品的價值就在于反映了這一轉變時期的歷史特點,反映了這一時期的社會面貌”。可見,屈原、司馬遷、杜甫、李商隱、曹雪芹,是聶石樵特別強調的五位古代作家。而《屈原論稿》《司馬遷論稿》已經完成,我們可以假想:如果他時間和精力允許的話,或會接著寫作有關杜甫、李商隱、曹雪芹的論稿。
① 聶石樵:《屈原論稿》,《聶石樵文集》第5卷,中華書局2015年版。本文引文出自該書者,皆據此本并隨文標注頁碼。
② 1984年,洪湛侯評論《屈原論稿》云,“這是一部比較全面的評傳式的著作”(洪湛侯:《楚辭要籍解題》,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1頁);1996年,郭建勛也認為“《屈原論稿》為評傳式著作”(中華孔子學會編輯委員會組編《國學通覽》,群眾出版社1996年版,第605頁)。
③??潘嘯龍、毛慶:《楚辭著作提要》,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15頁,第416頁,第416頁。
④ 《說文解字》:“三十年為一世。”(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89頁。)
⑤學界發表的主要評論文章如下:湯炳正《關鍵在于勇于探索——〈屈原論稿〉讀后》,載《光明日報》1983年1月11日;洪湛侯《楚辭要籍解題》第六十一節“《楚辭新注》附《屈原論稿》”,第435—444頁;潘嘯龍、毛慶《聶石樵:屈原論稿[附]楚辭新注》,《楚辭著作提要》,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15—522頁。
⑦湯炳正:《關鍵在于勇于探索——〈屈原論稿〉讀后》。
? 葛兆光:《大膽想像終究還得小心求證:關于文史研究的學術規范》,載《文匯報》2003年3月9日。
? 孫康宜、宇文所安:《劍橋中國文學史》,劉倩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版,第106頁。
? 《宋史·神宗本紀》載,元豐六年正月“丙午封楚三閭大夫屈平為忠潔侯”(《宋史》,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309頁)。
??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735頁,第2762頁。
? 葉罕云:《聞一多論屈原:從“文學弄臣”到“人民的詩人”》,載《名作欣賞》2012年第32期。
? 孫黨伯、袁謇正主編《聞一多全集》第5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20、23頁。
? 匡亞明:《孔子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29頁。
?? 劉全志:《〈屈原論稿〉的屈原生平研究與創新》,載《斯文》第4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版。
? 聶石樵關于“陵陽”具體所指的啟發與影響,參見劉全志《〈屈原論稿〉的屈原生平研究與創新》。
? 《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746頁。
? 李零:《蘭臺萬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版,第123、128頁。
? 如陳良運《論荀子和屈原的詩學觀》(載《暨南學報》1993年第4期)談及兩人的詩學觀,無論分析其內涵還是論述其影響,均采取分而論之的方式。這一研究方式在討論漢賦起源及賦體樣式時表現得更為突出和明顯,如高專誠《荀子的文學成就和影響》(載《名作欣賞》2016年第22期)。
? 章太炎:《國學概論》,中華書局2003年版,第60頁。
??? 李炳海:《荀子賦文本生成的多源性考論》,載《諸子學刊》第14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
? 費振剛:《辭與賦的區分》,載《中國楚辭學》第6輯,學苑出版社2005年版。
? 關于楚辭隨著戰國時代結束而衰竭的觀點,詳見費振剛《辭與賦的區分》。
? 如趙逵夫依據荀子《賦》的文本內容及古代文籍著錄篇數的變動,認為荀子之《賦》可分為兩個部分:隱與佹詩,而真正的賦就是佹詩,它是“《賦篇》的本來內容”(趙逵夫:《〈荀子·賦篇〉包括荀卿不同時期兩篇作品考》,載《貴州社會科學》1988年第4期)。
? 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一〇,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319頁。
? 趙逵夫:《〈荀子·賦篇〉包括荀卿不同時期兩篇作品考》。
? 魯迅:《漢文學史綱要》,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版,第12頁。
?廖化津:《屈原決不是“傳說人物”——駁屈原不見于先秦典籍說》,載《云夢學刊》1991年第2期。
? 參見曹晉《屈原、荀子人格異同論》(載《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98年第2期)和《屈原、荀子思想異同論》(載《江漢論壇》1998年第2期)。
? 趙彤:《這個屈原有點“嫩”》,載《光明日報》2017年5月24日。
?徐亞平、司念偉:《屈子文化園蓄勢“起飛”——湖南理工學院做實屈原文化產業》,載《湖南日報》2018年6月21日。
? 洪興祖:《楚辭補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7、226頁。
? 朱熹:《楚辭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頁。
? 汪瑗:《楚辭集解》,北京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14頁。
?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269頁。
? 王夫之:《楚辭通釋》,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