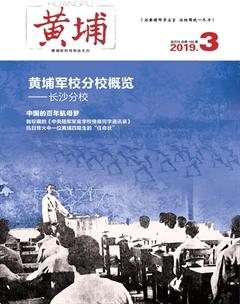父母情意常懷念
駱大仁
父親駱德敬,1913年生于四川雙流縣。父親天資聰敏,自幼喜好國學,尤其愛好中國古典詩詞文學。父親18周歲高中畢業即投筆從戎,自普通一兵始展開軍旅生涯。1939年,父親經其兄駱德榮將軍介紹,進入黃埔軍校高教班學習,成績優良。駱德榮,四川雙流人,經孫中山先生介紹進入黃埔軍校,3期畢業。1926年國共合作,駱德榮赴蘇聯中山大學學習。同期學友有鄧小平、蔣經國、烏蘭夫等。1944年,任原第五戰區長官部政治部中將主任,時年41歲。1944年,河南老河口之戰,駱將軍親自立身前沿陣地,指揮作戰,消滅日軍1600多人。
1942年,父親在四川資陽縣任國民兵團副團長(系地方武裝部門)。當時,縣衙眾官亂抓壯丁,收受錢財,層層加碼,以謀私利。父親得知后,予以抵制,得罪縣長及同伙官員,密謀加罪,準備抓之。父親一怒之下,欲持手槍進縣衙與一干人相拼。幸被朋友勸阻,曉以利害,即辭職離開資陽這一是非之地。經駱德榮推薦,父親奉調江西廬山,在國民黨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19期學習(時任校級軍官)。結業之時,蔣介石知父親是駱德榮之弟,欣然召見,并合影留念。

1943—1945年,父親在河南、武漢等地參加抗日戰爭,其間曾在第五戰區駱德榮將軍領導下負責征兵事務。
1946年,父親擔任國民黨軍委會河南軍官總隊上校總隊長,辦理百余名國民黨將、校級軍官復員事宜。因牽涉上述軍官復員之后的生計之事,風波不斷,事雜人煩。幸在武漢警備司令部參謀長等黃埔學友幫助之下,較好地處理了此項險象環生的復雜事務。1947年,父親升任國民黨中央委派的“西康督導專員”之職,趕赴原西康省(即今雅安市)就任。原西康省主席劉文輝為擴大勢力,以師長相許,父親謝卻。1949年,父親任原新12軍少將高參,參與中共成都地下黨領導的起義。
新12軍起義指揮部在溫江向全國發出起義通電后,父親著重做了雙流縣參議長彭直先的工作,因此,雙流和平解放,彭直先主動協助共產黨縣人民政府開展維持社會秩序、安撫百姓的工作。父親在溫江起義后,得知解放軍部隊已挺進至距雙流縣城數里的五洞橋處,而雙流城內縣中學校,尚駐新12軍直屬旅部隊,但通訊已斷。為不致刀兵相見,保地方安寧,父親立即乘車,帶司機和副官,從溫江趕至雙流城外解放軍駐地,同部隊指揮員見面,講明身份,言已起義,且本人時任城內直屬旅軍隊之副旅長,愿立即進城,勸軍隊放下武器。解放軍指揮員即令幾名偵察員同車趕去雙流中學。父親向旅長宣布:軍部已通電起義,速令全旅停止抵抗。至此,雙流縣和平解放。1949年12月23日,胡宗南逃離成都。擁有上千年文明歷史的錦官蓉城回到人民懷抱。
父親起義后,面臨人生之重要選擇,經張萬祿(時任中國共產黨川西行署組織科長,曾任中共四川地下黨領導成員)熱誠開導,指明形勢,他于1950年元月正式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先去重慶西南軍政大學高級軍官研究班學習,后正式轉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高級步兵學校高級軍官研究班學習,當時,按照解放軍師級干部任職。我們全家都在部隊隨軍生活。
1951年12月,因歷史原因,父親在重慶“西南戰犯管理所”學習勞動。處理前夕,西南軍區軍法處將父親召至辦公室,時重慶歌樂山區正逢大雪,天氣極寒,烤著火盆,于喝茶之中,宣布處理決定。四川省公安廳長曾到所內,坦誠同各位學習人員談話:“希望大家好好學習改造。共產黨有信心做好這次工作。我們將來還要共同建設社會主義社會。”
1952年7月,父親學習勞動期間,某日上午,肩挑煤炭約125斤,走坡登頂,疲累歇息,極目遠望,山峰起伏,思緒縈繞,詩興發也,即賦詩一首:
千頭萬緒感慨處,
一擔登坡不二時;
若問天涯何處樂,
乘風擔過此坡時。
思父當時處境,尚能樂而應之,可見父親之人生觀,經歷磨練仍樂觀若此,實令人敬佩。
1955年,父親給劉少奇副主席辦公室負責人、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樂昌國同志寫信,請他規勸其兄樂恕人回歸祖國大陸。樂恕人是我母親樂致和之胞兄。曾任國民黨中央日報副總編兼采訪室主任,曾在1945年11月24日,作為唯一代表中國新聞界的記者,在德國紐倫堡軍事法庭,見證審判德國一級戰犯。1949年,樂恕人曾專程乘飛機趕回成都,在溫江和我父親詳談,愿將父親一家全部帶至臺灣,而父親正參與起義工作,道不同,但不能明言,遂婉言謝拒。父親攜我大姐駱大華,在成都鳳凰山機場為樂恕人送行以謝。當初一別,海峽相隔,父親與樂恕人舅父從此未能見面,極為遺憾。
后來,父親談及此事時講:“我當時身為國軍少將,既有你舅父高層關系,更有我在國民黨‘中訓團學習的經歷,蔣介石因我是駱德榮之弟,召見過我,合影留念。這諸多因素,我到臺灣,前程、生活均會順利。但回想當年,我參軍入伍入學黃埔,為的是救國救民。而1949年那個年代,蔣介石把國家搞得一團糟糕,社會動蕩不安,民眾生計艱難。我之所以起義參加人民解放軍,就是為新社會作點貢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
父親在重慶學會種菜、竹編、燒磚等謀生之藝。1956年返回家鄉雙流縣城,于沖擊、艱苦、平淡之中度過漫漫歲月。1971年,我回家看望父母。父親當時在牧馬山燒磚。母親講:“前幾天,縣上同志領省公安廳領導來家,問了家庭情況,還摸著你爸床鋪,問怎么沒有蚊帳?鋪蓋太舊了嘛。”父親事后談及此事:“當晚,派出所通知我去有事,去后送了全新被子、床單、蚊帳。著重轉達省公安廳領導的話:‘對起義將領要全面妥善對待。功過是非,黨有政策。他們在歷史緊要關頭,成功起義,對和平解放成都是有貢獻的。”談到此處,父親甚為感慨:“我們畢竟是歷史上有錯,在1949年的特殊時期,深受共產黨、解放軍精神感召,起義走向新中國。但現在如此困境之中,共產黨沒有忘記我們,可貴之至。”
至1979年,父親已66歲。眼觀祖國走向富強,人民生活安康,遂只身一人,奔赴北京,到解放軍總政治部反映自身情況,請求落實政策,并要求面見總政主任余秋里同志(余秋里同志1950年任解放軍第二高級步兵學校校長兼政委。1977—1987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1982年任中央軍委副秘書長,總政治部主任)。總政接待同志經請示后,告知父親:“余主任已知道你在第二步校的學習情況,以及后來發生的變故,但這是歷史遺留問題,全國尚有類似情況。將及時請示黨中央,相信黨和政府會尊重歷史,妥善解決此類事務,會安排好你們的生活。”
1980年4月2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成都軍區根據黨中央文件精神,作出明確結論:“駱德敬原為國民黨新12軍少將高參,于1949年12月在四川溫江縣起義,是起義人員。”
父親自1981年起,按政策任雙流縣政協專職委員,盡心參政議政,為雙流及成都市相關地方招商引資,發展經濟,更為海峽兩岸統一之事務,聯絡海內外親友,奔走不息。1987年,父親陪陳季讓老伯(陳毅元帥胞弟,四川省政協秘書長)到我工作的酒廠參觀引資。父親曾對我言:“發展企業,要注重擴大宣傳,凡事之成,縱橫圓合。”在此期間,縣政協在縣府大院內建新樓房,決定分一套給父親,并已交鑰匙(父親當時外出)。父親回后,退還鑰匙給縣政協,稱家有住房,雖簡陋尚可居住,新房分給確有困難的同事。回憶父母相戀之時,樂氏之家多數人反對,都稱:我祖父家道清苦,兩家無門當戶對。獨有大舅父樂恕人,因曾和父親相交數次,彼此意誠,反復向其母陳述:“德敬之君,眉清目秀,學習良好,處事周到,未來前程必好。”舅父身為長子,外婆聽后,認可親事,給我母親一處600平方米的宅院,200畝水田,作陪嫁之禮。解放后土改,念父親起義,只劃走一半,余存之屋,父親又給其二哥150平方米,因此,我老家之房,只余150平方米,到其后政協分房之時,老屋已近50年之久,多次修補,勉強可住。在此狀況之下,父親退還新分之房,確是淡泊度生,令人感慨之至。
寫到此處,成串往事,歷歷在目。父親于1956年回鄉,以種菜、編竹筐謀生。1960年,我12歲,父親編筐至午夜,晨6時起,裝車畢,喚醒沉睡的我,父居中拉車,我在旁協力而行,冒著刺骨寒風行20余里,交貨換錢,方吃早點。父常言:“你尚年幼,本應在家睡好,以利讀書,但家境困苦,你要早一些適應生活艱難,為走向社會,成家立業作好準備。”因家境困難,我13歲即參加工作。因忙于生計,成家之后將3歲兒子駱小龍送老家由父母養育。父親教駱小龍文化知識,在家中庭院教他種菜,父對孫言:“一飯一菜,人生應需,種菜除草,學之有用,當知所食之物,皆是勤勞換得。”
寫到此處,更憶母親之悲喜人生。母親之樂家,是雙流名門望族。祖上曾在江浙一帶為官。后告老還鄉,廣置田產,修建房屋。現雙流縣城中心十字口百貨大樓即是樂家房屋所在地。三重朱紅大門,內有樓臺亭閣,奇石名花。池塘游魚,樹竹蔥蘢。樂恕人舅父1990年11月9日給我的信中,寫詩詠之:
四面窗開三面花,
欣看春色滿鄰家;
岷峨家有花千樹,
萬里歸心惜鬢華。
樂家兄弟姐妹甚多,母親是最小女兒,從小單住華樓,錦衣玉食。1951年,其生活跌入低谷。母親挺身挑起重擔,在成都當保姆,后回雙流老家擺煙攤,去藥材公司當零工,撫養我們兄弟姐妹5人,生活的重擔,致母親患病終身。但她常常掛念我們。1989年來信談及:“小韓(我妻)足病好些否?你們住的6樓太高,少下樓,注意安全。小龍今年春節不要回老家,你馬上要上高中,你爸工作忙,生活苦,你媽足有病,你放寒假后在家多復習,煮飯,照顧你媽。”
我回想起父親在駱德榮將軍逝世之時,為之寫的挽聯:
為光禹域,盡孝盡忠,鋼德以化人,未死精神如春茂。
欲轉乾坤,任勞任怨,熱心而從事,一生勛績似秋潮。
這正是兩位黃埔將軍兄弟的坦蕩心懷寫照。

1984年6月16日,黃埔軍校建校60周年校慶之際,黃埔軍校同學會在北京成立,中共中央和國家領導人李先念、徐向前、烏蘭夫、習仲勛、楊尚昆等領導出席北京盛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及聶榮臻元帥為會議揮筆題詞。父親喜得會議紀念冊,激情寫詩:
黃埔精神軍校歌,
東征北伐掃群魔;
精誠團結孫公教,
扭轉乾坤捐血多。
不必乾坤爭反復,
炎黃兒女豈無人;
中華一統群黎愿,
天下同胞賦有情。
1997年7月,父親病重住院。從電視上觀看香港回歸祖國之盛況,含笑不已。喜言:“國之強大,民之甚樂。”1997年7月22日,父親安祥離世,享年84歲。
寫畢此文,掩筆自思:父親以黃埔將軍之身,經歷動蕩貧窮和繁榮富強的兩個時代,度過數十年風風雨雨的歲月。但父親從不后悔在1949年的選擇。
父親晚年生活,簡樸雅閑。曾對我言:“父身為兩朝將軍,雖擁富貴榮華,也有生存低谷。1949年參加起義,為家鄉和平解放盡綿薄之力。今觀兒女成人,更已成才,意愿足也。再思1949年起義之舉,那是我們那一代人的新意追求。”
父親賦詩一首,贈我留存至今:
淡泊度生三十年,
種花勞作共長天;
浮云萬里飄風散,
且看嬋娟缺又圓。
我們姊妹,幼享錦衣玉食,50年代初,更浸潤于人民解放軍的溫情懷抱之中。然命運之因,突然跌身人生低谷,于磨難中生存。幸有父親、母親的言傳身教給我們注入活力。我們,鼓起不息的勇氣,我們,在生活之路上漫漫求索。中國夢,是中華民族奮斗的方向,我們每個人也都有著自身的夢想。我的夢想就是讓黃埔精神發揚光大,愿世界和平、人民安康:
清風月明星兒閃,
小舟緩緩銀河游;
黃埔精神育后代,
愿將和平漫全球。